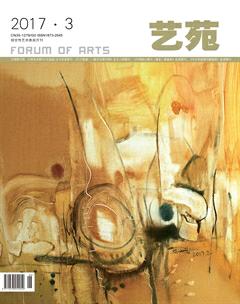音樂調性與色彩的聯覺特征研究
何藝珊+馬強



【摘要】 隨著西方音樂藝術的改革,人們逐漸對音樂調性產生了不同感性色彩的聯覺共鳴。本文采取跨學科研究、文獻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試圖從社會學角度研究音樂調性色彩中“個體特征”與“群體特征”兩者的聯覺現象,總結音樂調性與色彩聯覺模式的特征規律,進而得出其中的聯覺關系模式圖,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評價與展望。
【關鍵詞】 音樂調性;色彩;聯覺;模式;特征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在西方音樂史中,調性是其形式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樂音組合形成不同調式色彩,并具有不同風格、情感等意義指向。那么調性與色彩之間是否有聯覺效應?調性與色彩的聯覺模式中是否具有特征規律?從物理的角度來看,音色與顏色之間存在天然聯系。英國科學家牛頓曾將紅、橙、黃、綠、藍、靛、紫七種顏色,類比對應八度內C、D、E、F、G、A、bB七音(圖1)。路易斯·卡斯勒在《現代音樂與色彩》中也將人耳可聽音頻率范圍與可見光的光譜色帶按比例關聯起來,即由最低音到最高音對應紅色到紫色。音樂中調性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與色彩有著緊密聯系。所謂音樂調性色彩,即通過聽覺,通過不同調性音樂的審美情感喚起人們豐富的視覺意象的感覺,從而形成若干個帶有鮮明主觀色彩的調性色彩表達。音樂調性色彩是發生在感覺層次上的,因此是人所共有的心理反應的視覺表達。音樂調性則是在音樂想象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樂音關系系統,這種聯想是基于音響自身規范與歷史風格的選擇的基礎上的。一種感官同時觸發了另一感官的感受,這種現象在心理學上被稱為“聯覺”現象,聯覺也稱為通感。
本文將從社會學角度研究音樂調性色彩中“個體特征”與“群體特征”兩者的聯覺現象,并總結音樂調性與色彩聯覺模式的特征規律。
一、音樂調性色彩認同的個體特征
(一)斯克里亞賓的類比光線調性色彩論和點描式神秘調性色彩論
俄國的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斯克里亞賓認為音樂中的每個音調都有其相應的顏色對應,隨著升號調號的增多,色彩根據光譜順序由紅色向紫色過渡(圖2)。升降音之間具有“傾向性”,并在色彩上存在變化。升號調與降號調的色彩特征是相似的,但是升號調更為明凈透亮,隨著升號增加,其色彩由明亮逐漸變得鏗鏘有力;降號調較為暗淡,隨著降號的增多,暗淡中越發透亮;同時,大調小調的規律也是相似的。
斯克里亞賓將音樂和色彩作極致連結,并在“總體藝術”概念下發展出自己的神秘主義。他認為音樂、色彩等藝術都是相通的,他與生俱來的天賦便是利用通感整合宇宙大千。在單樂章交響詩《普羅米修斯》中,他將102音對應102種顏色,用“色光風琴”投射彩暈,幻想出音調、震動頻率與色彩之間的相對關系,使音樂與色彩相交融,努力尋求兩者的共鳴;在第三號鋼琴奏鳴曲中,他將音樂肌理打碎,通過點描式色彩來展現曲式;朦朧的曲式使得音樂的內涵也愈發神秘莫測——他名之為“靈魂狀態”。同時他發展了自己的“神秘和弦”—C調、升F調、降B調、E調、A調、D調——所有作品都是基于這些和弦,他的音樂開始在調性中探索一種具有神秘色彩意義的關系。
(二)里姆斯基個性調性色彩論
俄國古典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對調性顏色有著自己獨特的觀點。他的作曲題材個人色彩鮮明,宣敘調以小調類調式為主,整體上聽來色彩柔和暗淡;詠嘆調則以自然大調為主,縱向上使用同音列不同類調式的復合,橫向上則是復合調式與各種單一調式的相間進行。為了突出自己的民族風格,增強描寫性,他將色彩和和聲手法大量運用于作品中。里姆斯基從音樂的形象表現出發,無論是在調式和聲方面,還是在繼承西歐浪漫派色彩性和聲手法方面,都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和創新。尤其是在縱向上各種增減和弦、復合和弦的大量獨立運用,以及在橫向上局部的色彩性和聲手法和整體的色彩性構思等的運用,他都已越出前人的范疇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和聲風格(圖3)。[1]23-29
(三)德彪西的類比光色“保持調性—擴充色彩”法
德彪西依據心理學中的通感原理,用音樂來表現自然界中光與色的變化,將聽覺對應視覺,以感覺為媒介,通過聲與光的對比,從而創造出具有光色性音響效果的音樂表現手法。他采用新穎的音樂方式和表現手法,對表演色彩音樂的傳統創作模式進行改革,其中,和聲創新模式在其音樂色彩表現中起著更為直接的作用。他運用“保持調性擴充色彩”的方法,通過強調調式中心音、調性游移、雙調性以及變化音等創作手法,來加強音樂的色彩性。[2]
1.調式中心音
為了明確調性,德彪西使用“連續或是經常出現的音”,它具有調性中心音的功能,其音樂材料的統一基礎通過采用“調性痕跡”的手法來確立,給帶有人物主觀色彩的調式音階提供了依附感與穩定感(圖4)。[3]196-202整個調中心音的音高走向具有由上而下的發展趨勢,因此音色逐漸變暗和柔和。從整體上看,小節和聲由不穩定到穩定,色彩效果逐漸由明亮轉為暗淡。
2.調性游移及雙調性
《鋼琴練習曲》的第一集中,德彪西利用調性游移或雙調性來增加音樂色彩的變化,“所謂調性游移主要是指在作品中不能明確表明調性或同時呈現兩個及以上的調性意義的音樂片段”[4]76。它的功能是弱化和聲功能,增強色彩(圖5)。
德彪西更注重音樂色彩的表達,他獨特的和聲寫作風格是獲得色彩音樂的重要途徑。音樂的色彩性成為演奏處理方式的表現目的,德彪西將技術問題與音樂表達和語言整合,使其開拓了手指技術練習領域的新視角,豐富并遠遠超越了“練習曲”這一體裁的器樂曲,創造出具有較高欣賞價值的藝術音樂詩篇。
(四)梅西安的有限移動調式及色彩和聲
“色彩的音樂家”梅西安通過音樂勾勒色彩,他的每一個有限移位調式都具有特定的顏色,這些特定的色彩基本都是復合色彩。他利用音高表現色彩,并在和聲中配合使用大量的帶有個人主觀的色彩和弦。這些色彩在高音區逐漸褪變顏色向白色靠近,越發清透;在中音區則最為強烈;在低音區逐漸變暗,向黑色過渡(圖6)。
梅西安采用多個調式交替、轉換與融合,而不僅僅只用一個調式及移位。在他大部分作品中,音樂結構的橫向和縱向對比是通過各種形式的轉換和不同形式的疊加而獲得的。此外,他在調性的中心音不變的基礎上,通過轉換不同的調式來獲得音樂的發展與色彩的變化。
(五)貝多芬社會環境影響下的個人主義調性色彩
集古典、浪漫音樂于一身的路德維希·凡·貝多芬,他一生的創作貫穿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794到1800年,最具代表性的“英雄性”音樂風格在其作品中有著初步的反映,《悲愴》便是他遭受耳聾折磨苦痛的內心獨白;第二個時期是1801-1814年,這時期的作品是他逐漸背離18世紀傳統、進入創新階段的重要標志;第三個時期是從1816到1822,這時期所創作的音樂是他晚期風格的體現,這時期的鋼琴奏鳴曲不同于早期和中期作品的情感激昂、掙扎糾結,而給人以超越世俗的平靜與精神的升華。
貝多芬在不同時期社會環境影響下創作的作品的調性運用與風格不同,其不同時期的作曲調性運用及風格又反映了不同時代的社會背景與人生追求。他的個人主義調性色彩體現在,在社會環境變更的影響下,通過探索不同調性的情感性色彩,將自己對調性色彩的獨到見解充分融入到自己的創作中(圖7)。
在貝多芬的作品中,對調性的使用、作品總體結構及樂章曲式之間的擴展聯系,豐富和強化了音樂的色彩戲劇性和情緒感染力。他的許多作品大都圍繞其基調,根據調式內在關系或作品情感變化需要來選取不同樂章的調性。如,在偉大的第九交響曲中,第一和第二樂章的基調為d小調,第三樂章變奏曲主題基調為對比大調(降B大調),緊接著第四樂章為d小調,最后以同樣的基調在D大調上結束,從而傳達“從痛苦到快樂”的概念。
(六)德拉克洛瓦的色調類比音調的“色彩交響”說
歐根·德拉克洛瓦是深入探討音樂與造型藝術的相似性和潛在的藝術表現力的第一人。在德拉克羅瓦的繪畫作品中,“色調”的完美和諧來源于畫家頭腦中先現的“和聲”,同時,色彩的使用也不再依賴客體,這一切背后的創作理念都與浪漫主義音樂的創作理念是一致的。德拉克洛瓦在與肖邦的談話中,對繪畫中的色調與音樂中的音調進行了比較,他甚至曾多次說過,一部以繪畫開始的作品可以以音樂來結束[5],并力圖在繪畫作品中體現繪畫的音樂性一面。
德拉克洛瓦最成功的繪畫作品之一是取材于《哈姆雷特》的《奧菲麗婭之死》第三版(圖8)。奧菲麗婭是莎士比亞的這部名劇中的悲劇人物,她在遭遇嚴重的精神打擊后神志不清。畫家選擇的是奧菲麗婭失足落水后掙扎的情景,除了題材本身具有的悲劇性以外,了無生氣的水面與不可見的天空更大大提升了畫面的悲傷氣氛。該作品在技巧與美學上都體現出現代性特征,其具暗示性的大筆觸、光線的變化、各元素之間都達到了高度的和諧—。德拉克洛瓦稱之為“音畫”。
德拉克洛瓦作品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在于他將色彩(音響色彩/造型藝術色彩)、節奏與線條的張力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其產生了令人感動、震撼的藝術效果。他以色彩學為主線,對聽覺藝術與視覺藝術的跨學科思辨,反映了他對突破常規、探索新領域的熱衷,也反映了他對和諧、理性的熱愛,二者之間產生的矛盾沖突賦予他的作品以獨特的力量。
(七)康定斯基的調性明度色彩伴音論
瓦西里·康定斯基作為第一位純抽象畫家、抽象藝術的創始人,一生傾心于挖掘、探索音樂和視覺藝術的內在聯系。
不同的色彩其伴音也有所不同,色相會傳達出歡快或悲傷的視覺感受,其畫面所傳達出的情感色彩也會不同。作為色彩繪畫大師兼音樂家的康定斯基將色彩的明度與音樂的跨度相類比,認為色彩與音樂調性具有相似的色相和明度。如,樂器中音色清脆昂揚的小號,其高音明度最高,音調就相對最高;而聲音較為悠長深遠的低音提琴,其低音明度最低,音調就相對最低。若將聲音清亮的女高音與低沉的男低音比作畫作的話,女高音呈現出來的色彩是高調的,男低音呈現出的色彩則是低調色彩。康定斯基還將樂器的音色與色彩的色相、明度、情感相比較聯系:小號是紅色的,給人清脆、響亮、昂揚的感覺;提琴是深紅色的,給人悠長、細膩、舒緩的感受;而女低音和擁有舒緩悠長音域的小提琴則是橙色的。
康定斯基作品中有一種音樂般的節奏和調性,能“看見”那些看不見的宇宙琴弦上發出的各種高低音、伴音甚至合聲。宇宙具有泛音性,泛音是一種自然物理現象,也是宇宙能量場的一種特性。泛音滲透于整個宇宙,只要有一個音奏響,除了整體振動的發聲體,其部分也將振動,從而產生了一系列的自然諧波。康定斯基利用各種幾何化的形態、絕對漂亮的色彩和線條,揭開了宇宙泛音的神秘面紗(圖9)。
(八)梵高的“熱抽象”色彩與“動態音樂”調性說
梵高說:“為什么相對于畫家,我更理解音樂家?為什么在音樂中,我看到了更多的抽象理念?”他還更進一步提出:“繪畫如果更加超然,如果具有更強的音樂性、更弱的造型性,繪畫中的色彩就能得到更好的發揮。”梵高對色彩與音樂調性有著自己的認識與追求。他的畫作色彩感濃重熱烈,其較為活潑的色調帶給人高昂明快的視覺感受,他注重色彩所表達出的氛圍感和情緒感,畫面具有很強的音樂律動性,表現出熱烈、明快的音樂調性,構成一種“熱抽象”的“動態音樂”(圖10)。
(九)克利的個人主義感性樂調色彩想象說
作為集繪畫大師與音樂家于一身的保羅·克利,其作品特點相對較感性(相對于康定斯基),想象力豐富。他的畫面充滿夢幻的色調,色彩完全來源于他的靈感、記憶與情感流露,從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感性之聲,如同一場個人音樂會。克利繪畫作品中的色彩是一種抽象的語言,它們如同音樂中的旋律直接表達了人們的內心感受。其色彩象征帶來了音樂藝術的重要影響,也表現了音樂藝術的內涵和主題。視覺和音樂的共通性,帶給人們的不一樣的心靈震撼(圖11)。
(十)蒙德里安的“冷抽象”色彩構成下的“靜態音樂”調性說
彼埃·蒙德里安的純造型構成屬于一種“靜態音樂”,也可以說更接近于邏輯與理論處理的“冷抽象”。短小的黃、紅、藍小方塊,被看似隨意又合理地安排列起來,沒有琴弦,跳動的樂符卻躍然紙上,溫暖的、跳躍的、變換的……盡管畫面是理性靜態的,但種種音樂所能表達的情感都被蒙德里安用他那冷抽象色彩下的格子和方塊表達出來,所表現出的調性明快、雀躍,每一個聲部都干脆利落、干凈純粹(圖12)。
(十一)德勞奈的抽象色彩與音調律動構成下的“音樂主義繪畫”說
隨著繪畫藝術的發展,不少畫家開始有意識地追求繪畫中的“音樂性”。索尼亞·德勞奈將抽象造型與色彩和音調韻律相結合來體現畫面律動感,被稱為音樂主義繪畫(圖13)。現代繪畫著重強調構成要素的表達涵義,其音樂情感表達也在逐漸增多,憂傷或愉悅的感覺、靜謐或活躍的情緒不再通過藝術家畫筆下的高超技巧來體現,而是利用點線面搭配、色彩構成以及與調子相聯系,從而表達出不一樣的音樂律動的畫面感,帶給人不一樣的視覺美感。
二、社會語境下的音樂調性色彩聯覺三環制約模式
根據對以上代表人物及其理論的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音樂調性與色彩聯覺現象的內因結構由三個中心環節構成:(1)個人主觀激發(聯覺現象的激發環節)-調性個人主義化;(2)社會心理(社會心理定勢)-不同背景環境下的社會心理影響調性;(3)音樂調性結構(作品的藝術結構)-調性音高不同產生的色彩感覺不同。
如果我們用A表示個人主觀激發-調性個人主義化、B表示社會心理-不同背景環境下的社會心理影響調性、C表示音樂調性結構-調性音高不同產生的色彩感覺不同,就可以制定出如圖14中的音樂流行模式中A、B、C三個環節的相互制約圖。該圖可歸納為五種圖示,為此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A、B、C三者相關而形成的流形現象:
圖14中的圖示(a)是A、B、C兩個圓相交,它們的圓心趨向于重合。A、B、C三圓心靠得越近甚至重合,調性色彩在社會的風靡與反響越大,共振效應就越強。這也許就是音樂作曲家、表演者與聽眾心心相印、與時代合拍和同步的道理。
圖示(b)是A、B、C三圓心遠離的例子。在這種情況下,不具備聯覺效應。盡管A把作品指向社會,但A、B并不相關,即A產生的作品并未滿足某一部分或全部社會群體的某項社會定勢。而且C的結構與B需求相去甚遠,A的行為活動不佳。
圖示(c)、(d)、(e)中,盡管分別有兩圓相交,但遠離第三個圓心,說明調性與色彩聯覺模式效應中三個環節缺一不可的本質。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具有聯覺效應。因為聯覺激發者盡管顧及對象的心理定勢(A、B相交),但作品不具備特定的內部結構和強化這種心理定勢的內容表現,因此不具備聯覺關系,如圖示(c);聯覺激發者盡管積極向社會傳播作品(A、C相交),但激發者A根本不考慮社會需求,而且作品的內容表現和藝術結構不為社會聽眾所需要,為此也不具備聯覺效應,如圖示(d);社會需求和對應的作品是一個虛幻的理想結合,激發環節沒有工作,沒有任何聯覺現象產生,如圖示(e)。
在音樂調性與色彩的聯覺現象中,A(個人主觀激發-調性個人主義化)、B(社會心理-不同背景環境下的社會心理影響調性)、C(音樂調性結構-調性音高不同善生的色彩感覺不同)三個環節的圓心越近,人們對音樂調性的色彩共鳴越強;三個圓心重合,社會反響及共鳴可以達到最大值。
三、音樂調性色彩的評價與展望
(一)音樂調性色彩聯覺現象所面臨的問題
很多音樂學者對“色彩音樂”不抱樂觀的看法,因為利用計算機將“色音類比轉換”后的色彩無法表達音樂的思想、情緒、境界和形象的全部,限制了人的審美思維。它可以作為音樂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但不能視為主流藝術。
(二)音樂調性色彩聯覺的積極意義與展望
隨著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精神生活的追求越來越多。音樂調性與色彩的聯覺作為一種感性認知,在個人與社會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筆者從設計社會學的角度通過研究音樂調性與色彩的聯覺,進一步揭示音樂調性色彩的規律特征,以增強個人與社會對音樂調性色彩聯覺的重視,明確聯覺感在個人與社會中的重要地位,發掘了感性認知對于人與社會的積極意義和作用,開拓音樂調性與色彩的研究新領域,完善音樂調性與色彩聯覺模式特征的研究系統,這對于調性色彩與意義的構建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同時,音樂調性與色彩聯覺模式特征的研究又可以反過來促進音樂學科、色彩學科對音樂與色彩互通性及內在關聯的研究,為今后的學術研究提供色彩依據。
參考文獻:
[1]喬惟進.里姆斯基——科薩科夫作品中的色彩性和聲手法及其象形表現[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1988(1).
[2]桑桐.半音化的歷史演進(九)[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
[3]趙京封.德彪西調技法研究[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2).
[4]李遵鋼.浪漫派最后雙杰的調性游移手法[M].齊魯藝苑,2010(3).
[5]李征.火花:西方浪漫主義時期音樂、繪畫、建筑之間的碰撞與聯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