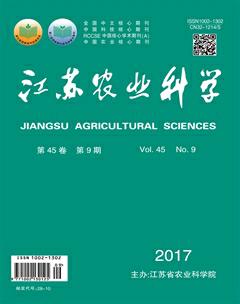基于熵值法的中國省域耕地生態安全評價
李根++楊慶媛++馬寅華++羅明++陳展圖++童小容



摘要: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是改善農田生態系統、促進耕地可持續利用的基礎性工作。根據耕地資源生態安全內涵及其影響因素,從自然、社會、經濟3個方面選取17個指標,構建了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選擇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并運用綜合評價模型計算全國省域單位2005—2014年的耕地生態安全指數,劃分耕地生態安全等級。結果表明:近10年來全國總體耕地生態安全等級由“臨界安全”逐步轉變為“較不安全”,耕地生態安全指數整體呈波動下降態勢,耕地生態安全朝逆向演化的方向發展。北京市、上海市近10年耕地生態安全相對穩定,且基本處于“較安全”等級;2006—2014年天津市耕地生態安全等級經歷“較安全—臨界安全”的變化,但在2012年后有明顯提升;2006—2014年吉林、黑龍江耕地生態安全明顯呈下降態勢,大致經歷了“臨界安全—較不安全—臨界安全”的演變歷程;近10年江蘇、浙江、新疆、西藏、內蒙古、海南地區耕地生態安全相對穩定,處于“臨界安全”;云南、貴州、廣西地區耕地生態安全指數呈波動上升趨勢,但也處于“不安全”等級;其他地區近10年耕地生態安全總體上雖然小有波動,但一直處于“較不安全”等級。
關鍵詞:耕地生態安全;安全等級;熵值法;綜合評價
中圖分類號: F323.211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09-0223-05
耕地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最寶貴的物質基礎,是地球資源的精華所在,我國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1-2]。然而近半個世紀以來,由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建設用地占用以及災害毀壞,耕地資源的稀缺性增強,耕地的生態安全受到極大威脅[3-5]。因此,診斷區域耕地生態安全等級、加強耕地生態安全建設顯得尤為重要。
國外學者主要把耕地生態安全與可持續利用相結合進行研究,Rasul等從自然生態環境、社會經濟需求方面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分析孟加拉耕地可持續利用與自然生態狀況[6]。Beesley等認為,農用地利用中,耕地的質量與生態安全越來越受農場主關注[7]。國內學者關于耕地生態安全的研究集中在耕地生態安全內涵、耕地生態安全評價、耕地生態安全影響因素以及耕地生態安全調控對策等[2,8-9]。朱紅波在分析耕地資源生態安全內涵、特征和影響因素的基礎上,構建了耕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認為耕地資源生態安全是指在一定時間和空間尺度內,耕地資源生態系統處于保持自身正常功能結構和滿足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的狀態[2]。趙其國等分別從耕地利用內外部環境及耕地供給方面探討了耕地生態安全,但是由于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人們對耕地生態安全的內涵認識不足,在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和研究方法選擇上形成的共識多為宏觀研究,使得耕地生態安全評價研究滯后[10]。筆者以全國為研究區域,以省域為研究單元,構建基于壓力-狀態-響應(PSR)模型的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綜合評價法和熵值法對我國耕地生態安全進行實證研究,識別并診斷耕地生態安全的制約因子,旨在為改善農田生態系統安全狀況、協調人地關系、促進耕地資源可持續利用提供理論依據。
1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1.1耕地生態安全的內涵
筆者認為,耕地生態安全是土地生態安全的一個重要方向,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含義:(1)它是實現耕地與自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與基礎;(2)它是耕地資源環境和生物環境所處的不受或少受威脅的可持續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耕地生態系統有均衡、充裕、穩定的自然資源可供利用;(3)指在一定時間和空間尺度內,耕地生態系統既能實現自身結構功能的完整,又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10]。
1.2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我國實際情況,結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10-16],遵循科學性、可比性、系統性、可獲取性原則,基于壓力-狀態-響應(PSR)模型,綜合考慮自然壓力、環境壓力、人口壓力、社會經濟壓力、耕地質量、耕地資源狀態、環境響應等7個方面影響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的因素,選取17個評價指標為指標層,構建了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表1)。
2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方法與模型
2.1數據來源與標準化處理
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國土資源年鑒》《中國農業年鑒》《中國國[CM(25]土資源公報》和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以下簡稱省市自治區)統計年鑒。由于數據的可獲取限制性,本研究只對2005—2014年我國耕地生態安全水平進行分析。
本研究構建的指標體系對耕地生態安全的影響分為正、負趨向性2個方面。正向性指標是數值越大,對耕地生態安全越有利;負向指標是數值越小,對耕地生態安全越有利。在獲取原始數據后,需對正、負趨向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具體步驟如下:
式中:Xij指第i指標第j省(市、自治區)的原始值;max(Xij)指第i指標第j省(市、自治區)的最大值;min(Xij)指第i指標第j省(市、自治區)的最小值;Zij指第i指標第j省(市、自治區)標準化后的值。
2.2指標權重確定
不同的評價指標對耕地生態安全的重要程度存在一定差異,為了反映這一差異,需要對不同的指標賦予權重,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主要有主觀賦權法與客觀賦權法兩大類。為了避免人為主觀判斷的影響,使得出的耕地生態安全權重更有科學性,本研究選取客觀賦權法里的熵值法來確定指標權重。熵值法根據評價指標變異程度的大小來確定指標權重,指標變異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少,該指標權重值就越大,反之越小[15-17]。
根據公式(1)、(2)得出的標準化值,再計算第i指標第j省(市、自治區)的比重Yij:
計算第i項評價指標的信息熵值ei:
式中:ei≥0,k為調節系數,與樣本數m有關,一般令k=1lnm。
計算第i項評價指標的權重wi。
最后,利用熵值法的公式,與均值法相結合,求取全國2005—2014年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權重(表2)。
2.3評價模型
國內學者對生態安全的評價多采用灰色關聯度評價模型、生態足跡評價模型、模糊綜合評價模型等[18-20]。本研究采用綜合評價模型,定量分析中國省域單位耕地生態安全狀況。
式中:Ej為第j省(市、自治區)的耕地生態安全綜合評價指數;wi為指標i的權重;zij為指標i的標準值。
2.4評價標準
借鑒相關文獻的研究結論[21-23],并且考慮到指標選取的局限性,表3將全國耕地生態安全指數值按其取值范圍(0~1),運用非等間距法分為5個安全檔次,指數值越大,耕地生態安全度越高,指數值越小,耕地生態安全度越低;并依次將5個對應的耕地生態安全等級與特征進行相應描述。
3結果與分析
3.1全國各省市自治區耕地生態安全等級劃分
通過收集中國省域相關數據,根據前文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定量計算,得到耕地生態安全評價綜合指數值。由于筆者研究的是2005—2014年中國省域耕地生態安全狀況及動態變化過程,計算量較大,文章篇幅所限,在此省略計算過程。中國省域2005—2014年耕地生態安全綜合指數見表4、表5。
由表4、表5可知,中國省域近10年的耕地生態安全總體水平并不高,全部處于生態安全等級的Ⅱ級到Ⅴ級。其中,北京市、上海市的耕地生態安全等級較高,總體處于Ⅱ級(較安全);云南、貴州、廣西地區的耕地生態安全水平等級較低,近年來波動較小,基本處于Ⅴ級(不安全)。近年來,河北、河南、陜西、山西、江西、山東、安徽、湖北、湖南、福建、遼寧、廣東、四川、重慶、甘肅、青海、寧夏等地耕地生態安全總體處于Ⅳ級(較不安全),江蘇、浙江、天津、內蒙古、吉林、黑龍江、西藏、新疆、海南等地近年來耕地生態安全總體處于Ⅲ級(臨界安全)。2005—2014年中國省域單位耕地生態安全空間分異及耕地生態安全變化分別見圖1、圖2。
收集中國省域單位有關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數據,經分析整理后,按照熵值法確定各評價指標的權重(表2),將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數據帶入綜合評價模型,計算得出中國省域單位2005—2014年的耕地生態安全指數,再運用非等間距法將耕地生態安全指數分為5個安全等級。生態安全指數越大,耕地生態安全度越高;生態安全指數越小,耕地生態安全度越低。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地區近10年耕地生態安全指數穩定,達到“較安全”等級,處于國內領先位置。江蘇、浙江、天津、山東、內蒙古、吉林、黑龍江、西藏、新疆、海南等地近10年耕地生態安全指數波動明顯,但基本處于“臨界安全”等級。其中,2006—2014年天津市耕地生態安全等級經歷“較安全—臨界安全”的變化,2012年后耕地生態安全指數有明顯提升;2006—2014年吉林、黑龍江地區耕地生態安全指數呈明顯下降態勢,大致經歷了“臨界安全—較不安全—臨界安全”的演變歷程。河北、河南、陜西、山西、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福建、遼寧、廣東、四川、重慶、甘肅、青海、寧夏等地近10年耕地生態安全指數總體稍有波動,基本處于“較不安全”等級;其中,2006—2012年遼寧省耕地生態安全指數波動明顯,由“臨界安全”下降為“較不安全”,2012年后稍有回升。近10年陜西省耕地生態安全指數總體由“不安全”等級提升到“較不安全”等級,到2014年又稍有回落,下降為“不安全等級”。云南、貴州、廣西地區的耕地生態安全指數波動較小,基本處于“不安全”等級。其中,2005—2007年廣西耕地生態安全指數經歷了“較不安全—不安全”的演變歷程,且之后幾年一直處于“不安全”等級。
4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通過對中國省域2005—2014年的耕地生態安全進行分析與評價,結果表明,近10年全國總體耕地生態安全等級由“臨界安全”逐步轉變為“較不安全”,耕地生態安全指數整體呈波動下降態勢,耕地生態安全朝逆向演化的方向發展。
近年,中國省域耕地生態安全發展態勢未得到根本性轉變,這與城市化的快速擴張、人口快速增長、工業迅速發展、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等因素有密切關系。今后,應積極制定應對措施確保全國耕地生態安全,推進人地協調發展與土地可持續利用。本研究結果表明,耕地農藥和化肥負荷、農業機械化水平、自然環境污染程度、人均耕地面積是制約農田生態系統安全狀況改善的關鍵因素。因此,須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提倡農業技術創新,適地適量施用農藥、地膜、化肥,減少對耕地資源的污染;積極開展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加強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增加有效耕地,提升耕地資源質量;重視耕地生態環境的建設與中低產田改造,嚴格控制建設用地占用耕地,從根本上解決人為拋荒、侵占和壓損問題,保證耕地數量與質量的平衡,保障糧食安全;合理控制人口增長,使人口規模在土地承載力范圍以內;加強預防災害能力建設,完善并優化防災減災以及抗旱、救災響應結構,建立耕地生態安全預警監測體系,為耕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與管理提供支撐,政府須加大資金投入力度,有效提升耕地生態安全等級。
參考文獻:
[1]張鳳榮,郭力娜,關小克,等. 生態安全觀下耕地后備資源評價指標體系探討[J]. 中國土地科學,2009,23(9):4-8,14.
[2]朱紅波. 我國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的特征與影響因素分析[J]. 農業現代化研究,2008,29(2):194-197.
[3]楊慶媛,周滔,張鵬飛,等. 耕地保護社會約束機制建設探討[J]. 創新,2010(4):60-64.
[4]吳大放,劉艷艷,劉毅華,等. 耕地生態安全評價展望[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15,23(3):257-267.
[5]付國珍,擺萬奇. 耕地質量評價研究進展及發展趨勢[J]. 資源科學,2015,37(2):226-236.
[6]Rasul G,Thapa G B.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of ecological and conven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s in Bangladesh[J]. World Development,2003,31(10):1721-1741.
[7]Beesley K,Ramsey D. Agricultural land preservatio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M]. Oxford:Elsevier Press,2009:65-69.
[8]張傳華. 耕地生態安全評價研究[D]. 重慶:西南大學,2006.
[9]徐輝,雷國平,崔登攀,等. 耕地生態安全評價研究:以黑龍江寧安市為例[J]. 水土保持研究,2011,18(6):180-184.
[10]趙其國,周炳中,楊浩,等. 中國耕地資源安全問題及相關對策思考[J]. 土壤,2002(6):293-302.
[11]郝軍,蘇根成,鄔文艷. 內蒙古耕地資源安全評價[J]. 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8,37(4):558-561.
[12]張銳,鄭華偉,劉友兆. 基于PSR模型的耕地生態安全物元分析評價[J]. 生態學報,2013,33(16):5090-5100.
[13]左曉英. 基于PSR模型的耕地生態安全評價[D]. 保定:河北農業大學,2014.
[14]余敦,陳文波. 潘陽湖生態經濟區土地生態安全研究[J]. 水土保持研究,2011,18(4):107-111.
[15]吳曉. 山峽庫區重慶東段生態安全評價研究[D]. 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4.
[16]易軍,梅昀. 基于PSR框架的耕地集約利用及其驅動研究:江西省為例[J]. 干旱區流域資源與環境,2010,19(8):895-900.
[17]張銳,劉友兆. 我國耕地生態安全評價及障礙因子診斷[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3,22(7):945-951.
[18]鄭華偉,劉友兆,王希睿. 中國城鎮化與土地集約利用關系的動態計量分析[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1,20(9):1029-1034.
[19]陶曉燕,章仁俊,徐輝,等. 基于改進熵值法的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評價[J].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6,20(5):38-41.
[20]胡永宏,賀思輝. 綜合評價方法[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21]伍恒雨. 基于熵權物元模型的萬州區土地生態安全評價研究[D]. 重慶:西南大學,2015.
[22]崔明哲,楊鳳海,李佳. 基于組合賦權法的哈爾濱市耕地生態安全評價[J]. 水土保持研究,2012,19(6):184-192.
[23]文森,邱道持,楊慶媛,等. 耕地資源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 農業資源與環境科學,2007,23(8):466-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