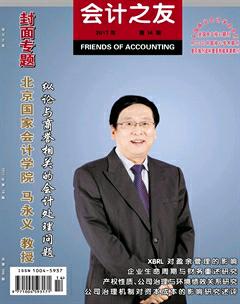企業生命周期與財務重述研究
蔣堯明++賴妍


【摘 要】 文章選取2010—2015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了生命周期對財務重述的影響。研究發現:生命周期與財務重述關系顯著;相比成熟期和衰退期企業,成長期企業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更高,偏向滯后重述。結論對監管部門規范財務重述行為和凈化證券市場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作用。
【關鍵詞】 生命周期; 財務重述; 上市公司
【中圖分類號】 F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14-0008-05
一、引言
財務重述是上市公司修正前期財務報告以反映這些報告中的差錯被更正的過程(FASB,2005)。目前我國上市公司財務重述現象日漸頻繁,2010—2015年上市公司重述總數達3 157次,由2010年的224次上升到2015年的430次,帶來了一系列的經濟后果,包括對股價產生負的市場反應[ 1-4 ]、股價崩盤風險明顯更高[ 5 ]、引致集體訴訟等[ 6 ],嚴重影響了資本市場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2016年12月,為進一步規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為,證監會修訂了《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第3號和《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3號。減少財務重述的發生,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成為國家和社會密切關注的課題。
企業生命周期理論指出: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企業面臨不同的發展需求以及內外部環境特點,這會導致企業不同的戰略決策意圖和行為傾向[ 7 ]。當財務報告基于會計、法律、技術等問題而存在錯誤或誤導性信息時,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業將如何作出財務重述決策,當期重述還是滯后重述?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已有關于企業生命周期的研究較多,但從企業生命周期這一動態視角探討與財務重述關系的研究較少,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機。因此,本文以2010—2015年在我國滬深兩市上市的A股數據為基礎,實證檢驗企業生命周期與財務重述的關系。
二、文獻回顧
時至今日,在剖析財務重述的原因時,大多數學者認為是管理層迫于資本市場的壓力和自利行為的滿足而進行盈余操縱引致的。Richardson et al.研究發現,迫于資本市場的壓力,上市公司管理層有動機進行盈余操縱以維持盈利增長或超過預期的盈利,而為達到上述目的采取激進的會計政策最終導致了更頻繁的財務重述[ 8 ]。喻焱文認為上市公司財務重述的基本動因是調整盈利水平,具體動因表現可以劃分為收入、成本費用、非經常性損益等其他變化[ 9 ]。Lev更是將財務重述作為管理層盈余操縱行為的表征[ 10 ]。曹強的觀點有所不同,認為公司內部控制缺陷是財務重述產生的最主要原因,其他的原因還包括管理層的盈余操縱、準則的模糊性和業務的復雜性[ 11 ]。
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由Mason Haire首先提出,認為可以用生物學中的生命周期觀點看待企業,企業的發展符合生物學中的成長曲線。70年代后學者們以企業組織行為(組織結構、管理風格、控制行為等)、與企業價值相關的會計指標兩方面作為企業生命周期劃分依據[ 12 ],展開了一系列的規范研究,提出了20余種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方法,從3階段到10階段不等。隨后企業生命周期理論拓展到投融資[ 13 ]、盈余管理[ 14 ]、企業績效[ 15 ]、公司治理[ 16 ]等實證研究領域。關于企業生命周期的度量方法有Dickinson的現金流量組合法,任佩瑜的管理熵法和范從來的產業經濟學增長率分類法等。迄今為止,上述哪一種度量方法更為合理和準確尚未定論,但一致認同企業需經歷孕育、成長、成熟、衰退或再發展等階段,每個階段具有顯著不同的特征。
通過已有文獻回顧,筆者發現尚未有直接揭示生命周期和財務重述關系的文獻,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本文可能的創新點在于:(1)引入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將其與財務重述研究相結合,拓展了財務重述相關問題的研究視角;(2)借鑒已有學者對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方法,分為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②。本文從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出發,動態分析了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下財務重述決策的差異,豐富了生命周期和財務重述的相關研究。
三、理論分析和假設提出
(一)企業生命周期與財務重述
王毅輝等認為財務重述是對存在錯誤或誤導性信息的歷史財務報告進行事后補救的公告行為[ 17 ]。財務重述是否發生及當期或滯后重述的決策都與企業所處的內外部環境密切相關。企業如同生命體一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體現不同的特征。成長期企業發展速度較快,有較多的投資機會和擴大生產規模的需要,但現金流和人才儲備嚴重不足,這時公司治理機制逐步建立,并處于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成熟期企業盈利水平達到高峰但增速放緩,面臨的市場趨于飽和,競爭更為激烈,但公司治理機制趨于成熟,對外界人才的吸引力不斷增強。衰退期企業的市場份額逐漸萎縮,產品失去競爭力,人才流失較為嚴重,如果不積極轉型、研發創新,將會被其他企業搶走市場份額,無法持續經營甚至面臨破產清算。企業生命周期各階段公司治理特征、財務特征和人才儲備方面的差異如同一雙無形的巨手,始終左右著企業的財務重述決策。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
H1:企業生命周期與財務重述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二)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與財務重述
處于成長期的企業,相比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業而言,在公司治理特征、財務特征和人才儲備方面存在顯著差異:(1)公司治理機制處于逐步建立的過程中。董事會和監事會的作用無法正常發揮以完全牽制管理層,甚至凌駕于公司治理層之上。基于職業防御和既得利益的需要,更有動機進行應計或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行為。周沖實證研究發現成長期比成熟期企業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 14 ]。前已述及,由于收入確認不恰當、成本費用不真實等原因可能導致財務重述,而上述行為實質是企業為實現盈余管理而運用的具體方式。(2)強烈的投資需求與有限的籌資能力并存。成長期企業雖然在獲利能力方面逐步增強,但明顯滯后于收入的增長,存在較大的資金缺口。而投資者或債權人因成長期企業風險較高往往會設定許多約束性條款,制約了融資的便利性。黃宏斌等通過實證檢驗發現成長期企業相比成熟和衰退期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更大[ 13 ]。管理層可能篡改財務數據以實現成功融資,導致財務報告存在差錯或誤導性信息,進而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更高。(3)急劇的人才需求與人才頻繁流動并存。成長期企業發展速度較快,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對人才的需求急劇攀升,但是配套的薪酬、晉升激勵體制滯后,造成人才的流動頻繁,儲備不足。尤其以原則為導向的新會計準則中隱性知識比重的提高[ 18 ],對企業會計人才的職業判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職業判斷出現偏差,差錯或誤導性信息將相伴而生,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提高。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
H2:與成熟期和衰退期企業相比,成長期企業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更高。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2010—2015年在我國滬深兩市上市的A股公司數據作為初始樣本。在獲得初始樣本后,依據以下標準進行了篩選:(1)剔除ST、*ST類特殊處理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3)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公司;(4)剔除2010—2015年未一直存續的企業。經過上述處理后,獲得6 096個平衡面板數據。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資料,通過DIB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數據庫中的財務重述庫查詢獲取;其他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或手工計算整理而得。數據處理上主要使用Stata12.0軟件。為了克服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連續變量按照前后各1%進行了Winsorize縮尾處理。
(二)模型設計與變量定義
模型(1)—(4)中的被解釋變量為財務重述RESTATE,表示上市公司當年是否發生了財務重述行為。由于DIB的財務重述庫有明確的財務重述公告日期,所以不需要將財務重述的數據滯后一期。
模型(1)中的解釋變量為LC,表示公司所屬的生命周期階段。當公司屬于成長期時LC=1,屬于成熟期時LC=2,屬于衰退期時LC=3。生命周期階段的劃分借鑒范從來等[ 15 ]的研究采用產業經濟學增長率分類法將上市公司所處生命周期大致劃分為成長階段、成熟階段和衰退階段。將2010—2015年分為2010—2012年和2013—2015年兩個相鄰的時期,比較企業在兩個相鄰時期的增長率與相應時期所屬行業的增長率。如果該企業的增長率(以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表示,下同)在兩個時期均高于行業平均增長率(以行業平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表示,下同),則為成長企業;如果前一時期大體接近于行業平均增長率,而在后一時期大大高于行業平均增長率,也為成長企業;如果在前一時期高于行業平均增長率,而在后一時期逐漸低于行業平均增長率,則為成熟企業;如果兩個相鄰時期的增長率均低于行業平均增長率,則為衰退企業。利用上述方法,將1 016家上市公司進行劃分后,處于成長期的有278家,成熟期的有242家,衰退期的有496家。
模型(2)—(4)分別考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對財務重述的影響是否顯著。當公司處于成長期時GS=1,否則GS=0;當公司處于成熟期時MS=1,否則MS=0;當公司處于衰退期時DS=1,否則DS=0。
此外,為了更好地測試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本文還借鑒已有學者的研究成果,所有模型都考慮財務杠桿(LEV)、公司規模(SIZE)、盈利能力(ROA)、股權集中度(TOP)、總資產周轉率(TURNOVER)、控制人性質(STATE)、行業(INDUSTRY)和年度(YEAR)控制變量。各變量定義見表1。
五、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為描述性統計結果。由表2可知,在2010—2015年這6年中,處于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業各占27.4%、23.8%和48.8%,衰退期企業數量接近一半。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概率為16.3%。控制變量方面,資產規模(取對數后)的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22.101和1.291,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發展不均衡;資產負債率平均為48.9%,說明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較強;總資產凈利率最高為21.1%,最低的為負數,說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普遍不高;總資產周轉率最高為2.701,最低為0.062,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業特點;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最高為74.3%,最低為8.8%,說明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相差較大;控制人性質的均值為0.541,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超過了半數。
(二)相關分析
表3報告了各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從表3可以看出,生命周期與財務重述在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初步表明生命周期與財務重述關系越顯著,成長期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越大。在控制變量方面,財務杠桿與財務重述顯著正相關,資產規模、盈利能力、總資產周轉率和股權集中度與財務重述顯著負相關,控制人性質與財務重述不相關。
(三)回歸結果分析
筆者利用模型(1)對生命周期與財務重述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為了更好地考察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對財務重述行為的影響,將生命周期的三個不同階段分別放入模型(2)—(4)中進行回歸,結果見表4。
表4中的(1)顯示,生命周期與財務重述顯著負相關,假設1得到驗證;(2)—(4)顯示,GS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與成熟期和衰退期企業相比,成長期企業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更高,假設2得到驗證。
控制變量方面,資產規模、總資產周轉率和股權集中度與財務重述顯著負相關。財務杠桿與財務重述顯著正相關,這與何威風的研究一致。總資產凈利率和控制人性質對財務重述影響不顯著。
六、穩健性測試
為進一步檢驗結果的可靠性,將被解釋變量財務重述用當期或滯后重述替代,當期重述取值為1,滯后重述取值為2,未發生則取值為0,對上述理論假設的檢驗結果進行了穩健性測試。總體上不改變本文的主要結論,成長期企業偏向滯后重述,結果見表5。
七、結論
本文選取2010—2015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了生命周期對財務重述的影響。研究發現:(1)生命周期對財務重述的影響顯著,兩者顯著負相關。(2)進一步將生命周期劃分為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結果顯示,成長期對財務重述的影響顯著。穩健性測試的結果表明,對于財務報告存在的差錯或誤導性信息,成長期企業偏向滯后重述而不是當期重述。可能的原因有:公司治理機制不健全,董事會和監事會無法有效牽制管理層,導致管理層權力過大。管理層一方面出于自身職業防御和既得利益的需要,擔心重述后影響薪酬和晉升;另一方面出于成長期企業利益的需要,擔心重述后導致融資失敗,因而推后財務重述的時間。
本文依據結論提出以下建議:(1)作為成長期企業,應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機制,規范管理層的經營行為。尤其是針對管理層權力過大的企業,為了避免機會主義傾向,可以實施股權激勵,使得管理層和股東的利益趨于一致,更好地為企業服務。(2)證監會一方面應重點加強對成長期企業的監管,提高其財務信息披露質量,保護投資者利益;另一方面應及時修訂信息披露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加大對故意隱瞞差錯或遺漏公司的處罰力度,提高違規成本,從而達到凈化證券市場,促進財務資金合理配置的目的。
【參考文獻】
[1] PALMROSE ZV,RICHARDSON VJ,SCHOLZ S. Determinants of market reactions to restatement announcement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4,37(1):59-89.
[2] SCHOLZ S.The changing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company financial restatements[R].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Reporting,2008.
[3] 朱朝暉,胡成偉,黃峰.上市公司年報財務重述的市場反應的統計檢驗[J].統計與決策,2012(8):160-163.
[4] 應可慧,董林蔚,胡鑫紅.我國上市公司財務重述對股價影響的實證分析[J].財經論叢,2015(3):66-73.
[5] 謝盛紋,廖佳.財務重述、管理層權力與股價崩盤風險: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7(1):80-87.
[6] LEV B, RYAN SG,WU M. Rewriting earnings history[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8,13(4):419-451.
[7] 楊林.公司股權結構、高管團隊認知多樣性與創業戰略導向關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5):93-106.
[8] RICHARDSON S,TUNA I,WU M.Capital market pressur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the case of earnings restatements[R].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3.
[9] 喻焱文.上市公司財務重述的強度、動因及影響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4(14):163-165.
[10] LEV B. Corporate earnings: facts and fic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3,17(2):27-50.
[11] 曹強.中國上市公司財務重述原因分析[J].經濟管理,2010(10):119-126.
[12] 曹裕,陳曉紅,王傅強.我國上市公司生命周期劃分方法實證比較研究[J].系統管理學報,2010(3):313-322.
[13] 黃宏斌,翟淑萍,陳靜楠.企業生命周期、融資方式與融資約束:基于投資者情緒調節效應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6(7):96-112.
[14] 周沖.不同成長階段下企業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5(11):182-185.
[15] 范從來,袁靜.成長性、成熟性和衰退性產業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的實證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2(8):65-72.
[16] 李云鶴,李湛,唐松蓮.企業生命周期、公司治理與公司資本配置效率[J].南開管理評論,2011(3):110-121.
[17] 王毅輝,魏志華.財務重述研究述評[J].證券市場導報,2008(3):55-60.
[18] 李剛,劉浩,徐華新,等.原則導向、隱性知識與會計準則的有效執行:從會計信息生產者的角度[J].會計研究,2011(6):17-24,95.
[19] 何威風,劉啟亮.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與財務重述行為研究[J].管理世界,2010(7):14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