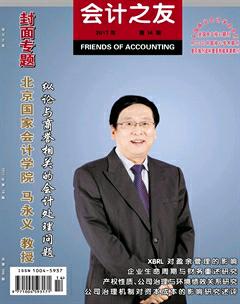企業(yè)異質性、人力資本結構與全要素生產率


【摘 要】 人力資本結構是決定全要素生產率的核心因素,為了實證檢驗企業(yè)異質性條件下人力資本結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制約與促進,文章以我國1995—2014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為基礎,通過人力資本模型的構建,將人力資本分為四個類別,考查企業(yè)異質性、人力資本結構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國有企業(yè)、高新技術企業(yè)、出口類型企業(yè)中,人力資本投資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更高;四個維度的人力資本中,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顯著促進效應的是知識人力資本、技能人力資本、基礎人力資本的積累,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明顯制約效應的是制度人力資本積累。最后依據實證分析結果,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企業(yè)異質性; 人力資本; 全要素生產率
【中圖分類號】 F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14-0017-05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經濟正處于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勞動力供給面臨新的結構調整,隨著勞動力供給“劉易斯拐點”到來,支撐中國經濟多年發(fā)展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口素質的提高及人力資本質量的改善,已成為我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xiàn)經濟有質量、穩(wěn)健、均衡發(fā)展的必要條件[ 1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對企業(yè)異質性、人力資本投資結構與全要素生產率關系研究的理論基礎,新經濟增長理論主要將技術進步內生到經濟增長率中,將人力資本從資本和勞動生產要素中分離出來。這樣,人力資本的積累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容易衡量。
隨著我國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無論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絕對量還是相對量都迅速增加,人力資本存量大幅提高,生產要素中人力資本投入比重提高。特別是20世紀末,伴隨著高校合并的浪潮,高校大規(guī)模擴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現(xiàn)倍數增長,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兩年。依據統(tǒng)計局官方數據,截至2014年,我國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已經超過1.2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9%,從事科技研發(fā)工作的人員規(guī)模僅次于美國,超過700萬人。從國民經濟核算來看,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技術效率與技術進步顯著提升,經濟增長中科技含量大幅提升,經濟增長從依賴于生產要素投入逐漸轉變?yōu)橐揽咳厣a率提高驅動[ 2 ]。但與歐美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國GDP中科技含量還是偏低。歐美等發(fā)達國家GDP中科技含量已經超過70%,而我國GDP中科技含量不到40%。
企業(yè)異質性、人力資本結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通過對以往學者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發(fā)現(xiàn),現(xiàn)有研究基礎數據對人力資本投資多體現(xiàn)在勞動力受教育年限也就是受教育水平上,較少涉及人力資本結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通過前述分析可知,受教育年限或受教育程度無法全面反映企業(yè)人力資本質量以及結構對全要素的影響[ 3 ]。另外,國內的諸多學者沒有從多角度來考察不同類型企業(yè)人力資本結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與制約,也沒有從不同維度的人力資本對不同企業(yè)類型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與效應進行分析。本文在我國1995—2014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基礎上,從人力資本的四個維度——基礎人力資本、知識人力資本、技能人力資本、制度人力資本深入研究它們對不同類型企業(yè)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并深入考察中國不同類型企業(yè)人力資本投資結構對全要素生產率影響有何差別。上述問題的研究,對中國企業(yè)改善人力資本投入結構,提高人力資本質量,加快實現(xiàn)經濟轉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一定的理論與政策指導意義。
二、選擇變量與設定模型
(一)設定計量模型
式(5)衡量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主要測度了實際生產前沿面與最佳生產前沿面之間的差距:如果數值比1大,說明技術進步或技術效率提高;這時全要素生產率是提高的;等于1說明技術進步或技術效率基本沒發(fā)生變化,表示全要素生產率是降低的;比1小,說明技術無效率。
核心解釋變量(hucit)。人力資本核心解釋變量主要由四部分組成:(1)基礎人力資本huc1,通過《中國統(tǒng)計年鑒》的查詢,找出人均健康醫(yī)療支出指標;(2)知識人力資本huc2,通過人均受教育年限來計算;(3)技能人力資本huc3:主要以《中國勞動統(tǒng)計年鑒》公布的每年各省技工培訓學校畢業(yè)生數占適齡人口的比重來計算;(4)制度人力資本huc4,用省級單位人口遷移量數量與總人口的比重來計算。
核心解釋變量(en-typeit)。主要包括以下類型:(1)是否為國有企業(yè)(sta-enit);(2)是否為出口企業(yè)(exp-enit);(3)是否為外資企業(yè)(for-enit);(4)是否為加工貿易企業(yè)(pro-enit);(5)是否為高科技企業(yè)(hig-enit)。以上企業(yè)類型變量均為二維變量,取值為1或0。
Xktit控制變量組。按前述分析,對居民收入分配產生作用的數據本文設定如下控制變量:(1)政府規(guī)模(govit);(2)城鎮(zhèn)化水平(urbit);(3)經濟開放度(eoit);(4)利用外資水平(fdiit);(5)人均GDP(rjgdpit)。
2.數據來源
通過選取1995—2014年我國30個省級單位的面板數據,對企業(yè)異質性、人力資本結構、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邏輯關系給予計量檢驗。各省級單位國民生產總值、財政分權、進出口額、固定資產投資、城鎮(zhèn)化水平、總人口數、一般政府預算收入、財政支出、CPI等數據均來自1995—2015年《中國人口年鑒》《中國勞動年鑒》《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以及各個省級單位1995—2015年統(tǒng)計年鑒。刻畫全要素生產率、資本投入、勞動投入等數據主要通過歷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國勞動就業(yè)年鑒》以及各省級單位統(tǒng)計年鑒得出。另外,部分控制變量的數據來源于國家統(tǒng)計局、商務部、發(fā)改委官方網站整理得到。
三、模型的回歸與實證分析
(一)關鍵變量的處理與統(tǒng)計分析結果
表1為變量統(tǒng)計分析結果。因為企業(yè)類型變量為二維向量,沒有做分析。
(二)企業(yè)異質性、人力資本結構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實證分析
在檢驗企業(yè)異質性、人力資本結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之前,為了更好地反映經濟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防止虛假回歸的出現(xiàn),必須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主要選擇IPS檢驗、LLC檢驗以及HT檢驗三種方法,不同的檢驗方法可以更全面地檢驗變量的平穩(wěn)性,保證實證分析的準確性。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平穩(wěn),具體如表2所示。
在對變量的平穩(wěn)性進行檢驗以后,就我國企業(yè)異質性、人力資本結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采用系統(tǒng)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實證檢驗,回歸結果見表3。
表3中(1)—(6)是依據計量模型(2)獲得的實證檢驗結果。通過計量結果可以看出,人力資本投資結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具有很強的企業(yè)異質性。衡量企業(yè)異質性的五個二維變量中,四個變量對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影響,而是否為國有企業(yè)、出口企業(yè)、高新技術企業(yè)三個變量系數為正。這說明,人力資本投資對于企業(yè)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程度在國有企業(yè)、出口企業(yè)、高新技術企業(yè)中的正向效應更強。加工貿易企業(yè)變量前面系數為負,說明人力資本投資在加工貿易類企業(yè)中全要素生產率的正向效應減弱。另外,是否為外資企業(yè)人力資本投資對企業(yè)全要素生產率是否有正向效應影響不顯著。四個維度的人力資本中,基礎人力資本、知識人力資本、技能人力資本三個維度估計系數為正,說明這三個維度的人力資本顯著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技能人力資本估計系數為負,說明技能人力資本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有負向影響作用。從影響的作用程度來看,知識人力資本比基礎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正向促進作用更大,而技能人力資本的正向作用最小。
知識人力資本投資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qū)居民的基本素質。在全社會人均受教育年限比較低的時期,隨著知識人力資本存量的增長,受教育年限越長,全要素生產率會獲得比較大的提高,但隨著一個國家從發(fā)展中國家步入發(fā)達國家的行列,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這時候人力資本存量進入到一個比較高的時期,受教育邊際產出下降,從而導致對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基礎人力資本主要衡量標準是人均健康醫(yī)療支出,這是因為,健康狀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會在代際之間傳遞。隨著人均醫(yī)療健康支出的增加,公民健康狀況提高,這種貧困的代際傳遞性會被切斷,這時候家庭對未來會比較樂觀,傾向于將更多的資源投資于教育,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反過來會反哺家庭,同時也降低了疾病死亡風險對貧困家庭的沖擊作用,形成基礎人力資本積累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良性互動。制度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人口遷移都是一些人力資本比較低的群體,這些群體的人力資本只是配置到一些技術含量相對偏低的行業(yè)或地區(qū),因此制度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沒有發(fā)生正向作用。
控制變量方面,政府規(guī)模、經濟開放度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產生了一定的抑制效應,即政府規(guī)模越大,全社會資源中由政府來支配的越多,經濟越開放,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究其原因主要為科研和技術改造的資金在政府財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偏小,隨著經濟開放度的增加,可能引進的是國外淘汰的技術,國內的自主研發(fā)將受到限制。利用外資水平高低、城鎮(zhèn)化率高低、經濟發(fā)展程度與全要素生產率變量呈正相關關系,即隨著利用外資規(guī)模的增加、城鎮(zhèn)化水平的提高、經濟發(fā)展程度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將會提高。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選取1995—2014年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qū))的面板數據,用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將全要素生產率進行量化,對企業(yè)異質性、人力資本結構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進行計量檢驗,研究結果表明人力資本投資對于企業(yè)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程度在國有企業(yè)、出口企業(yè)、高新技術企業(yè)中的正向效應更強,人力資本投資在加工貿易類企業(yè)中全要素生產率的正向效應在減弱[ 4 ]。另外,人力資本是全要素生產率增大的重要因素。在將我國人力資本分為四個維度的前提下,基礎人力資本、知識人力資本、技能人力資本積累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促進作用,而制度人力資本抑制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本文從以下角度提出政策建議。
第一,增加國民經濟中國有、出口、高新技術三個類型企業(yè)的比重,政府在對經濟引導的過程中,要注重發(fā)展這三個類型的企業(yè)。實際上國有企業(yè)一直是我國技術創(chuàng)新的主力軍,同時也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動力來源,在市場發(fā)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不應該否定國有企業(yè)對技術創(chuàng)新的作用。另外,可以對國有、出口、高新技術三個類型的企業(yè)進行稅收優(yōu)惠和補貼,鼓勵創(chuàng)新能力強的企業(yè)快速發(fā)展。
第二,用增加教育支出的方式來提高人力資本存量。知識人力資本主要來源于人均受教育年限,因此需要增加更多的財政支出來支撐教育支出。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可以為技術外溢的正外部性提供基礎,人力資本存量水平的提高可以促進勞動者對技術進步的吸收能力,這樣全要素生產率就會增加,以致經濟發(fā)展速度會提高,經濟上去了,反過來又有利于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二者之間形成良性互動[ 5 ]。
第三,通過加強區(qū)域內教育公平提升區(qū)域內人力資本的積累能力。在我國當前財政體制下,由省級和中央政府負擔義務教育,重點保障農村等偏遠地區(qū)兒童的入學。同時加大中央政府轉移支付力度,使轉移支付更多向中西部地區(qū)傾斜,增加人力資本的積累,彌補物質資本積累的不平衡。各項增加人力資本存量的轉移支付要直接撥付到縣一級財政,防止過多層級轉移而改變財政資金的用途,地方政府要做到專款專用。對用于教育經費的財政支出要公開,使社會公眾更好地監(jiān)督財政教育經費的使用方向,提高運行效率。
第四,大力發(fā)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科技創(chuàng)新的重要場所之一,高等教育投入增加將帶來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將對當地經濟發(fā)展有促進作用,地方政府要為高校提供物質基礎,區(qū)域經濟發(fā)展需要高校的正外部性,也就是說高校知識帶來的技術外溢不必具有全局性,但必須具有地方性。同時,地方政府要做好服務工作,為高校與當地企業(yè)的科研合作、技術研發(fā)提供好的平臺[ 6 ]。
第五,增加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投資,改善人力資本健康狀況。基礎人力資本投資是技術進步、技術效率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中央政府應保證醫(yī)療、衛(wèi)生的支出在空間上、結構上均衡分配,以實現(xiàn)合理醫(yī)療資源配置。地方政府也要提高醫(yī)療衛(wèi)生資金的使用效率,做到合理配置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
【參考文獻】
[1] 陳維濤,王永進,李坤望.地區(qū)出口企業(yè)生產率、二元勞動力市場與中國的人力資本積累[J].經濟研究,2014(1):83-96.
[2] 梁超.制度變遷、人力資本積累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基于動態(tài)面板和脈沖反應的實證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2(2):58-65.
[3] 陳仲常,謝波.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外部性檢驗:基于我國省際動態(tài)面板模型[J].人口與經濟,2013(1):68-75.
[4] 夏良科.人力資本與R&D如何影響全要素生產率:基于中國大中型工業(yè)企業(yè)的經驗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4):78-94.
[5] 魏下海.人力資本、空間溢出與省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基于三種空間權重測度的實證檢驗[J].財經研究,2010(12):94-104.
[6] 路美弄,彭學君.人力資本結構、技術外溢與全要素生產率關系研究[J].商業(yè)時代,2017(3):13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