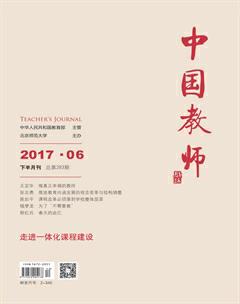平凡的教師,不凡的歷史
柴凈凈
鄭書廷
女,1945年10月生,河北省邢臺市平鄉縣宋夏莊人,初中學歷。1963—1972年于宋夏莊小學任教,1972—2000年于小章村任教。1986年以前為小學民辦教師,1986年轉為國辦教師。1993年被評為“小學高級教師”,2000年退休。
歷史的擁有不應僅局限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偉人,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歷史故事。追憶往事,那些不經意間走過的漫漫長路或許會成為后人永遠珍藏的精神食糧。用一篇文章來講述我作為一名鄉村女教師近四十年的歷史故事,恐怕不能完全概括。但是基于對教師生活整體上的認識,我會將最值得分享的教師故事展示給大家。回顧這一生,我認為可以用這樣兩個具有對比意蘊的詞匯來概括我的經歷:物質匱乏和精神飽滿。
一、物質匱乏的一生
物質匱乏是我們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是當時整個社會的主色調。我出生的時候,抗日戰爭剛剛結束;我的成長經歷解放戰爭、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等時期。可以說,我成長的那個年代,社會正處于尤為困頓的狀態,無論是生活條件還是教學條件都極其惡劣。我相信任何一個與我有著相似經歷的人以及任何一個真正走進我的生活世界的人都會有同樣的感觸。
1.生活上由朝不保夕到節衣縮食
(1)求學時代的朝不保夕
在那個窮的一無所有的年代,我人生的前四十年幾乎都生活在食不果腹的環境中,尤其是上學的那些年,生活的艱辛更是令人難以想象。
在艾村小學上高小的那兩年,我們家連過年都吃不上饅頭,平日里都是吃糠、野菜和草籽兒之類的東西,拉肚子便是經常的事情。一到春天,好多男孩都上樹去摘榆錢兒吃,我不會爬樹,只能吃榆樹皮和他們扔下來的榆樹葉。條件那么艱苦,我們也要堅持上學。
在平鄉中學讀初中的時候,正趕上三年自然災害,日子更加艱苦。家里的人都是在大隊里吃大鍋飯。他們吃的也不好,都是菜窩窩、野菜湯,見不到半點油水。而且,只有下地干活兒的人才能在大隊分到飯吃,我是學生,隊里不管飯,都是家人們把自己的飯勻給我一些。有的時候,姐姐會從大隊食堂里帶回來一些洗刷完之后、比較稠一點的湯水給我喝,除了這些,沒啥可以吃的。
那時候從來沒想到會過上現在這樣不缺吃不缺穿的日子,更不會想到幾十年后的人們會這樣嚴重浪費。現在鋪張浪費的人,大都是沒挨過餓的,尤其是現在的孩子,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反而不懂得珍惜。
(2)任教之后的節衣縮食
196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讓輟學在家的我與教育結緣。我先后在宋夏莊和小章村兩所農村小學任教,但是無論在哪里教學,我的生活依舊一貧如洗,尤其是在小章村當民辦教師的那二十多年,生活條件更是艱苦。
生活條件艱苦,最主要的原因是民辦教師的工資待遇極低。在宋夏莊小學任教期間,我的工資是一個月4元錢,外加一天9工分。在小章村任教期間,除了1984年①,我的工資一直都是一個月6元錢,外加一天9工分。每年積攢的工分到了夏天可以換半桶麥子(20多斤),秋天的時候大隊還會分四五十斤玉米和十來斤大豆。那時候的教師也沒有醫療保險,生病了連藥都買不起。感冒了,就用家里的土方法,用茅草根熬水喝,然后鉆到被窩里捂汗。
除了工資待遇低,“農民”的身份也加重了我們的生活負擔。由于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的四五畝農田便只能靠我一人打理。無論多累,我也要抽時間下地,遇到澆地的時候,就只能晚上自己去澆。我經常中午去鋤地,有一次實在累得撐不住了,竟躺在坷垃窩兒(農田洼處)里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看看太陽覺得到點兒了,就趕緊起來去學校上課。那些年,我早晨去學校的時候帶上午飯,中午把帶的冷窩窩頭什么的吃了,喝點兒水,然后不是備課就是下地干活,那些年(1972—1986年),我中午幾乎沒有回過家。
艱苦樸素的習慣就是這樣養成的,或許這就是時代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留下的印記:因為苦過,更知甜之不易。
2.教學上由一無所有到獨當一面
(1)任教之初的一無所有
嚴格意義上來講,我任教之初實際上是在創辦耕讀小學。村支書請我去當老師的時候,宋夏莊小學已不存在了。我答應邀請,便開始街鄰四舍地尋找生源。我們找到了十幾個五六歲的孩子,宋家莊小學又建起來了。然而,除了學生,我們幾乎一無所有。我們沒有教室。最初,我們在一戶鄉親家的大門底下上課,后來因為學生們太過吵鬧,被迫離開,搬到另外一個鄉親的破屋子里上課。不到一年,我們又因為同樣的原因被迫離開。最終,我們固定在村里的一間破廟里上課。有了教室,還沒有桌椅。我就帶著鐵鍬在破廟里挖坑,隔一段挖一個坑,學生們就坐在土坑里,把地面當桌子。桌椅的問題解決了,我們又開始上課了。
(2)教學路上的踽踽獨行
由于資源有限,宋夏莊小學和小章村小學(1966年以前)都是只有兩個老師、兩個班級、班級里各個年級的孩子都有。老師們都是全科教師,我主要負責三、四、五年級的課程。為了能夠教出好成績,我做的最多的就是給孩子們加課,其他班和村里的其他學校都是上午和下午上課,而我跟我的孩子們,每天五更(清晨3時至5時)上課,晚上也上課。每天早上起來之后,我會在我家門口點上油燈,孩子們看見我家門口的油燈亮了,就知道該上學了。晚上上課學校沒有照明設備,我就把自己家的花籽油拿到學校給學生點上照明。因為沒有鐘表,只能自己看天色或者憑感覺。那時候,下課也沒有具體的時間,從早上上課一直上到晚上,已經無法按照正常的課時來衡量工作量,只希望能夠教會
學生。
二、精神飽滿的一世
雖然物質上拮據了一些,但我依然熱愛生活和我的學生們,而且我堅信豐富的精神世界完全可以超越甚至掩蓋匱乏的物質世界。
1.鐘愛學習的可貴品質
我從小就喜歡學習,這種品質伴隨我走過了六七十個春秋。我在上學期間,學業成績一直都是名列前茅。那時重男輕女的思想還很嚴重,班上的女生寥寥無幾,父母也并不支持我上學,經常讓我曠課在家幫忙,我隨時面臨輟學的危險。因此,我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家里沒電,我就用膠泥捏成蠟碗,曬干,然后往里邊放點兒油,再把棉花搓成捻兒放進去,晚上點著這樣的油燈學習。
業精于勤荒于嬉。任教之后,我依舊保持著謙虛好學的態度。我珍惜每一次去縣城進修學習的機會,并經常寫教學日記以幫助自己反思、改進教學。20世紀90年代新課改之后,我面臨一些教學上的困難,但我沒有退縮,而是迎難而上。為了解決困難,我經常一個人在辦公室研讀各種教材、資料。實在無法解決,我便騎著自行車去向四五里之外的侄子求教。我的兒子和侄子比我的學歷高、懂得多,所以我便時不時地向他們請教。就這樣幾十年如一日,從未懈怠過。
2.樂此不疲的教學生涯
(1)選擇孩子就是選擇快樂
我喜歡教師這個職業,而且在我的熏陶下,兒子師范畢業以后也做了教師,兒媳婦也是小學教師,我們都是從內心認可自己的職業,覺得當老師是個良心活兒,心里踏實。在小章村小學任教的時候流行樣板戲,我便自編自演教孩子們說樣板戲,這曾經一度成為了我們音樂課的內容。全校的體育課也由我一人擔任,我參加過體育課的培訓,學過廣播體操,體育課上,我跟孩子們一起做操、做游戲、編順口溜。比如,在孩子們上體育課站隊的時候,我就自己編一些類似這樣的順口溜兒:“一二一、一二三四,挺起來脯兒,揚起來臉兒,嬉皮笑臉兒多難看兒。”孩子們很喜歡我的課,而我也樂在其中。雖然經濟條件落后,但是我們的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沒有條件,我們就自己
創造!
(2)付出實乃優秀教師之王道
雖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鄉村教師,但是跟村里的人關系非常融洽,大家也都很尊敬我。究其原因,我認為這跟我多年來的付出分不開。學生生病了沒去上學,我會在當天就去家訪,而且往往會帶上幾顆蘋果;學生想吃蔬菜卻沒錢買,我會伸出援助之手;學生在學校受傷了,我會送他去看醫生;偶爾會有經常曠課甚至幾欲輟學的學生,我苦口婆心地勸導他重新回到學校……因為經常給感冒的學生買藥打針,所以村里的人都知道我會打針。有一次爆發流感,村里的赤腳醫生不在,大家都找我打針,我就一個接著一個地打,從放學一直打到吃晚飯的時候,最后累得腰都直不起來。還有許多類似的事情,我勤勤懇懇地付出,鄉親們都看在眼里,怎么可能得不到學生及家長的尊重呢?
我這一輩子雖然沒邁出過學校的大門,但卻跟打仗一樣,一直在跟他們斗智斗勇,只是他們不是我的敵人,而是我的親人和戰友。
訪談后記
從一個十六七歲的初中畢業生到投入了二十多年心血的民辦教師,再到名正言順的公辦教師,直到以小學高級教師的職稱退休,可能很多人無法想象在那樣惡劣的條件下,在如此繁重的工作量面前,鄭老師是如何泰然處之的,又是如何化物質悲劇為精神動力的。鄭老師對往事記憶猶新,面對訪談毫無保留,侃侃而談。從她聲情并茂的話語中,可以看到一名普通的鄉村女教師對農村教育事業的默默耕耘與執著付出。在我看來,“苦”是鄭老師教學時代的主旋律,而“堅忍”則是生長在她內心深處的常青藤。未曾經歷過便很難真切地體會經歷者的情感世界,作為一個研究者,我能做的就是盡我所能將最真實、最原始的狀態呈獻給讀者,至于體會和感悟大概也會因人而
異吧!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師口述史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