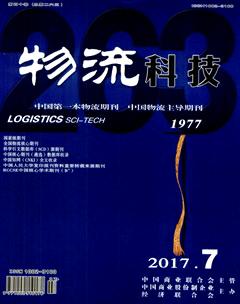“互聯網+”現代物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企業家偏好演化研究
陳一芳+王順林



摘 要:面對“互聯網+”現代物流的形勢,文章對現代物流業轉型升級的相關文獻進行了研究,發現相關文獻存在著“偏好外生給定”的假定,不利于解釋復雜的經濟現象。基于偏好內生演化,對奧斯特羅姆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圖進行了拓展,構建了“互聯網+”現代物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企業家偏好演化分析圖。在此基礎上,通過構建帶有規則偏好的個體效用函數,初步分析研究了“互聯網+”現代物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企業家偏好演化機理。
關鍵詞:互聯網+;物流;偏好演化
中圖分類號:F253.9 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In the face of“internet plus”modern logistics, this article has carri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to the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re is a hypothesis that“preference is given to the outsid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xplanation of complex economic phenomena.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evolution of preference, the paper analyzes Ostrom social ecosystem analysis diagram and constructs the analysis chart of entrepreneur' preference evolution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ocess of“Internet plus”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By constructing the individual utility function with rule preferenc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trepreneur' preference evolution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ocess of“internet plus”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has been carried out.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logistics; preference evolution
作為互聯網發展新業態的“互聯網+”,借助信息通信技術以及互聯網平臺,通過互聯網與相關行業的深度融合,創造出新的發展生態,以提升行業的創新力和生產力。2015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引發了全國各行各業的關注。從象征著跨入互聯網時代的手機APP終端的出現,到國家級物流平臺公共信息平臺的發布;從信息互聯互通,到智能化的服務體系;從大數據到云計算;從跨界融合到“四流”融合,“互聯網+物流”的新興運行思路正迅速崛起。
徐水波稱目前物流行業流行的車貨匹配APP都在回歸線下,甚至預言在2016~2017年間,將會有很多互聯網+物流企業死的很慘[1]。國家發改委公布的《2015年全國物流運行情況通報》數據顯示,2015年社會物流總費用為10.8萬億元,占GDP的比率為16.0%,相比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來說,我國物流成本仍居高不下。物流成本高帶來的問題不僅會使產品價格更加昂貴,同時也會導致消費品價格上漲,導致人民生活成本提高。
一方面參與者的熱情度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統計數據和實踐運行狀況不盡如意,面對“互聯網+”現代物流這一發展機遇,如何提升物流綜合效率效益,有效降低社會物流總體成本,在產業轉型升級背后的制約因素是什么,是目前業界迫切需要研究和追問的方向。
1 文獻綜述
作為生產性服務業之一的現代物流業,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勞動分工的細化、產業結構的變化和市場需求方式的變化,不斷調整著自身組織形式和發展方向,以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改革需求。物流產業特殊的發展歷程和產業特性,決定了現代物流產業升級的復雜性和個性化。縱觀現有文獻,目前關于現代物流業轉型或升級的論述有以下觀點。
一是,基于產業融合理論,探討了現代物流業的融合演進路徑。為了滿足用戶逐步釋放的“一站式”物流服務需求,借助物流信息技術的發展,物流產業涵蓋的不同行業(如倉儲、運輸、流通加工等)之間的關聯性不斷提升,物流產業內部進行了內部融合。其次,物流產業與外部產業之間的互動不斷提高,物流產業進行了外部融合(即產業互動)。如張蘭怡、邱榮祖(2010)將物流的發展過程劃分為早期階段、萌芽階段、綜合物流階段、供應鏈管理階段等四個階段[2];趙維平(2009)指出,信息技術對傳統物流產業的滲透與融合,導致傳統物流產業邊界變得模糊,形成了物流產業的內部融合[3];Marshall指出,隨著制造產業的不斷擴大,對生產性服務業的要求越來越高,需要專業的提供服務的第三方[4];Quinn認為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撐的,制造業依賴于生產性服務業所提供的服務,生產性服務業依賴于制造業提供的需求而存在[5];Lundvall和Borras提出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無論在發展過程中是怎樣的形式,最終均會融合發展[6]。
二是,借助產業生態系統理論,研究了現代物流如何拓展上下游產業鏈,形成閉合生態系統。產業生態系統認為在動態演化過程中,系統構成要素的數量和質量不盡相同,會出現迅猛發展、逐步穩定、劇變到內外部改革,最終形成一個新的穩定的、適應整體產業環境的產業生態系統。Zott和Amit(2010)提出由于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商業模式與企業發展不再匹配時,應該打破此時的平衡狀態,重塑商業模式,進而促進產業路徑演化[7];Morris(2003)強調企業應該根據外界環境的變化,不斷改變經營模式,從而促進商業模式向前演化[8];韓騰越(2013)認為應該以產業生態系統為方向,促使物流企業沿產業生態系統方向成長發展[9]。
三是,以價值鏈理論體系為指導,探究了突破“價值鎖定”的現代物流業發展路徑。Lee,H.L. and Billington(1993)指出供應鏈是由多個企業協同起來的企業群依據各自的專業化分工,構建的一個執行功能網絡[10]。有安健二(2005)認為物流的發展是“物的流通——商務物流——價值鏈物流”的過程,實現全球價值鏈整合的基礎是物流[11];Brusoni,Prencipe和Pravitt(2001)指出,在不同的技術生命周期階段,技術的專用性程度和標準化程度不同,企業應選擇不同的一體化策略[12];Christensen(2002)提出了一個推測性的模型來幫助企業決定應該在什么情況下使用一體化或外包策略來提升競爭力[13]。黃麗鴿、井晶研究了價值鏈的知識管理對企業業務價值的創造作用,通過將知識管理模式與企業業務結構進行匹配,從而給企業創造業務價值[14]。。
四是,依據平臺經濟和互聯網思維理論,分析了平臺經濟模式下物流企業資源的配置效率,借助互聯網平臺經濟模式的發展,推進物流產業的轉型升級。Kaplan & Sawhney(2000)分析了互聯網平臺的“聚集”效應,認為該特征類似于網絡效應[15];Koyuncu(2004)提出網絡購物的快捷性和更實惠的價格會吸引更多的消費者,但是快遞配送的時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消費者的網絡購物頻率[16];徐晉等(2006)指出平臺實際上是一種現實或虛擬空間,引導或促成雙方或多方用戶之間的交易,通過收取恰當的費用努力吸引交易各方使用該空間或場所,最終追求收益最大化[17]。田剛(2003)認為,隨著賣家和買家的水平和素養的提高以及相關的法律和信用體系完善,網絡平臺將成為消費者購物的有效渠道[18]。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對物流產業轉型或升級的研究相對較多,成果也比較豐富,但主要是立足于“偏好外生給定”的假設,結合相關經濟學理論范疇,對物流產業轉型或升級進行了相關探索。大量研究發現,個體偏好在許多情況下并不滿足新古典經濟學所描述的邏輯性質。“偏好外生給定”很難解釋復雜的社會經濟變遷現象,并且在方法論上容易陷入還原主義的窠臼。因此有必要從偏好演化角度,探索物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企業家偏好,以破解“互聯網+”現代物流背后隱藏的機理。
2 分析模型構建
“互聯網+”作為一種新業態、一種新的社會生態,借助互聯網這一共享資源,通過融合不同產業,促進相關產業的升級換代。對于“互聯網+”現代物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企業家偏好演化對于決策行動的研究,可以借助奧斯特羅姆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框架,基于企業家個體選擇行為的分析,揭示出企業家偏好演化引致的合作決策變動,初步探索轉型升級背后的隱藏機理。
奧斯特羅姆社會生態系統分析框架中的基于個體選擇行為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通過社會困境宏觀環境—個體決策微觀場景,對信任與合作行為的影響,探索了個體的合作決策過程。其中的“廣泛環境變量”包含著社會困境場景因素,這些變量影響著個體所處的微觀場景變量,即個體以前所經歷的場景,該場景的經歷,使個體學習并采納了某些處理應對事務的規范,個體們秉持的規范影響著他們對別人的信任水平;信任水平決定了合作水平,而合作水平決定各自的凈收益,凈收益又對個體的學習過程信念調整行為產生影響。
奧斯特羅姆分析框架雖然可以為我們后續研究提供一定的框架,但是不利之處在于,分析框架中的規則是給定的,認為特定的規則會影響個體的決策,但沒有分析對不同規則有不同偏好的個體,處于有多個規則的場景中,對不同規則的偏好程度是否會影響個體對他人的信任水平,進而影響合作決策。
行為經濟學家借助最后通牒博弈、獨裁者博弈、公共品博弈以及信任博弈實驗等研究,證實了社會偏好存在性的有力證據。卡尼曼(2012)認為人的決策依賴大腦的兩個識知系統:系統1和系統2,人們通常情況下都依賴系統1的自主運行,系統1可以看作是沖動,系統2可以看作是自我控制,人的決策同時受制于這兩個系統,從而表現出不那么理性。周業安(2015)認為系統1對應著社會偏好,是啟發式和框架決策,這種決策不僅依賴問題的描述和程序等外在框架, 更依賴個體自身的直接經驗、通過學習所掌握的間接經驗、個體所處的社會狀態、個體和他人之間的互動等社會因素。系統2負責理性決策,對應著自利偏好和風險偏好等[19]。
Amit和Zott(2001)指明,效率、互補性、新穎性、鎖定是企業改進其商業模式的方向[20];Miles等(2006)認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共贏是企業商業模式創新的重要方向[21];邵天宇(2014)指出,價值原則與Zott和Amit的設計主題以及Hamel的支撐要素相似,開放、合作、交互和快速構成了互聯網思維的價值原則內容[22]。
綜合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在考慮“互聯網+”現代物流產業轉型或升級過程中,必須將企業家的偏好演化與個體選擇行為分析框架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思考,才能較為準確地揭示隱藏在“互聯網+”現代物流背后的制約因素,據此,設計了“互聯網+”現代物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企業家偏好演化分析圖,如圖2所示。
3 “互聯網+”現代物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企業家偏好演化研究
從個體或微觀的視角看,偏好演化可以簡單地描述為個體放棄某一種偏好而轉向另一種偏好,而這種偏好變化不是完全理性的選擇,而是一種有限理性的學習過程或調整過程。偏好演化實際上是參與者對更具有適應性或者更好的偏好的學習或搜尋過程[23]。
如圖2所示,微觀場景變量是現代物流業的企業家面對“互聯網+”這個決策場景,該場景變量面對是否進行“互聯網+”現代物流這個決策變量,決策前,首先依賴的是自己未進行“互聯網+”之前的業務經歷,即原有的業務規則;其次,又受到互聯網秉持的價值原則的影響,即“互聯網+”規則。二者之間的交叉融合,致使企業家面對“互聯網+”現代物流命題出現難以抉擇的困境。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擬在個體效用函數上加入規則偏好影響因素,從效用函數和模型分析框架圖兩個角度探索“互聯網+”現代物流業轉型或升級過程中的企業家偏好演化與選擇行為。
其中,γ作為刻畫個體對規則的偏好程度。
金旭冉(2013)通過類似模型,通過對比獨裁者實驗、信任博弈、蜈蚣博弈、古諾均衡和最后通牒博弈實驗中的策略選擇,論證了上述模型的可行性[25]。
正如周業安所述,日常生活中人們更多地依賴系統1,即啟發式和框架決策,而不是尋求深思熟慮。換言之,即物流業的企業家們在長期經營過程中形成的規則具有一定的慣性,經過系統1的偏好強化,往往會對新生事物(“互聯網+”)產生“視而不見”或者“不急于參與”的心理感受[19]。
推導式(1)和式(2)效用函數,可以得出個體通常會以犧牲自己的物質收益為代價,遵守偏好的規則;當物質收益足夠大時,足以彌補違背規則產生的心理負疚感時,個體便會選擇偏離規則,獲得較高的物質收益。因此,要想使現代物流業的企業家們放棄原有業務的規則偏好,轉向“互聯網+”規則偏好,實現偏好演化,不能寄希望于企業家們的自我感知及自我探索,必須為其提供一定程度的“互聯網+”前后的物質收益對比,以激發企業家們的“互聯網+”現代物流的偏好演化,進而促使企業家們愉快地沿著圖2的路徑進行不斷的“互聯網+”現代物流行動方案選擇和決策。
其次,當合作行為需要長久、不斷付出時,除了自身的規則偏好程度,對他人是何種類型(是否持有相同規則偏好)的判斷對決策的影響也非常大。據此展開,在現代物流業轉型或升級過程中,圍繞“互聯網+”現代物流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可以使得合作伙伴能夠掌握彼此之間的規則偏好異同,通過彼此之間的業務融合,強化偏好演化從原有業務規則偏好向“互聯網+”規則偏好進行演化。
第三,當別人表現出善意行為時,個體也會選擇善意的行動,哪怕這種行為的物質收益相較于其他行動帶來的物質收益會有所減少。現代物流業的發展呈現出不均衡、粗曠發展的態勢,不同規模、類型的物流企業家們依據一體化模式的聯通,并不能解決彼此的技術、觀念和管理等的差異。可能的情況會發生,已經“互聯網+”現代物流的企業家面對著未“互聯網+”的參與者,考慮到對方的善意行為,往往在融合“互聯網+”的過程中留下非“互聯網+”缺口,以適應參與者的實際情況。由此帶來的問題會產生原有業務規則偏好和“互聯網+”偏好規則共存情況,當合作行為需要長久、不斷付出時,會出現參與者彼此之間在偏好判斷上出現模糊狀況,進而不利于偏好演化。
4 總結與展望
“互聯網+”物流的新興運行思路不斷涌現,但統計數據和實踐運行狀況不盡如意。產業轉型升級背后的制約因素有什么?通過對現有物流業轉型升級文獻研究,筆者發現“偏好外生給定”是很多文獻的假定條件。
按照格蘭諾維特的觀點,自利性和社會性都會在個體層面得到反映,人性原本就是一個復雜的結構。本文試圖從偏好內生角度,探索“互聯網+”現代物流業轉型升級背后的企業家偏好問題,希望借助企業家個體選擇行為分析,揭示出企業家偏好演化引致的合作決策變動,進而探索轉型升級背后的隱藏機理。
(1)本文基于奧斯特羅姆基于個體選擇行為分析框架圖思路,構建了“互聯網+”現代物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企業家偏好演化分析圖;
(2)基于企業家偏好演化分析圖,構建了帶有規則偏好的個體效用函數,進行了偏好演化分析。
構建一個能全面描述基于偏好演化視角下的物流業轉型升級企業家行為決策模型是今后進一步研究的重點,這種模型能夠涵蓋不同行業之間參與者(企業家)的收益變化和學習規則變化等對偏好演化的作用機理。此外,企業家偏好演化機制和物流系統動力因素之間的邏輯關系也是未來有待深入研究的重點。
參考文獻:
[1] 徐水波. 未來2年互聯網+物流企業將死的很慘[EB/OL]. (2016-03-01)[2017-03-25]. 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6/03/01/16828hzla.shtml.
[2] 張蘭怡,邱榮祖. 我國物流發展現狀與展望[J]. 物流科技,2010,33(12):8-11.
[3] 趙維平. 關于物流產業的融合研究[J]. 商業經濟,2009(7):92-93.
[4] Marshall J. N.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Service: Evidence from the Motor Vehicle Aftermarket in the West Midlands Region of the UK[J]. Regional Studies, 1989,23(2):139-150.
[5] Quinn J. B., Baruch J. J., Paquette P. C.. Exploiting the manufacturing-services interface[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88(1):49.
[6] Lundvall B. A., Borras S. The Globalizing Learning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Pllicy[R]. TSER Programmer Report, DG Ⅷ,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8.
[7] Zott C, Amit R, Massa L. The business model: Theoretical root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R]. Working Paper,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Navarra, 2010:401-412.
[8] Morris M, Schindehutte M, Allen J. The entrepreneur's business model: Toward a unified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3,58(1):726-735.
[9] 韓騰越. 產業生態系統視角下物流企業商業模式演化過程研究——以順風速運為例[D]. 遼寧:東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10] Lee H L, Billington C. Material management in decentralized supply chains[J]. Operations research, 1993,41(5):835-847.
[11] 劉義鵑. 價值鏈中節點企業之間關系的協調機制研究[J]. 財貿研究,2006,17(5):105-110.
[12] Brusoni S., A. Prencipe, K. Pavitt. Knowledge specialization, organizational coupling,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why do firms know more than they mak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1,4(6):597-621.
[13] Christensen, C. M., M. Verlinden, et al. Disruption, disintegration and the dissipation of differentiability[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2(5):955-993.
[14] 黃麗鴿,井晶. 關于知識管理創造企業業務價值的探討[J]. 中國集體經濟,2007(6):44-45.
[15] Kaplan S, Sawhney M. Marketplace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0(5):97.
[16] Cuneyt Koyuncu, Gautam Bhattachaiya. The impacts of quickness, price, payment risk, and delivery issues on line shopping[J].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4(33):241-251.
[17] 徐晉,張祥建. 平臺經濟學初探[J]. 中國工業經濟,2006(5):40-47.
[18] 田剛. 網絡購物的經濟學分析——成本與效用[J]. 商業研究,2003(7):164-166.
[19] 周業安. 論偏好的微觀結構[J]. 南方經濟,2015(4):110-114.
[20] Amit R, Zott C. Value creation in e-busines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22(6-7):493-520.
[21] Miles R E, Miles G, Snow C C. Collaborative Entrepreneurship: A Business Model for Continuous Innovation[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006,35(1):1-11.
[22] 邵天宇. 互聯網思維下的商業模式創新路徑研究[D]. 大連:大連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23] 黃凱南. 偏好與制度的內生互動:基于共同演化的分析視角[J]. 江海學刊,2013(2):80-85.
[24] Steven D. Levitt, John A. List. What do laboratory experiments measuring social preferences reveal about the real world?[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7(21):153-174.
[25] 金旭冉. 規則偏好對合作決策的影響——以住宅小區治理為例[D]. 江蘇:南京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