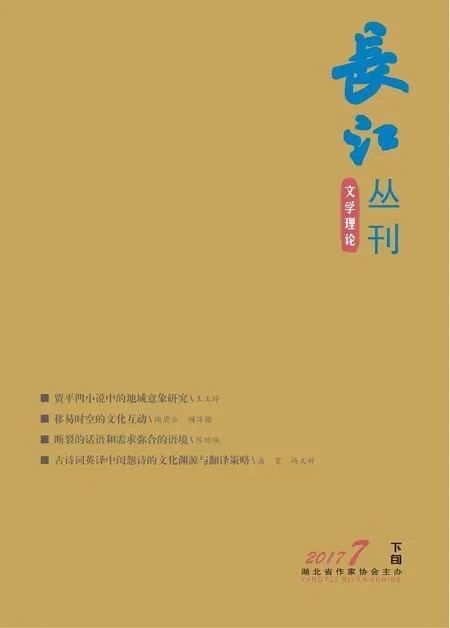山那邊,是崇陽(外一篇)
成 麗
山那邊,是崇陽(外一篇)
成 麗
向往崇陽,不單是向往可圈可點的視覺風景,更是渴望觸摸歷史在這塊熱土留下的足音。
——題記
古堰灣的水聲
一
都說崇陽古堰灣是一首詩。
有春的靈動,夏的蓬勃,秋的厚重,冬的壯美。
說的人多了,各種聲音如一團迷霧,在腦海糾纏、滲透,綴滿補丁。
古堰灣,是一座村莊,一方湖泊,抑或是一條攔河蓄水大壩?
無論是何種稱謂,一個“古”字,修飾、限定、說明了這個稱謂的品質與特征。
古字讓人無限遐想。
向往和追尋,時時涌起。
二
汽車在高速路上飛馳。車窗兩側飛逝而過的除了山,還是山。蒼茫無盡。綠,蔥翠了四面環山的崇陽。
山高的地方,有石,有洞,有水,有勝景。
青山水庫、洪下十里畫廊、大泉洞、何家巖、灌溪寺,崇陽數不勝數的景致留不住我匆匆行走的腳步。煙雨蔥蘢,明清時節的石板街如一幅水墨畫,木門木窗,飛檐斗拱馬頭墻,古意闌珊。汽車穿過白霓古鎮的喧鬧,越過清朝京劇名伶米應生白霓麻石的老家,在一片開闊地前停下。等候已久的崇陽文友,如注入了雞血,梳理著自己的情緒。
水聲。如庭院深處傳來的琴蕭合奏。低沉渾厚,清晰入耳。
田壟交錯,屋舍儼然,小路的兩側,綠樹成蔭。四下搜索,不見水源。
穿小道,過田塍,腳步催生了風,催生了植物的葉子與花朵之間的親昵。
水聲,伴著腳步的急切,越來越大。如悶雷滾過頭頂的磅礴,似萬馬奔騰的咆哮,攜竹浪排空的激越,似群猿嘯谷空壁回音的共鳴。轟隆隆,直撞耳膜。
透過路邊茂密的桃樹叢,上游,一條白練自兩山之間傾瀉而出,以銳不可當的氣勢向前奔流,流至白石港中段山咀相夾的窄處時突然斷層,壓縮為橫切面約40米的合力,以6米的垂直落差,向絕壁的下游翻滾、撞擊。水與石的撞擊,是高與低的較量,是柔與剛的撞擊,是力量與力量的搏擊。一簾瀑布,白生生、白凈凈、白茫茫,如霧似煙,跌落巖石。河的鱗甲,水的鱗甲,浪的鱗甲,四下飛濺,片片飛散。浪與石的撞擊與反彈,激起巨大的聲響——那是攝人心魄的悲壯!
三
瀑布下的礁石以塊、團、叢的方式存在。
黝黑,凜然。遺世獨立。
石的造型是一部生物化石標本。
單立或成片,相連或穿插。或半隱于水,或裸露于水面。圓或半圓,方形、菱形或多邊形,單孔、多孔或孔里再生密密匝匝的子孫。如老樹枯立,似田螺攀爬,如百獸奔跑,千姿百態,詭秘,怪異。讓人動容。浪從石上過,從孔中過,從腳下過,億萬次的承接與包容,激憤、兇猛、暴怒或舒緩,浪將礁石沖擊洗刷成自己的樣子。數不清的浪,數不清的水,在礁石的腳下流走了。數不盡的人來人往,斗轉星移,礁石終于洞穿了歲月,守著自己的影子,與蒼穹,遙遙相望。
石,不生花,不長草,只長堅韌。
脫鞋,涉水,靜坐石上,看白鷺翩飛,看蟹與魚蝦在通透的靜水里調情。下游,浩浩湯湯的水流浸潤萬頃良田。我撫摸著腳下的巖石,敲擊,耳邊傳來清脆的回聲:有三國東吳名將陸遜屯兵金城山時千軍萬馬的嘈雜;有后唐民夫抬石挑土筑壩的號子;有宋太史黃庭堅在“金城墨沼”濯洗筆硯的嘆息;有明嘉靖賈商熊白霓捐資建橋,小鎮世代以“白霓”命名、勒石銘記其善舉的贊語;有太平天國將士與清軍血戰歇馬山的豪情壯語;有商代銅鼓韻味回旋的鏗鏗鏘鏘;有現代提琴戲走進央視舞臺的咿咿呀呀……
四
一條河流的走向,因了人類的智慧而改變了單一的價值,從默默無聞的流淌,到后唐時期攔河筑壩蓄水、惠及千家萬戶的水利灌溉,到如今,成了一方水土的福星,一處游覽勝景。千年,在接納、承載中成就了自己。
古堰灣,你是大唐遺落的一紙綴滿小楷的折扇,是宋朝易安凄清婉約的一首小詞,你是清朝漢劇名家米應生唱腔激越的二黃,你是民國出土的年代久遠的青花瓷。古樸與厚重寫意你延綿千年的符號。
是夜,對著電腦的一幀照片出神:瀑布下方的巖石上,一個女子側身端坐,目視遠方。她的前方,是一群民夫勞作的剪影。他們頭系方巾身纏草繩打著赤腳,或挑土或抬石,用汗水將糯米與石灰糅合,一塊塊條石粘牢、疊加、壘起。人類用原始的手工造就了一座大壩的永恒。
關機,熄燈,巨大的水聲時時自頭頂轟響。
從回頭嶺到珞珈山
我去崇陽,不是為了考古,亦不是為了聽戲。我是專程去拜謁一個人。
我是從作家方方寫武大歷史的書里,得知這個人的名字的。準確地說,以寫小說馳名的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曾是1970年代末期武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她以輕松的筆調將母校武大從籌建到發展寫得深入淺出,跌宕起伏。最重要的是,她說武大與一個人息息相關,沒有這個人的不屈和堅持,武大的校址和歷史也許會改寫。她用厚重的筆墨將這個奠基人的見識、視野、智慧、執著、強悍、憂患、使命感及一根筋的倔強,寫得生動飽滿。從選址圈地的費盡周折,申報教育部時的巧妙周旋,到不懼安危與當地民眾的斗智斗勇,仿佛就是一部幻燈片在眼前上映。讓人一下子就記住了他——王世杰。
而我更多關注王世杰,不是武大第一任校長的頭銜,只因他是咸寧崇陽人。咸寧——崇陽,讓我一下子與先賢王世杰拉近了距離,有了親切感。仿佛這個胖墩墩的睿智長者就是我的祖父。國立武漢大學,民國時期中國的四大名校之一,我雖然不曾在那里求學,但因為我們咸寧人王世杰,我和她便有了天然的血脈相連。
是以,一到崇陽,我們便直奔王世杰故里。
司長也是文學的鐘情者,一路妙語連珠,握方向盤就像玩有規則的文字游戲,下高速,上國道,穿小道,他一路把車弄得妥妥帖帖。
車子拐進白霓鎮,在一片開闊地停下。我拿了相機,拉開車門,沖進雨地,朝那棟青磚瓦房奔去。
磚青,瓦黛,苔綠,四水歸堂的透亮天井;左右對稱的廂房、正房、雕花窗;一進二重的堂屋。一切都如我想象中故鄉老屋的模樣,簡約,寂靜。磚與木互為依托,與歲月艱難抗衡。老屋右側的巷口走廊處,有一棟空蕩蕩的共墻老屋。三重,三天井。陰暗、潮濕。穿行其中,不時得抬頭仰望屋頂,提防瓦片貿然掉下;或以手掌掩面,以遮擋木梁木條被蟲蟻啃蝕漏下的木屑。這左右相連的老屋,便是王世杰的故居。
石門、石窗、石柱、石天井,在舊時的鄉村,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而這門楣上精雕的“雙鳳呈祥”“花開富貴”“六畜興旺”的石雕倒是極為少見。
我舉起相機對著高高的墻頭拉近焦距,一條素龍頭枕檐角口含龍珠臥在屋脊上。蒼穹之下龍的圖騰活靈活現。細看,這屋宇上飛舞的長龍由玄黑瓦片砌成。有兩瓦對疊成對應弧度的橢圓空心形,亦有摞成張弛有度的密實弧線形。這些樸實的瓦片經過石瓦匠的一番搗鼓,變成了賞心悅目的手工藝品。暗自贊嘆這能工巧匠如何在屋頂立足,不經意間又見天井、墻頭的檐下內外皆是一字兒排開的繪畫,白底素描,與素色的飛龍渾然一體,讓人聯想起低調的名門望族之類的字眼。
右巷墻外是一片空曠之地,有耕地、有田壟,煙雨蔥蘢。水田里老農披蓑戴笠揮鞭正吆喝著老牛。遠山如黛,在微雨中靜默,好似國畫大師揮毫潑墨的山水畫。回頭嶺的地勢,左高右揚中間低,屋前是低洼的平畈,整個山形似一匹奔馳的駿馬。若干年前,王世杰當貨郎的曾祖父走村串戶,正是看中這塊風水寶地,才停下行走的腳步,在此筑屋開荒,落戶安居。
我坐在巷口的石坎上,視線從瓦楞、墻皮落到地面,思維卻在里弄的深處游走。時光的背影里,王世杰以不同的面貌不同身份向我走來,從幼年到少年,從青年、中年到老年,從家鄉、武大到臺灣,每一個身影都是孤獨的。在這種孤獨里,他完成了從起點到終點,從終點回歸起點的過程。從1891到1981,整整90年,他終于停下漂泊的腳步,魂歸武大,從此,靈魂安逸,不再孤獨。
125年前的那個春天,公元1891年3月10日的傍晚,天陰沉沉的。一聲啼哭,帶著清新的喜悅,打破了回頭嶺村莊的沉靜。王世杰誕生了。隨即,電閃雷鳴,大雨傾盆。接生婆喜顛顛沖著門外候著的王父高喊:恭喜老爺,是個少爺。見多識廣的王父見天象異常,近看兒子天庭飽滿,唇線的棱角分明,料想此兒日后絕非等閑之輩。便取名世杰,字雪艇。希望他為人中之杰,在風云四起的亂世中掌舵航行。
三歲之前,他是快樂的。
他在祖屋的巷弄攀爬。從咿呀學語到蹣跚獨步,一磚一石浸潤他的氣息他的體溫。稍大些,他在農舍看雞鴨搶食、犬貓相嬉,聽屋外布谷催春、鳴蟬鬧夏,回頭嶺的靈山秀水使他的小腦袋裝滿了許多幻想。淳樸的鄉情陶冶了他敦厚的性情。
四歲入私塾讀書,他的孤獨便開始了。同學在玩鬧時,他手持書本,目不斜視,博聞強記。年齡最小而學業優,師贊。父母夸。同學羨。這樣過了八年,小世杰成了鄉村少有的品學兼優的少年郎。恩師周芷熙力薦其父送他至武昌念書。
時值張之洞在鄂督學,主考官見世杰年齡偏小、個矮,在收不收間猶疑,報張之洞。張之洞幼年稟賦聰慧,13歲以前已學完四書五經及多篇兵學名著。不滿14歲考中本縣秀才第一名。這個學識淵博的學士有識才的慧眼,他決定親自考考小世杰:
“這么小,為什么要來武昌讀書?”
“為人杰,為堯舜。”
六個字,擲地有聲。張之洞一驚,大筆一揮,王世杰便進了考場。張之洞的慧眼有了回應:世杰考了武昌南路小學入學試的第一名。從此,崇陽山村飛出的小雛鷹,便在省城的天空展翅翱翔。
此后,他先后就讀湖北師范理化專科學校,天津北洋大學(天津大學)。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他的孤獨化成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他像蓄勢待發的斗士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寫倡議書,貼標語,演說,甚至參加守城戰斗。“二次革命”的失敗給他迎頭一擊。他清醒意識到只有國民思想的覺醒,才能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他先赴英國倫敦大學攻讀經濟學,后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究法學,分別獲碩士、博士學位。在世界知名學府的學習豐富了他的知識面,拓寬了視野,也讓他站在國際的前沿看清國內政治的動蕩和社會的混亂。
中國的現狀使他憂心忡忡。他從一介書生的孤獨,變成對民族的憂患。
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在國外的王世杰迅速聯絡留歐的中國學生,拒絕不平等條約,阻止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他帶領留歐學生和華工一同圍守中國首席代表陸徵祥的寓所,力陳利害,阻止簽約,使陸無法出席會議簽字。1920年,王世杰再次擔任中國旅歐學生代表,先后赴比利時、意大利,出席國際聯盟同志會。他的膽識、才干和過人的智慧再一次在國際政治舞臺得到認可。
29歲的王世杰受北大校長蔡元培之聘回國,任北大法學教授、系主任,他傾其所知以授莘莘學子,內心漸漸安靜,一頭扎進了學術研究。這期間,他著書立說,成績斐然。他所著的《比較憲法》講義,為我國法學界的奠基之作,被社會廣泛采用。他淵博的學識,獨特的見解受業界與學子的熱捧。隨后,著或與他人合著有增訂《比較憲法》《憲法論理》《代議政治》《中國不平等條約之廢除》《移民問題》《女子參政之研究》《中國奴婢制度》等,在當時引起了轟動。在大量的撰寫和編稿時,他的孤獨感慢慢趨于平復。我想,如果處于和平年代,以他的嚴謹自律和鍥而不舍的研究,他一定會成為世界頂尖的法學人才。
時值國內動蕩,群雄四起,魚目混珠,各黨派借機擴充勢力。學子與進步人士紛紛發起救國運動。他的憂患意識使他無法安心教學,在北大執教兩年后,1922年,王世杰與李大釗等人組織發起民權大同盟。次年,又與北大的陶希圣、周鯁生、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丁西林等四十多位著名學者、教授、骨干一道發起組織《現代評論》社。針砭時弊,傳播馬列主義、宣揚民主科學思想。
他對時事的敏感和深層次的洞察力,再一次使他鋒芒畢露。
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王世杰被任命為首任立法委員,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先后擔任法制局長、海牙國際仲裁所裁判官、湖北省政府政務委員等一系列重要職務,為他后半生長久的孤獨埋下了伏筆,同時也為他籌建武大時方方面面的周旋提供了方便。
王世杰的人生拐點在武大。
1929年2月,王世杰被任命為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世杰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另擇校址,興建校舍。校址由王世杰和李四光多次協商,圈定東湖珞珈山。從此,他奔赴于官方與民間,游走于湖北省與國家教育廳。從籌備建校經費到設計一物一景,從招標的考察到依山而建的各類建筑群,每一處,他的智慧和口才,耐力與韌性發揮到極致。尤其是校舍內的珞珈山上有很多大戶人家的祖墳,要想動人家祖墳無異于在太歲頭上動土。大戶人家的子孫從商、為官者眾多,他們一方面聚眾阻撓不讓動土,另一方面羅列數十條罪狀讓族中遺老遞送國家教育廳及南京政府,中央政府都被驚動了,發布告示,勒令另選校址。王世杰甚至數次收到當地群眾給他發來的死亡威脅。很多人都想打退堂鼓,不愿與政府對抗。可這個在大山里走出來的不屈漢子,多次在國外留學的開明紳士,他的謀略和視野早已非常人所同,他一心要將武大建成中國的名校。而名校的框架結構,建筑設施要經受百年千年歷史的考驗,數以萬計的學子將在這個搖籃學習、成長、走向各個重要崗位,乃至走向世界各地。依山傍水的東湖珞珈山便是當年楚莊王的宿營之地——落駕山,這湖光山色、萬千氣象之地,是千載難逢的風水寶地!王世杰胸懷大志,內心波濤洶涌,臉上卻波瀾不驚。他小小的個子穿行于阡陌之間,以立法委員的胸襟和海牙國際仲裁所裁判官的理性分析、調解,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耐心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一邊奔走在武漢至南京政府之間,以三寸不爛之舌,將方方面面的工作做通,工程如期動土……
1932年,新校舍一期工程竣工,氣勢恢宏、中西合璧的宮殿式建筑群錯落有致雄踞在珞珈山上。1934年武大新校舍落成典禮,蔡元培致辭,稱其為“國內最漂亮的大學建筑”。胡適也曾自豪地對一位美國友人說:“你如果要看中國怎樣進步,可以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漢大學!”
王世杰生活簡樸,不茍言笑。但他開明辦學,以“三嚴”管理武大:嚴謹治校,嚴明紀律,嚴選教授。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在四海之內不惜高薪聘請教授。致大師云集。武大很快成了全國各地名流、學子趨之若鶩的圣地。
東湖長,勿相忘。
一生濃墨重彩的得意之筆,落在東湖。東湖的武大傾注了王世杰的無限心血,牽著王世杰的魂。即使后來他身居要職,遠赴臺灣,仍對武大念念不忘。后半生的所有政績不抵一句“武大之父”!
“武大之父”是后世對王世杰最給力的肯定!
父,教父、神父、父親,有著山一樣的深厚,海一般的情懷。在甲骨文中,“父”是一個人手里拿著一柄石斧,持有石斧是力量與勇敢的象征,“父”引申為持斧之人,是值得敬重的人。
而歷史卻給王世杰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
王世杰淵博的知識和內治外交方面運籌帷幄的卓越才能,為最高當局所倚重。蔣介石慕其才華,遂吸收其為自己的智囊。王世杰曾兩度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擔任首任秘書長。他數年置身于最高決策圈,身兼數職。在蔣介石和宋美齡到埃及開羅參加美、中、蘇最高領導人會議時,出于工作和感情的需要,蔣介石指派王世杰以外交官員的身份陪同。后來,王世杰甚至愚忠替主子背黑鍋,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違心簽字,使他后半生一想起,心就隱隱作痛。
他這樣的人怎么能當幕僚呢?
他不煙不酒,不坐專車,不住官砥,自己租房住,步行上下班,自己裝電話,連話費都是自付。這樣簡樸的異類,怎么能在魚目混珠的政壇混?
共事多年的同僚說:“雪公的氣質,尤不適官場生活。官場上,多是巧言令色之輩,而他不茍言笑,幾乎無世俗的嗜好。單就這兩款,足以使他獨來獨往,無朋黨奧援。”
他在染缸里是何其的孤獨!
他在孤獨中逐漸老去。
在臺北自家花園的搖椅上,他想起1925年的家鄉,史上罕見的饑荒之年。故鄉崇陽三個月未下一場透雨,田地龜裂,莊稼顆粒無收,父老鄉親在死亡線上掙扎。一封家書使他寢食難安,他心如火焚找到時任湖北省建設廳長的老同學,以個人名義借了一筆錢,讓父親從江北買回兩船大米、三船大豆,在白霓橋、回頭嶺等地廣濟眾生。三萬余斤救命糧,一大批奄奄一息的鄉親得以生還,以至于多年后他才還完那筆巨款。他的眼前浮現那些劫后余生堅韌的身影,笑意,一點點爬上嘴角。
他想起長達60年的職業生涯中,經歷并參與過20世紀中國無數重大事件。他唯獨對1945年8月至10月重慶談判念念不忘。經過43天溝通談判,他與周恩來共簽《雙十協定》。簽字當晚,他與毛澤東侃侃而談。從三皇五帝的歷史到當時的時事政治,他廣博的知識和精辟的時政見解使毛澤東頷首微笑。那是他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次長談,每每想起,心中便有暖流流過。
陪伴他的還有一方“東湖長”的圖章。他所收藏的名貴字畫他都一一印上自己的簽章。一生珍藏的77件名人字畫他立囑贈予武漢大學,他看著這些字畫上“東湖長”圖章的時候,仿佛東湖就在眼前,仿佛看到那些年他在東湖在武大走過的腳印。他收集這些腳印的時候,內心的孤獨慢慢平復,他想,總有一天,他會回到武大,親手將自己連同畢生的收藏交給武大,可是,他沒能等到那一天,在他九十歲的時候,他把自己的肉身和遺憾留在臺灣島上,魂卻漂洋過海,到大陸的武大,生根。
西裝、領帶,厚厚的鏡片,堅定的目光,冷峻的面容,王世杰的銅像就是他一生的寫照。在武大校園蔥翠的古樹下,伴著學子的朗朗書聲,晨鐘暮鼓,歲歲年年。

成麗,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省作協第六屆高研班學員。2014 年入選湖北省青年作家定點寫作(系列散文)項目。2016年6 月簽約《散文選刊》原創版。曾任《長江文學》散文編輯,現任《云夢澤》雜志副主編。作品散見《海外文摘》《散文選刊》《長江文藝》《長江叢刊》《新作家》《旅游散文》《經濟日報》《湖北日報》《長江日報》《寶安日報》等。多次在國家級、省部級征文中獲獎。散文《農具》入選2014 年《中國散文大系》;《最后的花期》首發《長江叢刊》,后被《海外文摘》轉載,2015 年6 月被福建省福州市作為范文選入2014-2015 中考語文模擬卷。《家之南,是大幕山》入選多個版本后被收入全國高中生優秀(作文)范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