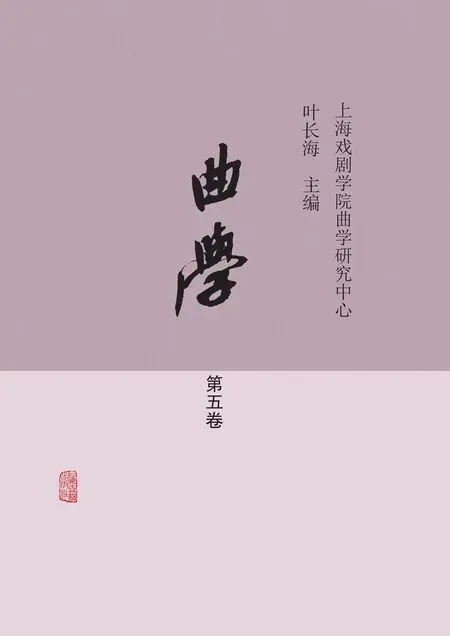曲學之曲藝音樂研究
——“南腔北調”論
莊永平
引 言
曲學,顧名思義就是研究“曲”的一門學科。“曲”,顯然是建立在中國文學史中,人們非常熟悉的“詩、詞、曲”的“曲”之上的,并以此為立足點和出發點來上溯下探,可以說涉及中國傳統聲腔音樂(甚至包括器樂)之一切。“曲”字的上溯最早只是作為彎曲、不正和曲折解。如《書·洪范》:“木曰曲直。”《左傳·僖二八年》:“師直為壯,曲為老。”《易·系辭》:“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辭源》,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455頁。由于音樂旋律線條的高低曲折,故而又用“曲”字來指樂曲或兼指旋律。如《樂記》:“如歌者,上如抗,下如隊(讀‘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釋》(上冊),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年,第282頁。古代樂官多由瞽者(盲人)擔任,而瞽官的工作就是采風、獻曲。如《國語·周上》:“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同上,第16頁。后來搞音樂就成為盲人的一條謀生之路。到了宋代,講唱文學幾乎是被盲人包攬了,有南宋著名詩人陸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詩為證:“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到了明代還是這樣,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記載有“陶真”,并為之下了定義:“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明) 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545頁。可見,人在喪失了眼睛的視覺之后,便專心于耳朵的聽覺,于是耳力也就格外地發達起來了。中國現代著名盲人二胡演奏家華彥鈞(阿炳)、孫文明創作的《二泉映月》、《流波曲》等優秀樂曲,都很能說明問題。其實外國也是一樣,意大利著名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被譽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說明人一旦致盲醉心于歌喉,連嗓音也會好起來,正是神妙得很,看來人的意念是真實存在的,且能發揮很大作用。“曲”者,到了漢魏時期就有了清商曲、西曲以及“相和歌”、“吳歌”等未以曲相稱之曲;再就是隋代出現的曲子詞,以及唐代達到高峰的歌舞大曲;直至宋代的詞體,發展到元代的曲體和明代的南北曲、昆曲。于是,“曲學”作為一門顯學,開始發軔。特別是到了南北曲、昆曲之后,民間的俗曲、時調等又開始活躍和發達了起來。這樣,廣義地說,曲學也就包括了戲曲、曲藝、俗曲、時調等聲腔音樂之一切了。而且,在明、清的一些曲學著作章節的最后,常又把器樂的“清彈琵琶”之類也記錄其中,說明“曲”從最早屬于純粹的音樂范疇,后來開始進入了文學領域,以至于一度成為文學的主體;再后來又漸漸回歸到音樂領域,把純粹音樂部分的器樂也包括了進去,這種現象確實十分有趣,也值得深入探究。實際上這些都離不開同樣處于聲腔之中的漢語,這一特定的以單音節詞根為主的語言與音樂的密切關系。換句話說,就是在聲腔中腔詞與腔調種種關系的對應、調整、演變的總體發展歷程,同時,器樂追求聲樂也是中外古代音樂所共同存在的現象。
曲藝音樂淵源
中國民族音樂通常分為: 民歌與古代歌曲、歌舞與舞蹈音樂、說唱音樂、戲曲音樂、民族器樂五大類型。*參見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編《民族音樂概論》,音樂出版社,1964年。當然,現在也有增添宮廷及宗教儀式音樂等作為類別的。那么,曲學大致也可以把它們列入其學科研究的范圍,只是單純地從音樂角度而言,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其中,說唱音樂就是“曲學”的主要部分。說唱音樂也即今天所稱的“曲藝”,其實,“曲藝”一詞大約是直到20世紀50年代后才逐漸普及的。“曲藝”的前身就是“說唱音樂”、“講唱文學”等的稱謂。之所以稱為“曲藝”,可能是為了與“戲曲”相對而言。顧名思義,“戲曲”就是戲與曲的結合,曲藝也就是說與唱的結合。因此,凡以說與唱為主的民間文藝形式都可以總稱為“曲藝”。問題是“說唱藝術”一詞既不能簡稱為“說藝”,也不能簡稱為“唱藝”。因為簡稱為“說藝”就變成純粹說話的藝術了,即使像今天以“說”為主的相聲,有時還是要說說唱唱的,只有戲劇中的話劇大概才是較純粹的“說藝”(還有表演藝術);簡稱為“唱藝”則變成了歌唱的藝術,這樣,又反過來排除了說唱藝術另一半重要的“說”的部分。而且,如果光以“說唱”兩字來對應“戲曲”,實際上戲曲中也有說(念白)和唱(唱腔)。因此,就選擇了戲曲與說唱都可以通用的歷史上涵義極其廣泛的“曲”字。于是,也就產生了“曲藝”這一名稱,成為各種說唱藝術的總稱,也就是“唱曲的藝術”。當然,與“戲曲”兩字的并列結構不同,它仍然是突出演唱的。不過問題在于,既然是說唱藝術的總稱,就不應再加“藝術”兩字組成“曲藝藝術”或“曲藝表演藝術家”等,這樣就有“疊床架屋”之嫌了。因為即便“曲藝”的“藝”作“技藝”講,但顯然強調的是“技”,是技術而不是藝術。因此,像《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中,把“曲藝音樂”、“曲藝說功”、“曲藝唱功”、“曲藝做功”,甚或“曲藝表演藝術家”都以“曲藝藝術”的總目標題統領之,這就不太合適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戲曲曲藝》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年,見目錄第15、16頁。其實取消這個總標題,如戲曲分類那樣,分為曲藝音樂(說功、唱功)、曲藝表演(做功)、曲藝表演家等或許更為合適。
說唱藝術的“說唱”一詞,大概最早見于南宋吳自牧的《夢粱錄》卷二十“妓樂”條:“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州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輩女童皆效此,說唱亦精,于上鼓板無二也。”*(宋) 吳自牧《夢粱錄》,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310頁。但其淵源則是極古的,現在一般認為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荀子的《成相篇》,還有那時盛行用散文(說)和韻文(唱)相間的文體形式——“賦”。到了漢魏時期的一些長篇敘事詩,如《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等,都對說唱文體及其音樂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當然,作為戲曲的一些源頭,如早在西周時出現的“倡優”與“俳優”,同樣可視為是說唱音樂的萌芽。尤其是后者常是擅長滑稽諷刺、插科打諢,有點像今天的相聲。因此,無論那時是“說”,還是“唱”,或是敘述的故事內容與表演形式,都成為孕育說唱藝術產生的溫床。而說唱藝術真正形成的契機,是隋唐時期的“說話”,以及寺院邊唱邊講佛經與世俗故事的“俗講”,其文體“變文”的出現,已經具備了后世說唱藝術的諸要素。到了宋元時期,不僅產生了“說唱”一詞,而且,其藝術的發展也達到了歷史上的高峰。據《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等書記載,當時的說唱藝術的品種極多,如說話、變文、史書、講故事、談經、學鄉談、說諢話、合生、商謎、陶真、涯詞,以及鼓子詞、纏令、纏達、唱賺、諸宮調,等等。其中,從聲腔形式上講,對后世影響最大的莫過于“鼓子詞”和“陶真”了,它們是現在頗具代表性的曲種“大鼓”和“彈詞”的源頭。如從音樂結構上講,“諸宮調”的層次較高,影響也較大。由于它集中了諸多的宮調來說唱而得名,運用的宮調多說明結構較為龐大,表現力也就較為豐富。像現存較完整的《董西廂諸宮調》,全本共用了14個宮調。不過,那時所謂的宮調轉換與我們現在的轉調概念并不相同的。因為傳統所謂宮調包括同宮與異宮的樂調在內,且以前者為多。同宮轉換僅是一種旋律樂句或樂段落音調式等方面的變化,如果認為這么多的調都是異宮調性轉換的話,那么,即使在今天的一劇音樂中,要轉用14個調性也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我國聲腔中文學與音樂的關系到了元代,又一次出現了分道揚鑣的現象。二者的第一次分離產生了“詞”,這一次分離又產生了“曲”。“曲”產生以后,文學主體的發展方向就較為明確了,除了歷來與音樂關系密切的詩、詞、曲之外,以書面文字的作品為主,產生了純文學的、散文化的小說(早期的所謂小說,仍是一種講唱文學的形式),它與音樂就很少發生關系了。當然,在聲腔特別是南北曲、昆曲中,文學的部分仍然是十分強大的。不過,到了這個時候,在人們的概念中,已經把聲腔中文學與音樂劃分為藝術的兩個不同門類。雖然其內核是兼有二者的(即唱詞與唱腔),但它的外殼是音樂,與聽眾直接接觸的傳媒是音樂而不是文學。唱詞(字)必須通過旋律曲調才能送到聽眾的耳朵里,不像小說那樣是直接通過眼睛來閱讀欣賞的。事實上到了明代,傳統的“詩詞曲”一路發展下來,從文學上講也已經越來越散文化、通俗化了。以前那種文學與音樂的演變方式似乎由此中斷,與此同時,民間大量的新型聲腔形式似乎突然冒了出來,實際上可視為是傳統演變的一種反動。明陳宏緒《寒夜錄》引卓珂月的話說:“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為我明一絕耳。”*引自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編《民族音樂概論》,音樂出版社,1964年,第8頁。這段話確實道出了當時文學與音樂發展的真實情況。如果僅從散文化、通俗化上講,尤其是后者它們是一脈相承的。問題是倒過頭來謀求長短體向整齊體的回歸,這種直接返回的方式顯然是走不通了。于是,就出現了在民間聲腔基礎上,再一次完成這種長短體向整齊體的回歸,這是依據民間聲腔的崛起,采取另起爐灶的辦法。當然,表面上看似乎是這樣,但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由我國語言文體的特殊性所決定的。這里是否也可套用一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句古話,聲腔上也是“整久必散,散久必整”。長短與整齊句型的反反復復,層次的穿插,都是與漢語單音節詞根占絕大部分以及單字組合上的靈活性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這也是造成文學與音樂形式豐富的主要原因。甚至今天的歌曲,唱詞的不整齊在腔調上也常納入整齊的樂句,這又是一種腔詞的對應關系,顯然是越來越傾向于音樂的方面。
明代《掛枝兒》《羅江怨》等實際上是一種民歌。那時還沒有“民歌”這一稱呼,相當于今天“民歌”的只有“山歌”。在城市里有了伴奏后就有了“小曲”、“俗曲”、“小調”等稱謂。小曲在內容上不斷地與時俱進,也就有了“時曲”或“時調”等名稱。這些腔調雖然常以民歌及民間歌曲形式來演唱的,但也常成為說唱藝術和戲曲藝術爭奪的目標。從腔調結構上看,說唱音樂中曲牌體的成分較多,但是,它已不是南北曲、昆曲中的那種曲牌體,它僅是將這些民間廣泛流傳的只(單)曲(獨立一曲),作為曲牌形式來演唱而已,有的又可能將這些只曲發展成為一種板腔體結構了。如果從發展進程上來看,民歌、小調演變成說唱體大概是其第一步,第二步再通過說唱體而進入戲曲之中。當然,有的時候這種發展經常是并行不悖的。據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時尚小令”(即“小曲”)載:“元人小令行于燕趙,后浸淫日盛,自宣(德)正(統)至成(化)弘(治)間(原為“后”字改),中原又行《鎖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自茲以后,又有《耍孩兒》、《駐云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明)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8頁。后來清劉廷璣《在園雜志》更直接指出這些小曲不同于昆曲的曲牌:“小曲者,別于‘昆’‘弋’大曲也。在南則始于《掛枝兒》。……一變為《劈破玉》,再變為《陳垂調》,再變為《黃鸝調》。……在北則始于《邊關調》。……再變為《呀呀優》。《呀呀優》者,《夜夜游》也,或亦變聲之余韻‘呀呀喲’,如《倒扳槳》、《靛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高》一種。”*(清) 宋犖《筠廊偶筆》、劉廷璣《在園雜志》,蔣文仙、吳法源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7—128頁。據極不完全的統計,到清時這類小曲至少有219曲。*參見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下冊),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第757—759頁。這些小曲在那時以及后世就被作為演唱的養料,廣泛而大量地運用于說唱音樂之中。
曲藝音樂特點
要說到曲藝音樂的特點,自然必須從“說”和“唱”兩方面來分析。首先,就是它的“說”的音樂性。北方曲藝如很多鼓曲,就有所謂散白、韻白、夾白等“說”的部分。散白就是大白話,不過任何大白話到了舞臺上,與生活中多少會有所不同。在曲藝中它被納入到整個說唱的范疇之中,尤其是北方曲藝不知不覺說著說著就唱了起來,這種“說”與“唱”的銜接可謂天衣無縫,說明這種“說”已具備了一定的音樂性,主要表現在字的調值趨向與銜接上,十分自然、自如、自覺,字調稍一夸張即所謂吟誦成腔也。另一種就是韻白,與戲曲中一樣特別講究字的抑揚頓挫、韻律線條等,這樣也就更能發揮它的音樂性了。然而,曲藝中最具特點的,大概也是其所特有的,就是一種被稱為“夾白”,即夾在唱腔中間的各種說白形式。這種說白大致分為帶節奏性和不帶節奏性兩種,前者與音樂結合得較為緊密;后者與唱形成對比,生活氣息較濃些。因為,我們知道,語言字調是一種連綿進行方式;音樂則是一種階梯進行方式,故稱為“音階”,這是不相同的。但是語言和音樂,特別是有聲調語言更可以互相靠攏,例如,將聲調引申至一定的音的階梯狀態;反過來音樂多用滑音來模仿語言連綿進行方式,等等。上面所說的“說著說著就唱了起來”,就是語言靠向音樂的明顯跡象。當然,這種形式在北方言中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容易成功的。表現上有所謂的“半說半唱”,更有“如說似唱”、“說唱不分”等,這是“說”與“唱”結合的種種高級形式。因此,通常把它們歸入到“唱”的部分中。實際上無論是歸在“說”或“唱”中,它就是介乎于二者之間的現象。但是,從記譜上看,二者還是能分清的:
例一
(1)
《林沖發配》

(2)
《秀才過溝》

上例(1)是在腔調中夾帶有節奏性的語言,這種語言也就是夸大字調,盡可能地向音樂腔調方面靠攏。也就是拉長聲調幅度,夸大它的調值趨向,有的就納入到音的階梯范疇之中了。上例(2)是反過來音樂腔調上多用裝飾滑音,來模擬語言的連綿進行方式,使人感到既像是在“唱”又像是在“說”。只是在不加裝飾音的地方,如“本姓、人稱、書、子百家”等處,才顯示出音的階梯形式。這些往往混雜在一起,所謂說說唱唱、由說至唱或由唱至說,有很多層次坡度,就看你如何來操縱表演了。然而,在南方曲藝中的說白,從音樂性方面來說就要遜色多了。主要是因為南方言字的調值差很小,你無論怎樣使它婉轉起來,就是達不到北方言那種程度。而且,它甚至還必須反過來借助于音樂的旋律,才能使語言的音樂性有所發揮。例如,南方言的入聲字本身就根本婉轉不了,它是要在斷音后靠旋律,來引申使其婉轉起來的。不過,不能婉轉卻也另有一種特殊的字調韻味,特別與其他字調連接時,一種“重煞”的對比之美常常油然而生。其實,像蘇州評彈中就有所謂的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襯白、托白等,這些大都與曲情表演有關,有的是第一人稱與其他人稱上的區別等,與唱腔音樂的關系是不大的。只有類似戲曲中的上韻、叫頭等,才與語言的音樂性有所聯系。因此,所謂“南腔北調”,雖然南方曲藝聲從口腔中發出,但字調趨向不明顯,故用“南腔”一詞就是強調了口腔的發聲而已。而北方曲藝同樣聲從口腔中發出,但字調分別明顯,常婉轉成腔調,故用“北調”一詞就是強調了口腔中的字調分別,看來,古人的用詞確實是既形象又精準。
其次,就是“唱”的部分,從結構上看,大致有下面幾種形式: 一是獨曲體,整個音樂只有一個曲調重復演唱所構成,與唐、五代的“變文”以及宋的“鼓子詞”等關系密切,現在北方曲藝中如岔曲、樂亭大鼓、北京琴書等中使用較多。二是聯曲體,整個音樂由若干牌子小曲并列組成大型套曲。通常有引子性質的“曲頭”和尾聲性質的“曲尾”,中間則聯合若干成套曲牌。這種結構形式與宋代以來的“纏令”、“纏達”以及“賺詞”、“諸宮調”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如單弦牌子曲、四川清音、湖南絲弦等中使用較多。三是板腔體,整個音樂是以某一曲調為基礎,衍化出若干板式按漸層節奏發展原則組合而成,它和戲曲的板腔體屬同類,如京韻大鼓、梅花大鼓、河南墜子等中使用較多。四是主插體,就是在獨曲體或板腔體中間,插入若干其他作為附屬性質曲調的結構,如蓮花落、漁鼓道情等中使用較多。曲牌體類的旋律進行,自然與其結構是互為表里的。唱腔常是運用多種曲牌的聯綴,一個曲種運用的曲牌常較固定,連接的次序也常相對有定,這是由各曲牌的性格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在運用上是約定俗成的,其間主要包括旋律進行上的聯系。凡結構連接不上的、旋律音區不合的、性格情趣相異的,自然就不可能組合起來運用的。這些,顯然是由詞曲音樂一路發展而來的緣故。板腔體類的主要是發展出一些快慢的板式,如慢板、緊板、垛板等。于是,形成各種腔型,如平腔、落腔、長腔、挑腔、甩腔等,以及帶表情意義的歡腔、悲腔、起伏腔等,這些大都是明清以來在民間小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很多介于它們之間的各種形式,通常只能稱為綜合體,如南方彈詞一類的就較多運用這些結構。這種唱腔常強調整體較整齊的句型曲式結構,這是與詞曲音樂不同的主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說唱音樂旋律結構中,比較富于中國特色的就是那種“起、平、落”的結構形式。也就是起腔是上句,音調上揚;落腔是下句,音調下墜;惟平腔旋律性不強,多作宣敘格式。這種分為三個部分的結構形式,與中外其他樂曲中常是成雙結構有很大的不同。
京韻大鼓音調及演唱特點
明時北方的“俗曲”、“小調”等進入了說唱音樂領域后,到了清代延續至民國時期,發展出最具特點的就是被稱為“大鼓”的曲種了。雖然從宋元的“鼓子詞”到后世北方的“大鼓”曲種,它們并未有那么直接的歷史淵源,但是,北方擊鼓伴唱的習慣實際是早就存在的。如宋耐得翁《都城紀勝》載:“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宋) 耐得翁《都城紀勝》,《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96頁。這不就很像今天演員親自執板擊鼓演唱“大鼓”的那樣?現在的“大鼓”曲種通常分類的習慣,是以伴奏樂器為主要標志的,如木板大鼓類的京韻大鼓、木板大鼓、梅花大鼓、滑稽大鼓、奉天大鼓、河南墜子等;鐵板大鼓類的犁鏵大鼓、西河大鼓、樂亭大鼓、膠東大鼓、京東大鼓等。其中最著名、藝術成就最高的非京韻大鼓莫屬了。京韻大鼓所用的鼓比其他大鼓曲種的為大,音量也比較宏闊些。其他的伴奏樂器有大三弦、四胡、琵琶、木板等。在曲式上京韻大鼓已是一種板腔體結構,這種結構較之曲牌體結構,在腔調旋律發展上更具邏輯性,節拍節奏更為自由,因而,于敘事性表現的同時,更充分地發揮了它的抒情性和戲劇性。其腔調常分有平腔、挑腔、長腔、甩腔、拉腔、落腔六種腔型;慢板、緊板、垛板三種板式,以及極富中國特色的起、平、落的段落結構形式。現在于整個聲腔音樂來分析,可以從腔調的縱橫兩個方面,即縱向方面的腔格旋律進行及其變化,主要是突出與唱詞字調的密切關系;橫向方面的就是節拍節奏的變化運用,包括起腔方式和多種板式的運用等。
在腔格旋律上,可以說京韻大鼓演唱旋律的音域、音區運用并不是很寬的。男聲猶如京劇的老生,女聲全用本嗓演唱,與京劇老旦相比,女聲主要以中低音區和較寬的音量取勝,不像京劇老旦那樣,時不時以飆高腔、拉長腔或疊垛板等來發揮。因此,演唱中通常沒有高音區高遏入云的行腔,有的則是中低音區意味深長的回旋。然而,其唱腔最主要的特色,就在于聽他(她)那種“擺字”(即字在音樂旋律中的腔格位置與旋法,以及字與字的節奏關系)的高低巧妙和準確,還有就是演唱上顫音等技巧的發揮運用。下面以劉寶全演唱的《丑末寅初》片段為例:
例二
丑末寅初
劉寶全演唱


風雨歸舟
駱玉笙演唱


京韻大鼓在演唱旋律上的突出技巧,就是被總括為“潤腔”的運用。“潤腔”一詞最早來自明代戲曲理論家王驥德《曲律》一書,他在“論腔調第十”中對明代以來聲腔音樂的豐富性與復雜性作出了正確的判斷。他說:“樂之筐格在曲,而色澤在唱,古四方之音不同,而為聲亦異,于是有秦聲,有趙曲,有燕歌,有吳歈,有越唱,有楚調,有蜀音,有蔡謳。”*(明) 王驥德《曲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四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114—115頁。這就是說,唱腔音樂設計好(即“筐格在曲”)以后,就看演唱者如何加以潤色演唱(即“色澤在唱”)了。于是,同樣的俗曲、時調,由于四方之音的不同,就流變出各種不同的曲種腔調,還有不同演員的演唱流派風格,等等。20世紀60年代初,于會泳根據王氏的論述提出了“潤腔”命題,并認為這是一個頗為復雜的問題,有待后人建立我國聲腔音樂上的“潤腔學”。“潤腔”也就是唱腔上各種裝飾旋律的手段與方法,在西洋音樂中“活裝飾法消逝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后來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即歐洲復調音樂對和聲的日益加深的依賴”*〔匈〕 薩波奇·本采、司徒幼譯《旋律史》,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年,第274頁。。而我國因長期處于單音音樂時期,就特別強調旋律的那種“活”的裝飾作用。當然,這不僅僅是單純地出于音樂曲調裝飾上的需要,可以使旋律線條更為順暢、流利;更主要的它是漢語單音節字于音樂旋律上的一種反映需求。因為音樂上多用裝飾滑音之類,實際上就類似語言字調的銜接進行,對音樂語言的表達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曲藝與戲曲唱腔上這種裝飾音的運用,首要的是具有一定的正字作用。這種輔助字正的裝飾音,通常就用于字頭上,在出字的一瞬間,短暫的裝飾音能使字音準確地唱出。例如,例二的“扶”字是個陽平聲,就運用了一個小三度的下倚音,來強化它的陽平字調。又如,“猛抬頭”的“頭”字就用復倚音來強化它的陽平字調。這種用于正字作用的裝飾,在唱腔中是數不勝數的。具體地說就是各種裝飾倚音的運用,其中就有上、下、快、慢、單、復等的區分。各種字調裝飾的方法不一,但都是根據不同的方言以強化各字調的趨勢。京韻大鼓屬于北方言中的北方方言分區,通常陰平字不太需要用裝飾音來輔助它的字正;陽平則用下倚音或復倚音;去聲多用上倚音;上聲多用下倚音或復倚音等。這里,也不可能來詳細闡述具體運用的情況。其次,這種旋律裝飾又是出于音樂本身的需要,一般用于出字以后及純音樂部分的拖腔旋律上。這種裝飾基本上常就是種種演唱技巧的運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種顫音的運用。我們知道,我國曲藝、戲曲以及民歌等唱法,不像西洋美聲唱法那樣,從頭至尾都要用顫音來裝飾美化的,他們稱為“vibrato”即顫吟。正是美聲唱法時時存在著這種顫吟,使得其他的顫音就不太好用了。因為這不僅有疊床架屋之嫌,而且確實也很難再疊加上去。但是,我國的民族唱法則不同,由于通常發出的聲音是平直的,沒有那種顫吟的現象,因此,當需要運用顫音時才加上去用的,這當然又是一番演唱風景了。實際上現在的流行歌曲唱法,包括西洋流行歌曲的聲音,大都也是不用這種常規顫吟的。可見,這里面確實存在著各有利弊的問題。那么,京韻大鼓演唱上最具特色的就是一種后顫音的運用,如上例的“雨”字就是運用了后顫音,緊接著的“淋”字則運用前顫音。而顫音常也有上、下、長、短、快、慢等的區分,這就大大增加了演唱的韻味。由于后顫音往往用在出字之后,既不影響字正,又可裝飾美化旋律,因此,京韻大鼓的那種獨特而意猶未盡的韻味,大都就是由這種后顫音運用所帶來的。

蘇州彈詞音調及演唱特點
蘇州彈詞現在簡稱“蘇州評彈”或直稱“評彈”。所謂“評”者,論也,以古事而今說,再加以評論即是。而“彈”字,顧名思義就是在講故事的中間,穿插有用彈撥樂器伴奏的演唱,這樣使所講的故事更為聲情并茂、繪聲繪色。這個“彈”字主要是指彈撥樂器的三弦和琵琶,而那個“詞”字就是指唱腔的唱詞(字)。“評彈”一詞大約是20世紀50年代后才啟用的。實際上它是“評話”和“彈詞”的合稱,前者就是所謂的“說大書”,表演中有“評說”與“說表”就是沒有“唱”的成分;后者就是所謂的“說小書”,是有說有唱的。由于傳統認為“評話”所講的是以帝王將相、叱咤風云人物的故事為主,故稱英雄氣概、金戈鐵馬之事為大;而“彈詞”所言的是以社會百態、人情世故的故事為主,故稱風流倜儻、私定終身之事為小,其實這大、小的說法并無高低之分。而用“評彈”一詞單指以前的“彈詞”,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因為“評彈”中也是有說表的“評”與“話”的部分。這樣,又可以分為“評話”和“評彈”兩種形式。前者僅指單純的評與說;后者也有“評彈唱腔”、“評彈曲調”等稱謂,這是排除了“話”的部分而特指其唱腔了。由于“評彈”起源于山明水秀的江南水鄉——蘇州,因而被冠于蘇州評彈。又由于近現代蘇州評彈在上海達到了其藝術發展的高峰,因此,它名稱的前置地區冠名蘇州兩字,往往也就被省略了,常就以“評彈”兩字概括之。當然,如果使用以前的“彈詞”名稱也是可以的,但必須冠以蘇州兩字。因為“彈詞”不僅有蘇州彈詞,還有揚州彈詞、溫州彈詞(南詞)、長沙彈詞、福州彈詞,等等。彈詞的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變文”,再就是在宋代“陶真”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載:“聽‘崖詞’只引子弟,聽‘陶真’盡是村人。”*(宋) 西湖老人《繁勝錄》,《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120頁。這是最早出現“陶真”名稱。上面所引用南宋著名詩人陸游的詩,就是村民們在聽蔡伯喈故事,聽得如醉如癡的情景。后來元代高明將蔡中郎的故事改編成《琵琶記》,成為明太祖朱元璋所說的“富貴人家不可無”的戲曲珍品。其中第十七出《義倉賑濟》中真的還唱了幾句“陶真”的調兒,可惜曲調不可能被記錄下來。元末文學家楊維楨的《四游記彈詞》(《俠游》《仙游》《冥游》《夢游》,他僅刻其三),是現知最早的以“彈詞”命名的唱本。再后來明楊慎編寫《二十四史彈詞》,其體裁與現在的彈詞已很接近。因此,就歷史的發展來說,元、明的“陶真”是“彈詞”的前身,而明、清的“彈詞”又可以看作是“陶真”的綿延,二者發展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到了清代彈詞也就發達了起來,其中自然以蘇州彈詞為最。
彈詞的唱詞是由上下句反復構成,又以此變化出很多其他不同形式的句型結構。其中有一個上句加兩個下句;或兩個上句加一個下句的,被稱為“鳳點頭”的句式頗具特點。另外,樂句的最后一字于節拍上常斷開,單獨演唱句末字的所謂“拖六點七”的處理別具一格。現在也可以從縱橫兩個方面對唱腔加以分析。下面以蔣月泉演唱的《寶玉夜探》片段為例,蔣在字調安排及演唱等方面,頗有京韻大鼓的風范:
寶玉夜探
蘇州彈詞

注: 為了與北方言對比,按新四聲標記聲調,入聲字見解釋。

蘇州彈詞的節拍形式,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南方腔調吟誦性強的特點。雖然像北方的京韻大鼓等腔調也具有吟誦性強的特點,但是,這種特點似乎主要是反映在縱向的腔調旋律方面,如半說半唱、似說似唱等,這是因為北方言字調的調值相差大,因此往往吟誦成腔。然而,在節拍方面他們反而比較早的就被納入到了規整的板眼之中,于吟誦成腔中能體現出一定的板眼律動來,因而常常出現了正反拍起腔及“停聲待拍”等現象。而蘇州彈詞等南方腔調,縱向方面不如北方腔調那樣活躍多變,因為南方言字調的調值相差很小,往往吟誦不像北方語言那樣高下閃賺、婉轉成趣。而且,在節拍方面也不容易被納入到板眼律動中去,相反,它常是根據唱詞的結構,主要是句逗與分句逗來劃分節拍的。例如,評彈唱腔中凡是“拖六點七”的落腳字都應該落在板上,然后拖到眼上的,如上例的“魂、清”字那樣,如果落在眼上拖到板上就要作節拍的調整了。當然,像徐(云志)派唱腔,其過門與通常的不太一樣,落在眼上不一定需要調整,落在板上倒是需要調整的。總之,為了句斷與過門相協要合符唱詞的規律,故而經常出現混合節拍形式。因此,像“結成”兩字用了三拍子,使“冰”字能落在板上,后面的句子(即“月色迷蒙”)就在板上起唱。但是,像第三句“一陣陣朔風透入骨”用了兩個三拍子,如不用兩個三拍子(3×2=6),按原來的三個兩拍子(2×3=6),實際上似乎也沒有翻板,那為什么要用兩個三拍子呢?說明在南方唱腔上,凡是句子的第一字,或其他分逗詞組的第一字,均應該放在板上的,如此句的“一、朔、透”那樣,否則就不很舒服了,但在北方唱腔上就不會產生這種感覺。其實,像蘇州彈詞的這些南方唱腔,都是以腔節分逗詞組(如2+2+3等)來劃分節律的。由于詞組節律本身是有單雙之分的,故而就造成了混合節拍的產生。因此,聽蘇州彈詞時不可能像聽京韻大鼓等北方腔調那樣,可以從頭至尾按板眼節律來打拍子的,那種混合拍式會使拍子打不下去的,只有根據唱詞的各詞逗節律來打才行。當然,偶爾正好單雙詞組相協不出現混合拍式,也能按板眼律動來打節拍,但這種情況似乎并不多。歷史地看,我國戲曲、曲藝唱腔的發展,特別是詞曲長短體要合符板眼的節拍規律,都要經過節拍規整的協調過程。昆曲是較早經過“點板眼”的,其“點”的過程應該說就是有所放棄、有所保留的,這只要看看那時魏良輔等人是如何來論述這種過程的。他在《曲律》中寫道:“其有專于磨擬腔調,而不顧板眼;又有專主板眼而不審腔調,二者病則一般。惟腔與板兩工者,乃為上乘。”*(明) 魏良輔《曲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五集,第6頁。此話講得非常辯證。也就是說魏氏是經過二者的協調與平衡,才使原來幾乎“罕有節奏”的昆山腔等南方腔調,成為板眼較為規整的昆曲等戲曲聲腔的。現在,一些后起的戲曲劇種如滬劇,它原先就是一種民歌調或說唱腔調,在成為戲曲腔調的過程中,還是或多或少要經過一番規整板眼的工作,使唱腔更合符于板眼規律。滬劇中有經驗的琴師總結出一些方法,如“較多的是逢單的字‘切板’(筆者注: 即下板),即在句式的一、七、五、三字‘切板’;如有雙字上‘切板’,那么句式定有變化,屬于三字句、四字句,或有加帽、搭尾、插腰等的例外句式”*朱介生、徐音萍《滬劇音樂簡述》,上海音樂出版社,1988年,第204頁。。像滬劇的[長腔慢板]尤其需要這種“點板眼”的規整過程,這實際也是唱腔板腔化的重要工作之一。比較典型的如王(盤聲)派的代表作《白兔記·劉智遠敲更》的[長腔慢板],要把它納入到規整的板眼節拍之中,就要再三權衡演唱、伴奏等各個方面。也就是說有的地方不能唯演唱馬首是瞻,有必要約束一下演員,節拍節奏不能唱得過于自由,常常要“停聲待拍”,不能產生脫板、翻板的現象;但更多的是伴奏要配合一下,過門可以適當增長或減短些,諸如此類。*莊永平《滬劇唱腔賞析》,上海音樂出版社,2013年,第29—33頁。總之,由于說唱聲腔不像戲曲聲腔那樣較為固定,它的板眼的靈活性更強,常沒有經過或有時也沒有必要去進行那種“點板眼”的規整過程,因而大都不一定合乎板眼的規律。當然,隨著音樂的發展在符合唱詞節律的同時,如果亦能合符音樂的板眼律動則更好。因為如果配上大樂隊伴奏的話,就涉及到旋律縱橫兩方面的交織相協、樂曲織體細節上互相配合與平衡等問題,自然是合符現代節拍規律的就更好些,使聽眾聽起來也就更為順暢些。
結 語
綜上所述,曲學之曲藝音樂是很有研究必要的,由于說唱音樂中音樂與語言結合得特別的緊密,可以知道漢語單音節為主的語言,在腔調表現上的特殊性所在。像京韻大鼓與蘇州彈詞為什么有那么持久的藝術魅力?與這種腔調表現上的特殊性密切相關。但是,我們也要知道它們處理上的異同。例如,在縱向旋律方面,有些由方言特點所造成的,在運用上加以發揮是極其自然的。像“斷”字(屬“鵑園”轍)在南方唱腔中常是拖音發揮的,如滬劇《為你打開一扇窗》中的“扇”字,與上例“斷”字等就常拖腔加以發揮。相反,北方聲腔中常常發揮的則是江陽、一七等轍,這無不說明南北字音的不同,處理上也是判然有別的。在橫向節奏節拍方面,南方唱腔中兩個字前一字如是入聲字,由于不太容易拖音,于是就造成處理上兩字緊靠的現象。如上例的“月色、欲斷、朔風”等的切分節奏,在滬劇等南方唱腔中也是常見的,等等,諸如此類在曲藝聲腔的處理上都是不足為奇的。又如,在橫向的節奏節拍方面,北方言容易吟誦成腔,其腔調常是眼上起或反拍上起,這樣才顯得氣粗力大。正如交響樂隊在板上全奏一個強音,不如弱拍上加一個用定音鼓或樂器滾奏,推出這個強音顯得更強烈些。說明北方唱腔板眼的輕重長短與節奏節拍上的聯系,猶如字音被推出來的那樣似乎是比較強的。而南方言就不太容易吟誦成腔,即使成腔的腔型也比較狹窄,其板眼的律動性也不強,故而常造成混合節拍。說明南方板上起的不一定強而是顯得平穩,北方眼上起的并不弱而更顯氣盛。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板上起的就強,眼上起的就弱,其實恰恰相反,是板上起的平穩,眼上起的氣盛;平穩者并不示弱,氣盛者則更逞強。正如中西音樂的“強弱”與“尺寸”(長短)并不總是矛盾的那樣,它們也是經常可以同一的,但時時又會顯示出它們各自的特點來。至于談到南北說唱音樂的韻味及藝術趣味則各有千秋,特別是南北語言字調造成的趣味,如北方言的去聲和南方言的入聲,常常聽來韻味就迥異,正可謂“南腔北調,各領風騷”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