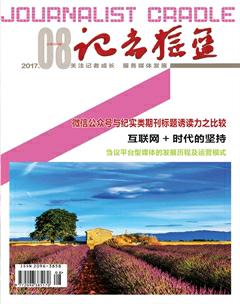城市臺法治節目如何“突圍”
馬維慧
【摘 要】城市臺法治類節目曾經風光無限,節目形態多樣,但近些年,相關節目大有縮水之勢,是節目本身的問題,還是大勢所趨?本文嘗試探索城市臺法治節目如何走出困境,如何突圍。
【關鍵詞】法治節目 城市 突圍
法治節目是重要的電視節目形態,但是地方臺的法治節目則讓這個廣義上的節目類型有了特殊的要求和意義。地方臺有沒有必要辦法治節目?或者說,一旦辦了法治節目,地方臺如何運營?如果說地方臺的法治節目是一座城,現在,它的狀態是被圍,突圍似乎是地方臺法治節目的唯一出路。
一、“被圍”之困
相對于娛樂節目的堅挺,法治類節目一直處于疲軟狀態,除了幾檔觀眾耳熟能詳的節目,如央視的《今日說法》《法治在線》,北京電視臺《法治進行時》等,其他的法治節目基本上處在灰色地帶,收視低迷、節目關注度低。這其中原因,業內人士給出的原因不外乎選題狹窄、同質節目競爭、內容娛樂性差等。其中選題單一成了法治類節目發展的瓶頸。
盡管處在疲軟的狀態,但是在我國社會發展的現狀下,人們需要法律所代表的正義和約束力,因此,法治類節目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據統計,我國大約有200個法治欄目,近10個以法治或法制命名的頻道。代表性的法治節目形態不外乎以下幾種:(1)案例展示加演播室說法,以央視《今日說法》為代表。(2)單純案件展示,中間穿插法律專家說法,以上海臺《案件聚焦》為代表。(3)案件加專家說法加觀眾互動的板塊式結構,突出新聞性,以央視《法治在線》為代表。(4)主持人以說書方式講述案例,演播室嫁接談話節目形態,主持人、嘉賓、觀眾就法律和社會話題展開討論,以2006年8月改版前重慶電視臺《拍案說法》為代表。(5)法治新聞加專題的組合,類似于民生法治新聞,以北京電視臺《法治進行時》為代表。(6)記者出擊,與案件當事人一道行動,攝像機跟蹤紀錄的體驗式報道,以長沙政法頻道《主播出發》為代表。(7)由虛擬主持人引入,以欄目劇的方式表現帶有推理懸疑的偵破故事,以浙江臺《大偵探西門》為代表。(8)根據真實案例改編,演播室嘉賓、觀眾組成探案俱樂部,對案情進行偵探推理,以江蘇衛視《探案俱樂部》(現已停播)為代表。
這些形態歸納起來就是以案說法或者是法治現場,基本上以故事和現場直擊吸引觀眾。分析這些法治節目,能夠完全依靠自采的微乎其微,大部分的節目來自于各個臺的互相交流。題材一直是法治節目發展的瓶頸,不同于民生新聞,法治節目的選題要緊緊和法相關,對于地方臺來說,如果僅僅立足于本地,題材上就受到很多的限制,例如,與當地公檢法合作的深度,受當地新聞環境的限制程度,可采訪和播出的題材的數量等等,這使地方臺的法治節目或者輕描淡寫,或者慢慢流于民生新聞。法治節目的定位是明確的,但是地方臺的法治節目卻一直游走在定位模糊的狀態下,定位一旦清晰就會被各種條件限制甚至窒息,只有在模糊的狀態下,地方臺的法治節目才能步履維艱地走下去。
二、如何“突圍”
對于法治節目如何“突圍”,業內人士給出了各種不同的意見,大家都認同的幾點包括:首先,法治節目要以故事吸引人;其次,法治節目要表現人文關懷;再次,法治節目要追求現場,先聲奪人。當然在制作手段上要運用多種敘述方式和電視表現手段。看著業內人士開出的藥方也不難發現,對于法治節目的突圍,這些辦法指向性不強,針對性不強,這些辦法同樣適用于其他類型的電視節目。對于地方臺來說,如果選題源都缺乏,何談方法呢?
解決問題,筆者認為首先要改變觀念,樹立大法治概念。這也就是對法治節目定位的模糊化處理。地方臺辦法治節目不見得有那么多的法治案件,也不會有很多可以拍攝的庭審現場,能夠找到的選題,與法最密切的大多也都是百姓之間的民事糾紛,因此,對法治的理解,就不能僅僅限于法條的解讀、法治案件的法理,而要超越于法但又不割斷法。超越于法,是說法的概念不是枯燥的法條,法也不是若干法條的集合,它是一種規范、規則、常規、模范、秩序,在這個框架內,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生活,并且這種自由不影響和損害他人的自由。立足于這樣的法治點,我們的眼光就可以不局限于單個的事件和案例,而可以從社會眾多的事件中發現法的存在。
其次,地方臺辦法治節目,應該重解讀大于重自采。這是解決選題困境的一個辦法,即便是本地自采可以滿足制作播出的需要,也有可能會陷入選題同質化的泥淖,或者讓節目氣量狹小。因此,地方臺在辦法治節目的時候,可以在大的法治視角下,選取全國或者世界上有重大意義或者對地方有借鑒意義的法治事件進行與眾不同的解讀,讓解讀成為對法治事件的深度加工,讓一個普遍的事件展現不同的意義。這些法治事件來源于網絡,編輯會給出比較詳細的事件信息,這些事件信息是大眾化的、普遍化的,是明顯的事實呈現。重要的是這些信息背后的情與理、法與情、法與理,它們就像是海底的冰山,需要編輯、記者發現這些潛文本。如何發現?在地方臺中,有的電視臺采取的方法是記者用評論的方式發現,依靠的是團隊自身的力量,這種方式投入的成本不大,但是解讀的深度受記者、編輯自身素養的限制。有的地方臺聘請觀察員來解讀,這些觀察員是來自于當地各大律師事務所的知名律師。他們對法理的解讀有一定的深度,而且比較權威。通過解讀,每一個看似傳播了很多遍的新聞,到了這里就有了更深的落腳點。
再次,地方臺辦法治節目,重說事也要重說理。目前,各種類型的電視節目都把故事性作為衡量一個節目好壞的標準,講“好”故事和“講好”故事成了電視從業人的追求。地方臺的法治節目,講故事的居多,而且隨著電視技術的發展,制作手段的提高,電視從業者講故事的水平和包裝的水平都一山更比一山高。然而現實是不是每一個地方臺都有包裝和講故事的高手,也不是每一個地方臺都有最先進的設備,如果這些條件都無法具備,法治節目何以維系?如果有故事我們依然要講,如果故事匱乏,說理也不妨是一個吸引眼球的手段。法的本質就是理,故事不過是理的外衣,但是現在,法治節目大多以故事為主,理反而退居幕后。說理的方式有很多,以故事說理是比較流行的,還有一種方式是觀眾的意見表達,記者把觀眾就某一個問題或者事件的意見搜集過來,經過有分析地編輯可以形成一種以民間聲音為主的觀點。盡管法律點不是每一個人都熟知,甚至它對于大多數人是陌生的,但是對一個事件,每一個人都能夠憑著自己的經驗進行分析,這種經驗是最貼近地皮的也是最具有溫度的,當編導后期重新組織、篩選這些經驗的時候,對法理的民間感悟也就呈現出來,不管這種感悟是偏頗的還是錯誤的,因其具有廣泛的認同性,因此它是一個階段大多數觀眾的意見流。等到電視節目對這些感悟正本清源,觀眾就能夠更深刻地認識法理并理解它。
第四,地方臺辦法治節目,別忽略幫忙的含義。電視節目的形態與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定的關系,當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社會矛盾、貧富分化明顯的時候,人們對公平、正義的呼喚就相對強烈,對媒體的依賴就相對緊密,媒體在觀眾的眼中就是推進問題解決的助推器,因此,幫忙必然成為地方臺辦好法治類節目不可忽略的一個方式。法律服務更加貼近,服務對象更加直接,服務效果才能立竿見影。
法治類節目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普法,如何普法,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每一個地方臺所采取的方式是不能一樣的,法治類節目想吸引觀眾的眼球,靠眼花繚亂的形式是不適合的,只有讓法變得深入淺出,并能得到更廣泛的傳播才是硬道理。
(作者單位:延邊電視臺)
【參考文獻】
[1]柯 澤 廣播電視節目策劃與創新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喻國明 傳媒變革力—傳媒轉型的行動路線圖 南方日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