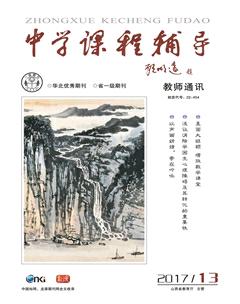綱目并舉,文言并重
趙滿麗
文言文該如何上才能上出語文課的味道來?一直是困擾一線語文教師的一個話題,如今的語文教學越來越重視學生對傳統(tǒng)文化的學習和繼承,文言文在語文學習和考試中的分量也越來越重要,可是如何在文言文學習中踐行《語文課程標準》所提出的:語文教學應致力于學生語文素養(yǎng)的形成,卻是我們值得研究和思考的一個重大命題。
傳承民族文化,吸收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本應是我們進行文言文教學的主要目的。但在許多文言文教學的課堂,教師上課時往往將重心放在前面“言”的部分:實詞、虛詞、一詞多義、詞類活用、通假字、古今異義、特殊句式等,而對“文”的部分卻往往一筆帶過。“言”固然重要,沒有“言”何來“文”,但文言文,尤其是選編進教材的文言文,大多是文質(zhì)兼美,意蘊豐富而且結(jié)構(gòu)又精巧、寫作技法高超的名家大作,學習這些文言文,我們不僅可以學習到古人遣詞造句的精妙,還可以學到前輩起承轉(zhuǎn)合的磅礴氣勢和駕馭文章的絕妙,這不僅是我們現(xiàn)代文閱讀寫作中著力學習借鑒的,也是我們承傳傳統(tǒng)文化精髓之所在。
一、文在左,言在右,文言并進花香滿徑
文言文距離我們時間比較久遠,又脫離我們的口語交際,學生即便會讀但卻難懂意思,所以學習文言文時就得在串講中落實字詞,在理解的基礎(chǔ)上予以背誦,基于這一點來說,文言文學習初始階段的正音,斷句和吟誦,確實是必不可少的,而接下去的串講和積累文言文知識更是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
串講,一方面可以積累古典文化的精粹,另一方面,也為我們研究和傳承古典文化奠定了基礎(chǔ)。上個世紀40年代,朱自清先生在《經(jīng)典長談》序中強調(diào):“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jīng)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jīng)典訓練的價值不在于實用,而在文化……”。周敦頤的《愛蓮說》應該是一篇上乘之作,當我們欲形容美好高潔的物象時,總習慣于引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但是作者是如何用這一句形容蓮花的高潔品性呢?我們就先要從翻譯方面了解:通常的注解都是蓮花在清水里洗滌過但并不妖媚云云。但學生就會納悶:為什么說“濯清漣”會給人以“妖”的感覺呢?這個時候,僅僅靠“言”的注釋和解釋已經(jīng)無法給人一個信服,就得借助“文”“文化”來幫助我們挖掘文本的內(nèi)涵了:先來看看“清漣”一詞出現(xiàn)的語境。南北朝的謝靈運《過始寧墅》詩中寫道“白云抱幽石,綠筱媚清漣”,意即天邊的白云環(huán)抱著清幽的山石,嫩綠的竹子頻頻向清澈的水波獻出嫵媚嬌柔。詩中,綠筱和清漣是互為映襯的,也正是因為清漣的映襯,綠筱才顯得更為嫵媚。還有白居易,在他們眼中,水波映襯的東西給人以光華流動的感覺。因此,水邊的竹、水里的龍、水中的島、水生的蓮都能夠用一個“媚”字來形容。這樣,“濯清漣而不妖”一句中的“濯”字就應當理解為“洗滌著”了:只有“洗滌著”,花光水光交相輝映,才能讓人產(chǎn)生目眩神迷的感覺,也才能談及“媚”和“妖”了。如果再要追究謝靈運和周敦頤筆下一個是“媚”,一個是“妖”,就得繼續(xù)在古典文化體系中挖掘作者的思想體系了。
波光瀲滟的水讓花顯得妖媚,而蓮生水中卻又不顯妖媚,君子純正而又莊重的品格就躍然紙上了;“言”在前,“文”相伴,文言文的博大精深才能從中予以彰顯。
二、文言并舉,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
文言文學習要“言”“文”并舉,即不知關(guān)注“言”,以至于“死于章句”;也不能只關(guān)注“文”,以至于“廢于清議”。所謂“死于章句”就是離章析句,死摳字詞問句,孤立單調(diào)地記誦詞句意思,而不去探究詞義的源流,更不去顧及詞匯的語境,使得文言文學習味同嚼蠟,苦不堪言。所謂“廢于清議”是指脫離語言文字,架空分析文章,一團和氣,實效頓失。文言文學習要“文言并舉”,既要重視文章內(nèi)容的解讀和賞評,又要重視詞句的理解和掌握,只有二者有機結(jié)合,相輔相成,才能相得益彰。
在學習柳宗元《小石潭記》中的文言實詞“清”時,如果只看到了“水尤清冽”中“清澈”這個意思,就不能很好的理解文末“以其境過清”中“清”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只有把“清”這個字反復多次的放在不同層次的語境中,我們才能深刻領(lǐng)悟其在文中所表達的“清閑”、“冷清”、“凄清”的不同意味。作者被貶永州后,因為心中苦悶,游山玩水,忽然間在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發(fā)現(xiàn)了一眼“水尤清冽”的小潭。試想,如果不是“清閑”之人,誰會有那么多閑情逸致去荒郊野外尋找野景呢?當作者剛剛沉浸在游魚與游人的無限樂趣之際,筆鋒忽然一轉(zhuǎn)——“坐潭上,四面竹樹環(huán)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試想,如此“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的人間勝景,為何讓作者在游興正濃時感覺到了“冷清”與“寂寥”呢?這就不得不要提到作者當時的處境:柳宗元于唐順宗永貞元年因擁護王叔文的改革,被貶為永州司馬。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不得不寄情山水;借景抒情,抒發(fā)自己的不幸遭遇。宦海浮沉,萬千孤獨,這個“清”字也就同時具備了好幾層意思:“清澈”繼而“清閑”、“冷清”,兼而“凄清”、“悲涼”,文章在迷惘的離去中給讀者留下無窮的遐想。
三、讀在先,寫在后,搭建深度溝通橋梁
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言:“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fā),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就是說,作家創(chuàng)作,總是由內(nèi)而外;而閱讀文章的人則是通過文辭來了解作者所表達的感情的,沿著文辭找到文章的源頭,及時是深幽的意思也將會得以顯現(xiàn),被人所理解。文言文與現(xiàn)代文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字詞障礙,要掃除字詞障礙,最關(guān)鍵的就在于讀,就如古人所言“書讀百遍其義自見”一樣,在看似“浪費”時間的閱讀中,帶動學生對文本的解讀;在看似“浪費”時間的朗讀中,帶動學生追根溯源,不斷前行。因此,教師在教授文言文時,要舍得“浪費”時間,舍得“浪費”時間讓學生盡情地讀。就如法國思想家盧梭說的:“最重要的教育原則是不要愛惜時間,要浪費時間。”我認為,盧梭所說的“浪費”時間,并不是平常意義上的時間的無謂消耗,而是指教師要避免低效的灌輸,在課堂上保證學生有充分的時間進行體驗,感悟,才能使其心智能力獲得自由。體現(xiàn)在“精教活學”的語文課堂教學即就是:“教”的根本目的不僅是幫助學生“學”,還要根據(jù)學生的學情來確定教學內(nèi)容;“教學”活動實質(zhì)就是組織學生“學”的活動,教學過程其實是“學”的活動的充分展開。
怎么讀文言文呢?朱自清先生在《怎樣學習國文》中告訴我們:“古人作一篇文章,他是有了濃厚的感情,發(fā)自他的肺腑,才用文字表現(xiàn)出來的。”“你能否從文字中體會古人的感情呢?這需要訓練,需要用心,慢慢地去揣摩古人的心懷,然后才能發(fā)現(xiàn)其中的奧蘊……”在學習劉禹錫的《陋室銘》時,學生讀到“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時,“碧綠的苔蘚,清翠的草色”都能在學生的朗讀中了然于胸,但是“上”和“入”這對既相對又相近的實詞該如何解釋?又該如何表現(xiàn)此種物象的意蘊呢?陋室環(huán)境清幽,可是這種清幽如何通過環(huán)境的描寫得以呈現(xiàn)呢?在學生的筆下:“點點鮮綠的苔痕蔓上臺階,油油如染的青草映入眼簾……”或“茸茸的苔痕似一條長長的綠毯蔓延到臺階上,青青的小草似一條柔柔的綠絲帶直逼眼球……”這些語句一出,陋室環(huán)境的清幽躍然紙上,“上”和“入”的解讀更不在話下。讀,看似只給我們聲調(diào)里的生命,而寫卻讓學生領(lǐng)略了文言文的味兒。
錢夢龍先生說:“經(jīng)過千百年時間淘洗而流傳下來的一些膾炙人口的文言文(包括古詩歌)是詩文中的極品,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chǎn)的精華……這些作者千錘百煉的語言,斐然可觀的文采,匠心經(jīng)營的章法,也都足以垂范后世。”而“文”和“言”就是我們學習文言文的精粹所在,當然,此文所論述的文言并舉,并非在一篇文言文中面面俱到,而是要根據(jù)教學大綱、教學目標和篇章特點,各取所需,有所側(cè)重罷了。
(作者單位:江蘇省張家港市大新實驗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