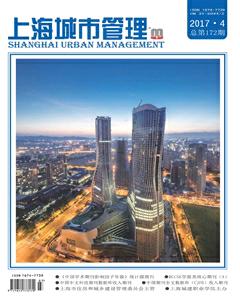都市邊緣區農民對土地征用的補償預期及共享機制
陳世棟 羅忱
摘要:隨著快速城市化帶來城市空間的擴大,大都市邊緣區往往被劃為規劃控制區,其中農地極有可能被征用為城市建設用地,不確定的土地利用預期及土地級差地租對農民形成了強烈的激勵,導致大量違建產生。通過對廣州市白云區北部三個鎮97條行政村的問卷調查,試圖了解快速城市化地區的農民對集體土地被征用及其可能獲得補償的預期。結果表明,都市邊緣區農民對征地補償普遍存在較大的期望,并希望獲得與城市地區功能與市場價值相匹配的補償。大量農民甚至認為其土地只能出租而不能被征,反映了農民對于以其土地產權分享城市化紅利的意識日漸高漲,因而,政府在通過征地來推動空間城市化時,應注意構建城鄉土地發展權共享機制。
引言
中國獨有的“城鄉雙重二元”[1]土地制度是造成城鄉二元格局的制度性根源之一,受到各界的廣泛爭議。[2]在土地的價值城鄉分配過程中,通過低價征地和高價出讓的方式,政府獲得了絕大部分地租收入,[3]從而造成了大量因征地而產生的社會問題,[4]但最重要的問題是因同地不同價而造成的城鄉公平。[5]盡管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正是得益于這一制度安排而獲得快速城市化的積累,是支撐中國“城市化奇跡”的根本原因,[6]在現行的分稅制制度安排下,地方用獨有的土地財政的方式獲得了建設城市基礎設施的資金,為產業發展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支付成本,因而具有合理性。目前,中國經過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整體已經進入城市化后期前半段,但在城市人口增長的過程中,城鄉建設用地同步增長,即存在嚴重的“雙棲城市化”現象,[7]造成了嚴重的土地資源浪費,而在都市邊緣區,隨著城鎮用地的平面推進,存在農民大規模的違規的土地轉用現象,[8]即通過加建、搶建或者違法建設廠房和小產權房出,極力將城市化紅利內部化。[9]雖然單個村莊面積不大,但村莊主體過多,[10]基層政府難以對之實施有效的監管,造成了大量分散和混雜的非城非鄉的景觀,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城市基礎設施和優質產業用地的安排。
珠三角地區自改革開放初期以農村社區工業化起步后,[11]鄉村地區發展逐漸形成了對土地租金的“路徑依賴”,[12]以通過不斷擴大建設用地規模來獲取土地租金,并通過構建股份合作制[13]來鞏固已獲得的土地租金紅利。集體用地實際上已經成為本地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主要來源,因而往往抗拒政府的征地,導致城市產業和空間被低端鎖定。所以,對大都市邊緣地區的農民對政府征地的意愿及其獲得土地租金補償預期的研究,可以深入揭示自下而上城市化地區農民對農地關系的變化,為政府制定征地措施及城市空間更新提供借鑒。
一、研究區域與問卷調查
(一)研究區域
本文主要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剖析都市邊緣區農民對農地被征用及其對獲得不同補償的態度。調查問卷空間范圍為廣州市白云區北部三鎮,從西往東分別為江高鎮、人和鎮和鐘落潭鎮,面積共334.99km2(圖1)。三鎮處于廣州市核心建成區與北部花都組團的過渡地帶,流溪河貫穿三鎮。流溪河流域是廣州重要的水源保護區,沿岸有13萬畝基本農田。在快速城市化下,本地農民面臨較大的外部發展機會,1980年代以來,大量的小產權房及農村集資房建設屢禁不止,存在普遍的加建和搶建等違規建設行為,[9]3個鎮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是研究農民對政府征地意愿及不同的補償方式態度的典型區域。
廣州市白云區東鄰增城區,西靠佛山市南海區,南接荔灣、越秀、天河、黃埔等4個核心城區,北至花都區和從化區。目前,白云區內有14條行政街、4個中心鎮,設居民委員會241個,村民委員會118個。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222.27萬,戶籍人口82.85萬,流動人口約139.42萬。行政街道位于南部,四個中心鎮位于北部,白云區長期作為廣州郊區,城鄉結合部特征明顯。村鎮面積大,分布廣泛。由于南接廣州核心建成區,北連空港,快速城市化給白云區帶來了分享發展的機遇,是傳統的自下而上鄉鎮經濟發達地區,但隨著廣州大量的交通基礎設置布局及城市空間擴大,也給白云區未來發展帶來不確定性。
(二)問卷調查與數據處理
本文采用調查問卷及訪談法收集相關信息。采取全覆蓋的方式,每村100份村民問卷對三鎮共97條行政村(鐘落潭鎮37條村,人和鎮25條村及江高鎮35條村)發放問卷調查。村民問卷共發放9 700份。獲得了江高34條村、人和鎮24條村,共56條村的村民問卷(其中兩條村作廢);總計4 500份,有效約3 556份。
所有問卷均通過村委會向村民發放和組織填寫,并經村委會上收后統一寄送至本研究課題組(發放時間為2013年11月6日至2013年12月16日)。課題組統一組織人員,基于SPSS進行數據錄用及分析(數據處理時間為期一個月,從2013年12月26日至2014年1月26日),數據錄入過程中進行了有效問卷的篩選,將筆跡相似問卷去除,將前后邏輯矛盾問卷去除。為了研究都市邊緣區農民對其農地或宅基地未來被征用的可能預期時,設置的問題為:您覺得您的農地或宅基地未來會被政府征用嗎?答案有3個選項,分別為“可能性極大”、“不會”和“無所謂”。為研究農民對希望獲得的征地補償的態度,設置了問題:您認為政府征用農地或宅基地應如何補償?答案分為4個選項,分別為“農地按照農地價格補償,宅基地按照宅基地價格補償”、“農地按照農地價值補償,宅基地按照城市建設用地價值補償”、“按照被征地功能和用途補償”和“不能被征,只能被租”。第一個選項能了解農民是否在意集體用地被征用前后市場價格的變化;第二個選項能了解農民在意農地還是宅基地的收益權和城鄉建設用地同地不同價的看法;第三個選項意在了解農民是否在意集體土地在征地前后市場價值的巨大差異,能從側面了解農民是土地城市化市場紅利的重視程度;第三個選項是了解農民對城鄉土地市場價值不平衡及土地作為財產權能獲得長期收益的態度。
二、問卷結果分析
(一)農民對其集體土地會否被征用的預期
部分研究[9、10、12]認為,都市邊緣區之所以存在大量的農地非法轉用現象,原因就是農民和村集體基于農地可能被征為城市建設用地的預期。各行為主體在城市化形成的巨大的土地級差地租的激勵下,紛紛通過“多個村民聯合、本村村民與外部資本聯合、農村集體組織主導、村集體與外部資本聯合”等多種方式聯合行動以降低違法成本。而不同村莊土地利用安排的差異主要是受到村莊交通區位、信息獲得渠道相關,但也存在村莊區位相似而村莊違建規模和力度相差甚遠,或者村莊區位差異較大但違建規模均較大的情況,但不管哪種情況,都與外部管制力度和村莊內部結構差異相關。然而,農地轉用行為受到相關法律的嚴格管制,特別是國家嚴控任何單位或個人對基本農田的轉用,但何以廣州都市邊緣區的農民依然存在甘冒著違法風險的農地轉用行為?[3]以下以農村調查問卷為基礎,分析農民對農地是否會被征用的預期態度。
在問及“您覺得您的農地或宅基地未來會被政府征用嗎”這一問題時,有1 078位被訪者回答可能性極大,占39.2%,選擇“不會”的為少數,僅687人,占25.0%,另有35.9%的村民選擇“無所謂”。可見,本地大部分農民認為在城市化快速推進背景下,本村的農地或者宅基地可能會被政府征用。政府征地則需進行補償,農民從政府征地所得的補償費用遠遠高于其從事農業的收益,正是來源于征地所得的財產性收入預期,造成了農民的農地轉用行為及違建行為的發生。
1.不同鎮集體土地被征用的期望的差異
征地預期對不同鎮村民的激勵程度并不一致。但被調查的3個鎮中,除了江高鎮選擇“無所謂”人數高于“可能性極大”和“不會”外,其他兩鎮選擇“可能性極大”選擇的人數均高于選擇“不會”及“無所謂”的人數,說明了快速城市化下,城市擴大帶來的租金收益對農民的存在極大激勵。
從鎮街的差別來看,鐘落潭鎮認為“可能性極大”的農民占全鎮的43.8%,認為“不會”的占26.6%,人和鎮認為“可能性極大”的農民占全鎮的45.5%,認為“不會”的占22.6%;江高鎮認為“可能性極大”的農民占全鎮的32.5%,認為“不會”的占25.8%。在三鎮之中,人和鎮農民認為農地極有可能被被征的人數比例最高,反映了人和鎮農地面臨快速城市化對農地的侵蝕力度最大,鐘落潭鎮次之,江高鎮最低,同時反映了農民對農地被征的預期。可以推測的是,預期較大的鎮,其農民對投入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不高,反而通過正規或者非正規途徑尋求農地非農化,以獲取城市化級差地租或者征地補償款的激勵作用更高。較大的征地預期下,農地保護的難度將加大(圖2)。
2.18歲至35歲年齡段的人對于政府征地期望最大
年齡的差異體現了個體行為及其效果的差異。從不同年齡組的被訪者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來看,在60歲以上年齡組中,39.60%的人選擇“可能性極大”,選擇“不會”的占24.83%,選擇“無所謂”的占35.57%。在36歲至60歲這一年齡層次中,38.19%的人選擇“可能性極大”,選擇“不會”的占25.80%,選擇“無所謂”的占36.02%。在18歲至35歲的年齡組中,有67.14%的被訪者選擇“可能性極大”,占了大部分。可見,在成年人的三個年齡段中,青年人口組對政府征地的期望最大(圖3)。
3.打工及務農者對于政府征地期望最大
職業的差異可以反映行為人獲取信息渠道及其對信息判斷的差異,從而影響了其對地方發展趨勢及政府管制力度的判斷。從各類型職業被訪者對農地可能被征的態度來看,認為“極有可能”被征的比例最大的人群是專業人員或管理人員,最低的是“無工作中”,打工者認為農地極有可能被征的達到了41.2%,而務農者為38.6%,私營企業或個體戶為36.9%,政府公務員或單位職員為38.1%。認為“不會”被征的被訪者中,“無工作者”的比例最高,達到32.0%;其次是私人企業主或個體戶,達到31.2%,再次是務農者,達到27.5%;而打工者最低,僅為22.1%(圖4)。
認為農地會否被征主要跟被訪者所掌握的信息相關,從類型上看,公職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外出打工者認為農地被征可能性極大的比例高于外出務農者及無工作者,反映了前者所掌握的信息量大于后者。而在認為“不會”被征的人群中,顯然“無工作者”總體上所掌握的信息量較小,認為不會被征也就不足為奇;而打工者認為“不會”的比例最低,更是由于外出打工者所掌握的外部信息可能優于務農者及無工作者人群,證明了對農地是否會被征用的預期與職業的非農化呈現極大的正相關。
4.收入水平越低對政府征地期望越大
收入水平的差異影響著行為人對獲得高收益前期投入的能力。不同收入水平的被訪者對農地或宅基地未來是否會被征用這一問題的回答的差異較大。收入水平在3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的各個收入組被訪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最具代表性。在60 001元至100 000元的收入組中,選擇“無所謂”的占41.13%,“可能性極大”占40.32%,表示“不會”的占18.55%。在4 0001元至60 000元收入組中,表示“可能性極大”的為41.79%,表示無所謂的為33.57%,選擇“不會”的為24.64%。在200 001元至40 000元收入組中,選擇“可能性極大”的為42.44%,選擇“不會”的為22.20%,選擇“無所謂”的為35.37%。在10 001元至20 000元收入組中,選擇“可能性極大”的為44.58%,選擇“不會”的為26.68%,選擇“無所謂”的為28.74%。在6 001元至10 000元收入組中,選擇“可能性極大”的為35.21%,選擇“不會”的為24.41%,選擇“無所謂”的為40.39%。在3 001元至6 000元收入組中,選擇“可能性極大”的為38.66%,選擇“不會”的為20.37%,選擇“無所謂”的為40.97%。可見從10 000元以上至100 000元之間的各個收入組別之中,收入越低者,對政府征地的期望越大,可能的原因是雖然其經濟收入不高,但也能把握一定的信息機會,并希望借征地能帶來實在的收益。在10 000元以下的兩個收入組中,選擇“可能性極大”者的比例還低于選擇“無所謂”者的比例,可見,因為收入低,難以有資金投入違建建設以把握政府征地可能帶來收入的增加機會,所以這兩個收入組者對于通過政府征地提高收入不敏感(圖5)。
(二)農民對于政府征用農地及宅基地后給予補償的方式差異
如前所述,研究區域內農民普遍存在對政府征地的期望,這種期望的經濟體現就是希望獲得較高的補償收入,因而,通過問卷農民對征地的補償費用高低及補償方式的差異可以反映這一問題。大量的研究認為,政府在以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上征得土地,如征用農地的補償僅僅是其近三年的農地農產品產出的價值,而建設用地價格也較低,但不管征用建設用地還是農地,政府均可能改變原有土地屬性,建設工廠或者房地產等開發項目,而又以較高的價格在市場上出讓,從中賺取差價。[1]不公平的城鄉征地補償往往造成很多社會問題,這一現象受到很多詬病。為探究農民對其農地或宅基地被征用時所希望獲得補償的差異,將問題“農民希望農地或宅基地被征的補償方式”的答案設置為“農地按照農地價值補償,宅基地按照城市建設用地價值補償”、“農地按照農地價值補償、宅基地按照宅基地價格補償”、“按照被征地功能和用途補償”和“不能被征,只能租地”四種類型,以充分反映農民對其土地被征用后獲得補償的意愿。在所有回收的有效問卷中,有47.8%的被訪者希望“農地按照農地價值補償,宅基地按照城市建設用地價值補償”,說明了城鄉接合部地區,農民普遍認為被征地后應獲得與城市建設用地相同功能的價值補償。選擇“農地按照農地價值補償、宅基地按照宅基地價格補償”的僅為15.6%,選擇人數較少,說明了農民普遍認識到存在上述的城鄉土地價值差異對其存在的不公平。選擇“按照被征地功能和用途補償”的僅為9.1%,選擇人數最少,說明了農民普遍意識到的城鄉土地價值差異。而選擇“不能被征,只能租地”的也達27.5%。選擇人數為第二多,說明了農民對其農地產權意識的普遍覺醒,因其土地被征后,僅僅能獲得一次性補償,而不能被征只能出租則能夠細水長流,獲得長時間的財產性收益。數據反映了大部分被訪者普遍存在對被征地高價值補償的渴望,部分被訪者甚至認為農地或宅基地不能被征,而只能被租,同樣也反映了農村與村集體在城市化下對分享土地租金收入的渴望。
1.各鎮農民均希望獲得等同于城市建設用地的補償標準
3個鎮的被訪者對該問題的回答也體現了各個鎮的發展差異及農民對土地租金剩余追求的差異。按照“農地按照農地價值補償,宅基地按照宅基地價值補償”、“農地按照農地價值補償,宅基地按照城市建設用地價值補償”、“按照被征地價值補償”和“不能被征,只能租地”四個選項的先后順序,3個鎮被訪者進行選擇的百分比見圖6。這些數據反映,人和鎮被訪者更多希望“農地按照農地價值補償,宅基地按照城市建設用地價值補償”,其他兩鎮的被訪者持有這種意見在四個選項中均為最多。其次為“不能被征,只能租地”,各鎮選擇的人數均排在第二位,說明了農民希望能夠掌握集體土地的利益權,并相應獲得與市場份額一樣的收益。總之,盡管各鎮各村的村莊社會結構并不一致,但這并不影響各鎮農民對于基于集體產權所應獲得完全一致的土地市場的收益。
2.不同職業組的人對于政府征地期望存在較大差異
務農、打工、私營企業主或個體戶、政府公務員或單位職員、專業人員或管理人員、其他、無工作等七大類別。按照不同職業組人員對上述四個選項的選擇,“打工”和“務農者”選擇“不能被征,只能租地”分別排在前兩位,分別為38.9%和34.3%,第三為無工作者,僅為9.2%。無論任何職業,選擇“農地按照農地價值補償,宅基地按照城市建設用地價值補償”的被訪者數量均最多,除了務農者為42%外,其他均在50%左右,最高的為務工者,達到了52%,表明無論何種職業,均希望政府征地時,能夠獲得按照等同于城市用地的價值進行補償。同時,在選擇“不能被征,只能租地”的選項中,無工作者占比最高,達到了36%,務農者在所有職業被訪者中的排在第二,達到了30.9%,表明了集體土地對無工作及務農者的生活及就業保障功能。
三、結論與討論
都市邊緣區是處于城市向鄉村過度的區域,這里土地利用情況復雜,變化迅速,又往往是城市建設用地未來的重點擴展之地,因為屬于規劃控制區。由于存在巨大的城市化外部紅利,農民往往農民聯合或與外部聯合,避免政府的強力管制,從而獲得土地建設收益,所以,存在城市規劃的空間管制被激烈突破的現象。
通過問卷調查,能深入分析微觀層面基于農民這一行為人對于參與城市化進程及獲得收益的態度。總體來看,基本結論如下:
一是由于城市的快速擴張,都市邊緣區農民對政府征用農地存在強烈的期望,說明了農民對分享城市化紅利的期望。
二是人和鎮農民對征地的期望最大。在人和鎮的603份有效問卷中,有403人回答“可能性極大”,占66.83%,鐘落潭鎮則達到62.20%,而江高鎮則為55.78%,三鎮農民對政府征用農地的期望均超過半數,說明白云區農民對政府征地的期望普遍較大,但各鎮有差異,可能是因為距離廣州城市建成區的距離遠近和城市發展程度的差異而有所區別。
三是18歲至35歲年齡段、打工及務農者及年收入水平在10 000元左右的被訪者對征地的期望最大。
總之,廣州等珠三角城市農民通過集體土地來獲得城市化紅利的愿望,往往加大了政府的公共預算開支,也不利于城市的產業和空間更新,表明未來政府應更加尊重農民的土地發展權,這也是珠三角在進入城市化后期階段后需要進行機的制創新之處。
說明:本文受“廣東省社會科學院2017年度院級應用決策課題——廣東省特色小鎮產業發展路徑及空間組織模式”資助。
參考文獻:
劉守英.中國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的特征、問題與改革[J].國際經濟評論,2014(5):9-25.
洪世鍵,張京祥.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背景下中國城市空間擴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J],城市規劃學刊,2009(5): 89-94.
鐘成林,胡雪萍.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對城市建設用地利用效率的影響研究——基于門限回歸模型的實證分析[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6(2): 22-35.
馬軍成,吳翼虎,鄭防修,等.城鄉一體化土地市場下的征地補償標準研究[J].中國農學通報,2016(1): 200-204.
孫東琪,張京祥,陳浩,等.中國大城市拆遷安置居民補償方式與受益率測度——以南京為例[J].地理科學,2016(2):161-169.
趙燕菁.土地財政:歷史、邏輯與抉擇[J].城市發展研究,2014(1):1-13.
劉紀遠,劉文超,匡文慧,等.基于主體功能區規劃的中國城鄉建設用地擴張時空特征遙感分析[J].地理學報,2016(3):355-369.
陳世棟,袁奇峰.都市邊緣區空間管制效果的產權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基于基本農田保護區政策視角[J].地理科學,2015(7):852-859.
呂鳳琴,陳世棟,袁奇峰.都市邊緣區農村集資房時空演進特征及驅動機制——以20世紀90年代廣州白云區為例[J].熱帶地理,2015,35(5):753-761.
袁奇峰,陳世棟.城鄉統籌視角下都市邊緣區的農民、農地與村莊[J].城市規劃學刊,2015(3):111-118.
林永新.鄉村治理視角下半城鎮化地區的農村工業化——基于珠三角、蘇南、溫州的比較研究[J].城市規劃學刊,2015(3):101-110.
孟繁瑜,李呈.中國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協調統一發展研究——國家土地政策的負外部性路徑依賴分析與破解[J].中國軟科學,2015(5):1-11.
魏建平.完善農村股份合作制,提高珠三角城市化質量[J],規劃師,2006(10):66-67.
責任編輯:許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