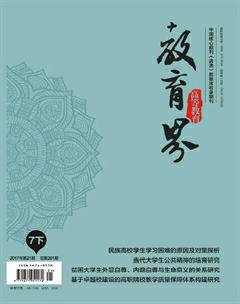《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課堂教學(xué)中必須重點(diǎn)闡釋的幾個問題
張海豐
【摘要】文章結(jié)合教學(xué)實(shí)踐,認(rèn)為在《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課堂上必須闡釋清楚幾個重要問題:一是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核心命題是“國富國強(qiáng)”;二是“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追趕”是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切入點(diǎn);三是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要與時俱進(jìn)的不斷修正自身的理論體系:四是比較經(jīng)濟(jì)史研究方法、專利制度設(shè)計和制度調(diào)整對于發(fā)展中國家的重要性。
【關(guān)鍵詞】《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國富國強(qiáng);工業(yè)化;技術(shù)追趕;專利制度
【基金項(xiàng)目】國家社科基金項(xiàng)目(15XMZ088),本文是“廣西人文社會科學(xué)發(fā)展研究中心團(tuán)隊建設(shè)”階段性成果。2017年度廣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學(xué)改革工程項(xiàng)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課程體系構(gòu)(2017JGA138)。
一、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核心命題是“國富國強(qiáng)”
托馬斯·R·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給大衛(wèi)·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一封信中曾寫道:“探求國富國窮的原因是一切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的重中之重。”(傅軍,2009)毋庸諱言,“國富國窮”是經(jīng)濟(jì)學(xué)最古老,但又是歷久彌新的課題。這一主題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命題,所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將智力資源投入其中。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Lucas,1988)曾感嘆道:“國家間的收入水平和增長率差異如此之大,以致于一個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一旦開始關(guān)注經(jīng)濟(jì)增長問題,那么其他一切命題都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誠如盧卡斯所言,世界各國之間的增長績效差異的確非常驚人。其實(shí)在更早的時候,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就已經(jīng)注意到了這個現(xiàn)象。為了解釋這一現(xiàn)象,新古典增長理論將技術(shù)作為一個外生變量納入增長模型(Solow,1957),并認(rèn)為后發(fā)國家可以通過引進(jìn)技術(shù)縮小與發(fā)達(dá)國家之間的差距,全球經(jīng)濟(jì)最終會出現(xiàn)收斂。而現(xiàn)實(shí)世界中這種差距還在不斷拉大之中,也即富國越富,窮國越窮了。內(nèi)生增長理論試圖彌補(bǔ)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缺陷,將技術(shù)和知識作內(nèi)生化處理,這的確能夠更好地解釋經(jīng)濟(jì)增長,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需要進(jìn)一步厘清。從根本上來說,內(nèi)生增長理論仍然是靜態(tài)的均衡分析框架,而且對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的各因素之間的協(xié)同效應(yīng)關(guān)注不夠。
二、“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追趕”是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切入點(diǎn)
第一次工業(yè)革命以降,世界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進(jìn)入快車道,工業(yè)化的推進(jìn)和技術(shù)進(jìn)步成為經(jīng)濟(jì)增長的根本動力,發(fā)達(dá)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差距主要體現(xiàn)為工業(yè)化水平和技術(shù)水平的差異。因此,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要以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追趕作為切入點(diǎn),來探討后發(fā)國家的追趕戰(zhàn)略。后發(fā)國家的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追趕是一個歷時變化的動態(tài)過程,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的靜態(tài)分析框架在解釋這一動態(tài)問題時是有缺陷的。因此,運(yùn)用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動態(tài)分析方法來闡釋這一問題是更為合適的。作為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的重要分支,以埃里克·S·賴納特(Erik S.Reinert)和張夏準(zhǔn)(Ha-joon Chang)為代表的演化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可以作為主要分析框架。他們追隨德國歷史學(xué)派先驅(q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傳統(tǒng),以生產(chǎn)、知識和創(chuàng)新為中心,為后發(fā)國家的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追趕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張。而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技術(shù)追趕理論、路徑依賴與路徑創(chuàng)造理論以及技術(shù)進(jìn)步與制度匹配理論,可以成為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
發(fā)達(dá)國家在發(fā)展之初,都經(jīng)歷了一段通過保護(hù)國內(nèi)報酬遞增產(chǎn)業(yè),以此追趕領(lǐng)先國家的發(fā)展歷程。通過保護(hù)主義,實(shí)現(xiàn)本國工業(yè)化和對發(fā)達(dá)國家的技術(shù)追趕,從早期的英國、美國、歐洲大陸、日本,一直到最近的韓國和中國臺灣,這一模式一直得以復(fù)現(xiàn)。然而,同樣采用保護(hù)主義手段推進(jìn)本國工業(yè)化的拉丁美洲國家和南亞國家(如印度),卻沒有那么成功。因此,教師講授時要特別強(qiáng)調(diào),后發(fā)國家的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追趕,雖然保護(hù)主義是必要的,但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通過對成功實(shí)現(xiàn)追趕和追趕失敗兩個組別國家的比較經(jīng)濟(jì)史研究,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都是保護(hù)主義,但具體的政策工具箱是有區(qū)別的。如果上升到機(jī)理的高度,那么后發(fā)國家在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追趕進(jìn)程中,要采用“好的保護(hù)主義”,遠(yuǎn)離“壞的保護(hù)主義”。更為關(guān)鍵的是,通過實(shí)施保護(hù)主義戰(zhàn)略,隨著國內(nèi)產(chǎn)業(yè)部門的壯大,實(shí)現(xiàn)了組織創(chuàng)新和技術(shù)創(chuàng)新良性互動的局面。而在國家層面,通過產(chǎn)業(yè)保護(hù)而發(fā)展壯大的國內(nèi)大企業(yè)建立起了研發(fā)制度,加上政府支持的國家實(shí)驗(yàn)室以及教育基礎(chǔ)設(shè)施等的完善,國家創(chuàng)新系統(tǒng)得以建立,這又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追趕。
三、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要與時俱進(jìn)和不斷修正自身理論體系
雖然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能夠較好地解釋發(fā)展中國家的追趕型工業(yè)化,但該理論體系也存在著時空局限性,因此,對其理論成立的假設(shè)前提作進(jìn)一步的厘清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說,在講授《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時不能停留在用理論來解釋經(jīng)濟(jì)現(xiàn)象的層面,在運(yùn)用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來解釋后發(fā)國家的追趕現(xiàn)象時,要同樣注重對該理論體系的拓展和完善。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很好地解釋了歷史上后發(fā)國家的追趕和欠發(fā)達(dá)現(xiàn)象,但放在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的新背景下,進(jìn)一步豐富它的政策工具箱是必要的。所以授課時必須講清楚,在模塊化生產(chǎn)和價值鏈斷裂的國際分工新形勢下,再加上TRIPS和WTO等國際規(guī)則體系的制約,傳統(tǒng)保護(hù)主義的實(shí)施空間已經(jīng)非常有限。因此,筆者提出的“選擇性專利保護(hù)”策略,可以成為后發(fā)國家向價值鏈高端環(huán)節(jié)攀升的有效手段。而隨著工業(yè)化的深入和技術(shù)不斷趨近世界前沿,制度也要做出不斷的調(diào)整,以適應(yīng)這種變化。以中國的政策實(shí)踐為例,隨著工業(yè)化進(jìn)入后半程,技術(shù)也越來越接近發(fā)達(dá)國家,因此,教師講授時也要特別強(qiáng)調(diào),中國應(yīng)該轉(zhuǎn)變發(fā)展戰(zhàn)略,注重保護(hù)國內(nèi)市場與鼓勵技術(shù)創(chuàng)新并重,從而實(shí)現(xiàn)國內(nèi)經(jīng)濟(jì)良性大循環(huán)。
在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中,保護(hù)主義之于后發(fā)國家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追趕的重要性,是始終被強(qiáng)調(diào)的。這也是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的題中之義,在賴納特和張夏準(zhǔn)看來,選擇和保護(hù)高質(zhì)量(報酬遞增)產(chǎn)業(yè)活動對經(jīng)濟(jì)發(fā)展而言是基礎(chǔ)性和根本性的,這也是其富國策中的核心觀點(diǎn)。然而,這一觀點(diǎn)成立有一個隱含的假設(shè)前提,即作為實(shí)施保護(hù)主義和選擇正確產(chǎn)業(yè)活動的行為主體——國家——必須具備較強(qiáng)的能力,在這一點(diǎn)上,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沒有深入展開。因此,教師授課中有必要將比較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發(fā)展型國家論”和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綜合,嘗試將“國家自主性”和“國家能力”等概念納入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分析框架,從而對其隱含的假設(shè)前提作一個較好的補(bǔ)充解釋。除此之外,也有必要對國家自主性進(jìn)行對內(nèi)、對外兩個層面的闡述,并豐富國家能力的內(nèi)涵,將其細(xì)分為政策的制定和實(shí)施能力、產(chǎn)業(yè)甄別能力、尋租抑制能力和政策動態(tài)調(diào)整能力。將“發(fā)展型國家論”和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兩個體系加以融合,筆者認(rèn)為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
四、《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課堂教學(xué)中的其他問題
(一)比較經(jīng)濟(jì)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運(yùn)用比較經(jīng)濟(jì)史的研究方法,對當(dāng)今發(fā)達(dá)國家的工業(yè)化歷史進(jìn)行簡單梳理,發(fā)現(xiàn)保護(hù)主義是后發(fā)國家在追趕型工業(yè)化階段必不可少的政策手段。無論是實(shí)行重商主義政策的都鐸王朝時期的英國,還是在追趕階段實(shí)行高關(guān)稅政策的美國,可以說保護(hù)主義是一以貫之的。歐洲大陸國家的效仿和追趕同樣體現(xiàn)為濃厚的保護(hù)主義色彩,德、法等國家除了運(yùn)用關(guān)稅手段,還禁止本國的技術(shù)人員外流,并向外國大量派出工業(yè)間諜以吸引優(yōu)秀的技術(shù)人員。亞洲的日本和韓國同樣是在一整套嚴(yán)密的保護(hù)主義政策體系下實(shí)現(xiàn)了工業(yè)化,并通過“逆向工程”以及“引進(jìn)-消化-再創(chuàng)新”等手段,在很多技術(shù)方面實(shí)現(xiàn)了對西方發(fā)達(dá)國家趕超。而在另一些國家,比如拉美國家在早期也實(shí)行具有保護(hù)主義色彩的“進(jìn)口替代”戰(zhàn)略,但此后工業(yè)化陷入困境,追趕績效遠(yuǎn)不及東亞國家。筆者在講授時給出的解釋是:保護(hù)主義政策要隨著工業(yè)化深入不斷做出調(diào)整,也即隨著技術(shù)的不斷進(jìn)步,制度要做出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追趕成功的國家都做到了這一點(diǎn),而追趕失敗者往往都陷入制度僵化,產(chǎn)業(yè)政策被利益集團(tuán)俘獲等困局。因此,保護(hù)主義是后發(fā)國家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追趕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
(二)全球化時代專利制度設(shè)計的重要性
在講授時筆者指出,在新的全球分工格局和產(chǎn)業(yè)價值鏈高度分解的大背景下,歷史上使美國和德國實(shí)現(xiàn)趕超型工業(yè)化的傳統(tǒng)保護(hù)主義策略對當(dāng)今的后發(fā)國家已經(jīng)不再適用,加之1994年在WTO框架內(nèi)簽訂的《與貿(mào)易有關(guān)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協(xié)議》(簡稱TRIPS協(xié)議),更加劇了后發(fā)國家技術(shù)追趕的難度。在現(xiàn)有的WTO和TRIPS等全球規(guī)則體系下,當(dāng)年幫助日本和韓國實(shí)現(xiàn)技術(shù)追趕的“引進(jìn)-模仿-消化吸收-再創(chuàng)新”模式和“反向工程”為主的追趕道路也已基本被堵死。因此筆者提出,后發(fā)國家必須在借鑒追趕型工業(yè)化國家成功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當(dāng)今國際政治經(jīng)濟(jì)新背景,制定本國的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追趕戰(zhàn)略。
(三)制度調(diào)整之于發(fā)展中國家的重要性
在課堂講授中必須重視中國的政策實(shí)踐。筆者以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工業(yè)化和政策實(shí)踐為例,論證了工業(yè)進(jìn)程中制度調(diào)整的重要性,進(jìn)一步對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理論框架進(jìn)行了拓展。筆者指出,經(jīng)過30多年的高速發(fā)展之后,中國的稟賦結(jié)構(gòu)正在發(fā)生變化,資本的相對稀缺程度大為降低,技術(shù)水平和技術(shù)能力也有相當(dāng)大的提升,再加上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續(xù)提高,國內(nèi)市場空前擴(kuò)大。中國正處于一個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的關(guān)鍵時期,在這個時期,工業(yè)化戰(zhàn)略和技術(shù)政策必須做出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筆者認(rèn)為,中國現(xiàn)階段正處于由技術(shù)追趕階段向趕超階段的轉(zhuǎn)換期,在這個關(guān)鍵轉(zhuǎn)折點(diǎn)上,國內(nèi)市場保護(hù)比任何時候都要重要。如果我們能夠通過靈活的關(guān)稅政策、非關(guān)稅手段和FDI限制等措施成功地保護(hù)了國內(nèi)市場,那么我們可以通過發(fā)展適宜性的本土技術(shù)深入推進(jìn)工業(yè)化,并實(shí)現(xiàn)良性的國內(nèi)經(jīng)濟(jì)大循環(huán)。
【參考文獻(xiàn)】
[1]Lucas,L.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Monetary Economics,1988,22(01):3-42.
[2]傅軍.國富之道[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
[3]埃里克·S·賴納特.富國為什么富 窮國為什么窮[M].楊虎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
[4]林毅夫.新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學(xué)——反思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