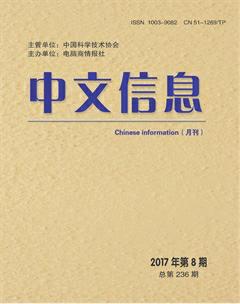淺談講解詞的撰寫思路
陳昊
摘 要:從博物館教育專業的角度來看,展覽講解詞的撰寫和文物詞條的撰寫是有較大區別的。但目前國內一些展覽的講解詞內容還停留在文物詞條的介紹階段,缺乏展品和展覽之間的聯系,分不清“講展覽”和“講文物”的區別,造成重視介紹文物而忽略展覽主題的問題。本文放棄目前同類文章從理論上宏觀闡釋講解詞寫作的方式,僅從其中選取“撰寫思路”一點,試從博物館具體的展覽和文物入手,通過實例來分析如何把握好講解詞在展覽中的撰寫方向,從而真正地讓文物起到詮釋展覽信息作用。
關鍵詞:博物館 展覽 講解詞 文物
中圖分類號:G26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 ( 2017 ) 08-0-01
近年來,隨著社會對博物館文化需求的增大,各地博物館都在舉辦形式多樣的展覽以滿足公眾的文化需求。而辦好一個展覽,不僅需要優秀的策展團隊,也需要有杰出的講解團隊將展覽的意圖清晰地傳達給觀眾。但是,從目前業界的講解情況來看,尚存在一些講解詞以物講物、內容與展覽脫節的問題,這里我就根據自己工作經驗,并輔以具體實例來談談講解詞的撰寫思路。
有人認為,講解詞所傳達的信息應該越全面越好,于是就把能查到的內容都堆砌在一起。其實,一篇好的講解詞是需要進行整體設計的,每一件文物都蘊含著豐富的信息,如何結合展覽主題選取最有價值的信息以便更好地詮釋展覽主題,這就需要撰稿者精心設計,大膽取舍了。2015年底,國家博物館曾舉辦《大象中原——河南歷史文化展》,下面就以這個展覽中展出的“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出土的石磨盤和石磨棒”為例,分析一下文物展品和展覽主題的關系。
《大象中原——河南歷史文化展》展覽介紹了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文明發展歷程,以及河南各地的考古發現。所以,在撰寫講解詞時,我嘗試著將這組文物放在“河南裴李崗文化”的背景下進行表述:
“這組石磨盤和石磨棒出土于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一般認為是用來給谷物去殼的農具。裴李崗文化距今約7800年,是中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之一。與同時期同類文物相比,裴李崗文化的石制工具表現的更為精細和進步,比如這類石磨盤,比普通的平底石磨盤增加了四個圓足,并且打磨得更加光滑,它們在使用者死后作為陪葬品埋入墓地。值得注意的是,裴李崗遺址中,凡隨葬石磨盤、石磨棒的墓葬都沒有發現石斧、石鐮、石鏟等工具,反之,有石斧等工具的墓葬也沒有石磨盤。現象表明,裴李崗文化已經有了明確的社會分工。”
與《大象中原——河南歷史文化展》中這組文物同時出土于同一遺址的另一組石磨盤和石磨棒,現在由國家博物館收藏,并展出于《古代中國》基本陳列的新石器時期北方農業展柜。《古代中國》基本陳列是以時間為線索展現中華文明發展的展覽,強調的是每件文物對于“中華文明”的意義。根據展覽思路,這組文物的寫作方向我放在了“中國新石器時期北方農業”之上。對于這件文物我的表述如下:
“距今七八千年前,黃河流域及北方一些地區已經種植了粟和黍。而這種石磨盤和石磨棒就多出土于北方粟類作物的種植區域,一般認為是用來給粟去殼的農具。類似的石磨盤和石磨棒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中也有所發現,當時用來研磨采集的果實及根莖類食物。農業發明后,石磨盤被進一步完善。但隨著農耕經濟的發展,石磨盤的生產效率已趕不上農業的進步速度,從仰韶文化時期逐漸開始消亡。這也說明石磨盤和石磨棒是一種由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過渡時期的農具。”
通過以上兩篇介紹,我嘗試說明“講展覽”的意義。所謂“講展覽”首先要明確展覽的主題思想,而文物僅僅是用來服務展覽思路的媒介。同一個遺址出土的同樣文物,在《古代中國》展覽中的要放在中國農業發展的角度去詮釋,而在《大象中原——河南歷史文化展》中,則更側重介紹裴李崗文化的特征,以突出河南在中華文明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同時,一個思路清晰的講解,不僅應該注意同一件文物如何詮釋不同展覽的主題,還應該注重同一展覽中前后文物之間的關系。這里,還以《大象中原——河南歷史文化展》的介紹為例。如果只需要通過四足石磨盤來介紹裴李崗文化與其他文化的差別的話,內容寫到“它們在使用者死后作為陪葬品埋入墓地”就可以了。但是,為了與后面文物呼應,我特意介紹了石磨盤和石斧等工具不會出現在同一個墓葬中的現象,目的是為了說明裴李崗文化出現了“社會分工”現象。因為在之后的展柜中展出了龍山文化平糧臺遺址出土的磨光黑陶,通過那件文物將引出“權貴階層和社會分化”的觀點。正是通過對前后兩件文物講解詞的設計,講解員才能夠引導觀眾通過展覽逐步揭示人類文明從“社會分工”到“社會分化”的發展歷程。
由此可見,“講展覽”最重要是以文物為載體,把展覽的整體思路和每一部分的主題表達清楚,讓文物服務于展覽,而不是渲染文物的個體意義。與之相反,“講文物”則是更多地關注文物本身,與展覽的聯系性就不那么緊密了。區別到底是“講展覽”,還是“講文物”,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這篇內容是否可以“通吃”所有展覽。比如以下的介紹方式:
“石磨盤和石磨棒是給谷物脫殼的農具,也有說法是將谷物研磨制粉的工具。裴李崗文化的石磨盤盤面制作平整,整體呈鞋底形,底部有四個圓足。磨棒多為圓柱形,中間略粗,兩端略細,制作精致。使用的時候,用石磨棒在石磨盤上來回滾壓,將谷物脫殼或磨粉。”
如果通篇講解詞都是這樣的介紹,每句話的內容放在任何展覽里都能通用,顯然沒有達到“通過文物詮釋展覽”的目的,僅僅是文物知識的簡單堆砌,內容上沒有針對展覽主題明確的指向。而這樣的講解詞恰恰在很多“明星文物”上都有體現。
很多展覽中,都會有幾件“明星文物”。正是由于文物太過知名,大家便不惜筆墨地對文物進行全方位描述。先從文物的造型紋飾說起,進而全面分析器物的制作工藝,然后開始介紹文物的歷史背景,之后講述文物流傳的傳奇故事,最后繼續說到文物對于今天和未來的啟示,內容詳盡得幾乎把所能找到的資料全部應用起來。文物的明星地位被無限突出,卻恰恰忽略了該文物在本展覽中應有的作用。這正是目前博物館講解行業中較為突出的問題。endprint
說完文物與展覽的關系,我們再來看一下如何從文物資料中選取適當內容進行講解詞的撰寫。以下是一篇介紹青銅壺的節選資料:
“壺是一種用來盛酒的長頸容器,在《詩經·大雅 ·韓奕》中寫道:‘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孟子·梁惠王下》中也寫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些都證明了壺是一種酒器……壺的口部外侈,長頸,頸部裝飾兩圈凸弦紋,弦紋下方是一圈以云雷紋為地,主紋為目紋的一組裝飾紋樣,腹部無紋飾……壺的提梁處有套鏈與器鈕相連,提梁的兩端為龍頭,中間部分用來當作龍身,并且在龍身上還裝飾有鱗紋。”
這篇介紹,全文485字,其中細節描述為228字,如果將此資料直接作為講解詞,觀眾肯定會聽得天旋地轉了。首先,文物的體量不大,細節紋飾需要近距離仔細觀察才能看清,其次,即便可以看清紋飾,觀眾也不一定能聽懂。因為根據科學測定,人類對于一個畫面的注意力基本上可以維持30秒左右,按照正常語速講解的話,30秒大概可以說出150到200字。所以在陳述文物信息的時候,盡量將觀眾每次視線停留的時間控制在30秒內,也就是200字之內。如果用40、50秒的時間一直介紹看不清楚的細節紋飾的話,觀眾的注意力便無法集中。另外,資料中引用了兩部古文獻中的文言文,目的是為了證明“壺是酒器”。但是,作為講解詞,就不能直接拿來使用。從對于信息的接收效率看,“聽”比“看”要低得多,而就普通觀眾來說,在沒有看到文字的情況下,理解古文是比較困難的,更何況有些內容都不一定能讀懂。如果在講解中過多地運用晦澀的文言文,觀眾也就無法理解講解的信息,講解自然就是失敗的。
所以,講解詞的文字一定要做到信息指向明確,內容通俗,抓住重點,每句話都要體現出自己對文物的理解。同樣的文物,我嘗試這樣描述:
“青銅壺是一種長頸的酒器,從商周到漢魏之際被廣泛使用,因此壺的形制相當復雜。這件銅壺出土于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器物除頸部裝飾一圈紋飾外,通體素面無紋。紋飾以細密的云雷紋作底,底紋之上突出主體的浮雕獸目紋,底紋和主紋形成強烈對比的裝飾,是商代后期青銅器的普遍現象。”
原先485字的資料根據展覽被概括為130字。第一句“青銅壺是一種長頸的酒器”直接明確指出器物的用途和特征;第二句“從商周到漢魏之際被廣泛使用,因此壺的形制相當復雜”,目的是為后面介紹這件文物在眾多復雜形制中呈現的商后期特點做鋪墊;第三句“銅壺出土于河南安陽殷墟遺址”明確了文物出土于商后期遺址;之后的內容,僅從所有細節描述中選取了“紋飾”有偏重地進行了歸納,進一步說明器物具有商后期的時代特征。
僅用130字,講解詞明確表達了這件文物的兩個信息:其一,壺是長頸酒器;其二,這件壺是商代晚期的典型器物。之所以從這兩點進行闡述,是考慮這件文物陳列在青銅器展廳來敘述青銅器發展,所以在撰寫講解詞的時候就應該抓住文物時代特征去描寫,這樣的介紹就比簡單的文物信息堆積要清晰得多,講解員也可以抓住觀眾注意力最集中的時候明確傳達目標信息。
本文僅通過以上案例分析并結合自己的工作感受,試圖從實操層面來探討展覽講解詞的正確撰寫方式。撰寫講解詞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工作,所涵蓋的內容涉及諸多方面,本文囿于篇幅所限,僅從撰寫思路一點進行了簡單闡述,不當之處還請同行指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