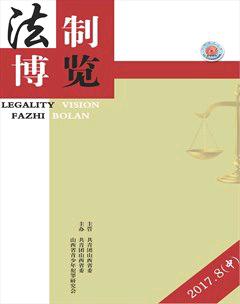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立法方向
齊國勝
西藏警官高等專科學校科研所,西藏拉薩850000
摘要:毋庸置疑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最有效的是建章立制,通過立法進行規范。立法行為要遵循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規律,其中首要任務是樹立正確的立法方向。在立法過程中,需要結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特征、要求等,因地制宜、講求實效,在國際規范與本國法律的整體框架內,各民族地區以實施區域自治為依托,按照立法針對性的要求,構建具有地方性的立體化、全方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規范體系,制度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立法;方向
中圖分類號:D922.16;D923.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23-0055-03
在弘揚傳統文化以及法治國家建設的背景下,我國不斷強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立法保護。在立法過程中,要在國家法律的整體框架下,從地方自治權的行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主體的良性運作以及形成立法的框架體系等方面進行規范,以實現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立法的整體效能。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立法的基本情況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形成往往歷史悠久,其獨特的傳承性、民族性等形成了別具一格、綿延不斷的傳統文化。而相應的傳承性、民族性等特征,要求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地方層面,都要基于自身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職責,開展系列立法工作。
(一)國家層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立法
《憲法》中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保護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遺產,發展和繁榮民族文化。”以《憲法》保護文化遺產的目標為基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制定相關的各類法律規范中,不斷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制度設計。
1.《民族區域自治法》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堡壘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傳統文化精神的顯現、文化認同的基礎,激發著中華民族的自豪感、榮譽感。為保護民族地區文化遺產,《民族區域自治法》中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保護民族的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繼承和發展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民族區域自治法》在貫徹實施過程中,通過自治機關對于地方事務的治理,使得區域性、民族性的文化遺產得到保護;通過自治權的運用,可以促使自治機關因地制宜,通過制度構建、方法創新等,發揮自治地方、自治機關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起到積極的作用。通過《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貫徹實施,“少數民族歷史文化遺產得到保護,少數民族文藝人才不斷涌現,優秀的少數民族文化得到傳承、發展與創新”。[1]
2.《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律依據
2011年6月,《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正式實施。在立法目的上,《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規定明確是:為了繼承和弘揚民族傳統文化,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在國家立法層面、從總體上對于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進行了規范,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別進行了法律上的明確,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主體既包括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也包括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等,并設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方式、方法以及法律責任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在吸收了國外及國際組織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經驗同時,設定了對邊遠及民族貧困地區的扶持制度、保護規劃制度等。[2]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總體規范,《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進行了法律上的設定,系統的建構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門法律規范。
此外,其他的法律、國務院法規規章其中的部分規定作為附屬規范,其中的某些規定涉及到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如《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規定: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實物和場所,凡屬文物的,應當適用《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律、行政法規等各類法律規范等構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國家層面法律體系。
(二)地方層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立法
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過程中,地方各級機關、部門等負責具體實施,在其職責范圍內,地方各級各類機關根據《立法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等規范,通過進行地方立法工作,因地制宜,制定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地方規范。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享有自治權,自治的內容包含根據民族地方情況設定規范的權力。根據相關法律的授權,民族地區各級機關在授權的范圍內,切實履行自身職責,制定地方性規范,積極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地方人大制定的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規范,是通過自治權力在立法方面的運用來保護文化遺產,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梳理的同時,挖掘其中潛藏的民族文化傳承,使得傳統文化在當代得以延續。同時,自治地方在制定規范過程中可以因地制宜,將當地的民族風俗習慣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結合,防止出現損害當地民族文化生態的現象發生。如西藏地方人大及常委會在開展地方立法工作時,“充分尊重藏民族的風俗習慣,凡是涉及藏族特殊的風俗習慣,在地方立法時都酌情予以變通處理,從而以法制的手段保障了藏族的合法權益”。[3]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立法方向
在歷史的螺旋式上升演進過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文化傳遞的內容、方式、載體等在保持原有特色基礎上不斷更迭,時至今日,已經形成頗具地方特色、民族特點的多層次、多種類的文化遺產。因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尤其是在立法工作中,要整合各方資源,形成合力,明確重點,以制度保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行為能夠取得實效。
(一)通過立法規范保護主體,形成多層次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體網絡
眾多門類、形式各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中,要將各級機關的職責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掛鉤,發揮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專業優勢,構建多層次的保護主體。在保護主體職能的發揮上,要通過立法工作,劃定不同保護主體的權限范圍,尤其是在涉及交叉的部分,以立法規范職能的行使,促使各類保護主體之間形成有效的鏈接,相互意思有效傳達、聯絡,形成網絡覆蓋,防止不同主體導致的多頭管理、各自為政的現象,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各級各類機構在各司其職的同時,形成合力,齊抓共管。如在西藏自治區,對于《格薩爾》的搜集、整理,1980年,設立了《格薩爾》搶救領導小組和搶救辦事機構;在部分高校成立《格薩爾王傳》搶救小組;在西藏那曲、阿里、昌都等史詩流傳較廣的地區,相繼設立了《格薩爾王傳》搶救點。[4]在《格薩爾王傳》的保護過程中,西藏各級各類機關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點,按照部門工作職責,有效配合,形成了對于民族傳統文化遺產保護齊抓共管的局面,拓展了傳統文化保護的覆蓋面,提升了傳統文化保護的效率、水平。而選擇立法規范的途徑,毫無疑問是在法治西藏背景下的最優選擇。
(二)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有針對性,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地方特色
在地方立法工作中,通過規范的制定、執行,使得各地方、各部門在賦予的權限范圍內,可以因地制宜,結合地方實際,貫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使各項政策、措施體現出明顯的地方性、針對性。如2005年西藏自治區制定《關于加強我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意見的通知》,要求組織科研機構等:“對我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研究,注重科研成果和現代技術的應用”。在法律規范授權范圍內,地方機關通過公布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建立傳承機制、加大經費投入等針對性的措施,形成地域特征顯著、民族遺產具象化突出的傳統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是原則性、概括性的,各地區、各部門要根據其負責范圍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點、現狀等,通過立法等行為,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原則性規范具體化,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納入法制軌道。如目前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民間藝人,在其技藝的傳承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規范內容,一般僅僅做了原則性的規定,對此,應當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將包括諸如技藝的傳承方式、方法、宣傳、資助等方面進行具體的規定,形成可操作的規范體系。
(三)在立法過程中要多措并舉,注重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輔助、支撐
在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地方立法工作中,要立足長遠、統籌規劃,防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要拓寬保護的措施,通過地方人大、政府的行為設立輔助規范,形成主體架構突出、輔助支撐齊備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系統。如在西藏,“藏語是西藏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口頭傳說和表述的重要媒介”[4]。作為民族地區,其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無法脫離本民族的獨特地域環境,藏語是西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重要媒介,西藏自治區人大根據《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等,于1987年通過《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規定》,要求西藏自治區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重視和加強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工作,在制度層面對于藏語文的應用進行規范。對于藏語言文字的使用進行規范,一方面是對于當地少數民族權利的保障,另一方面有利于保護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是以民族語言的媒介作用暢通為基礎的,此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輔助支撐對于相關的傳承不容忽視。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中,要形成對于民族語言等輔助的載體、媒介的關注,尤其是在立法層面的規范、引發,配置齊全輔助支撐,才可能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長遠發展。
(四)立法要有協調統一,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全方位、立體化法制體系
為傳承民族傳統文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完善法律、條例、辦法等制度體系建設,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規范化,同時有效整合各類資源,提高工作效能,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如西藏自治區制定了包括《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條例》《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遺產法>辦法》等規范,從制度建設上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但是,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種類眾多,我國的法治建設還在進行過程中,加之經濟基礎等限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制度體系建設還需要不斷加強。目前的制度規范等缺乏統一、系統的整合,同時缺乏針對某一部分問題形成專門的規范的機制,沒有形成立體性、全方位的法制體系,需要提升立法技術,協調立法主體,規范立法行為,健全立法內容。
為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各民族自治地方應該根據本地方的實際情況……制定地方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5]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立法工作中,既要有原則性的規定,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布局;又要有具體的實施細則,設定針對性、可操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范;此外還要設立體系完備、角度各異的諸如語言媒介等輔助支撐,使非物質文化遺產所承載的民族精神、傳統文化,得以繼承、創新,成為復興中國夢的支撐。
[參考文獻]
[1]楊力源.民族區域自治與民族事務治理的內在邏輯統一性探析[J].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14(6):62.
[2]辛紀元,吳大華,吳紀樹.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的不足及完善[J].貴州社會科學,2014(9):83.
[3]宋月紅,方偉.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及其地方立法研究[J].中國藏學,2005(3):43.
[4]馬寧.駁斥達賴集團的“文化滅絕論”[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17-18.
[5]鄒敏.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立法探析[J].寧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