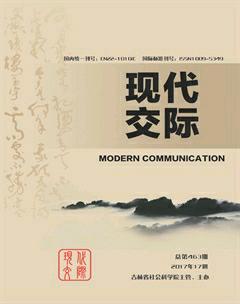探析清代臨汾地區地獄信仰文化
劉紅燕
摘要:隨著佛教地獄觀念與中國本土冥界觀念的不斷融合,其逐漸發展成為具有我國民間特色的地獄信仰文化,清代山西蒲縣東岳廟“地獄變”和地府建筑就為其典型代表,體現了因果報應、六道輪回的佛教地獄思想。基于這一信仰,清代該地方官員與民眾不斷對廟宇進行修繕和舉行圣誕祭祀等活動,由此發展成為當地民眾生活文化習俗的一部分,即為具有臨汾地區特色的地獄信仰文化,其在區域文化中發揮了倫理教化和娛樂狂歡的社會功能。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筆者通過整理碑刻與縣志來探討清代臨汾地區的地獄信仰文化,以此來闡述這一時期該地區的地獄信仰文化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點。
關鍵詞:臨汾地區 地獄信仰 蒲縣東岳廟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17-0079-02
佛教大約于兩漢時期傳入中國,地獄思想也隨之傳入,在佛教不斷中國化的進程中,地獄思想不僅與傳統的冥界鬼魂觀念相融合,而且深刻地影響著民間的生活、思想和文化習俗,因此,在清代臨汾地區民眾將佛教地獄思想中因果報應、六道輪回思想以及世俗故事轉化在泥塑和建筑布局上,如蒲縣東岳廟“地獄變”和地府建筑就是地獄信仰文化典型的表現形式。為了充分發揮地獄信仰文化在倫理教化和娛樂狂歡兩方面的社會功能,當地官員與民眾積極對廟宇進行修繕,定期舉行圣誕祭祀等活動,與地方區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具有區域特色的地獄信仰文化。
一、清代蒲縣東岳廟地獄信仰文化表現形式
清代臨汾地區民眾深受地獄思想的影響,而人們將這種思想通過一系列“地獄變”泥塑和地府建筑直觀地表現出來,使得這一時期民眾的地獄信仰文化更具世俗化和區域化特征。
(一)蒲縣東岳廟“地獄變”泥塑概況
地獄一詞梵語Nayaka的意譯,即“那落伽”“泥黎”等,漢譯為“不樂”“可厭”“苦具”“苦器”“為苦的世界”等,又因其處于地下,有八寒、八熱等名目,“寒”“熱”之外有“無間”“孤獨”等名目,有十八所之多,故俗稱“十八層地獄”。《三法度人經》云:“地獄有三種,一熱有十八所,二寒有十八所,三邊又名輕系,又名孤獨。”①
蒲縣東岳廟“地獄變”恰恰就是把佛籍中有關地獄思想的文字內容用塑像的形式表現出來,蒲縣東岳廟“地獄變”中有“爬心小地獄”“捆壓手腳,刀剖臍痕,鉤出其心,血滴慘魂”“坐北方劍樹為城,刀山為濺”“磨摧流血小地獄,剝皮揎革小地獄”,“油釜滾烹小地獄”“用空心銅柱,練其手足相抱,煽火焚燒,燙盡心肝”等的形象描述的場景,其中展現的沸鍋、銅柱、牛頭、獄卒、長叉、碓搗、鐵床等在上面的地府中都有形象的塑像表現,在康熙五十六年《重修地獄碑記》中記載有“佛經所載,寒冰、烈火、刀山、油鍋諸慘苦刑,真黃泉地獄此尤廟以傳,幽魂口,人心之陰險、暴燥、奸利、油滑,經上各以類應,此地獄之所由取也”②。因此筆者認為東岳廟中的地獄與佛教的地獄記載有著一定的關聯。
(二)地府建筑布局
地獄第一層是陰曹,也稱為上院,分東曹、西曹。在東西曹之間建于石臺階上之三間小殿堂即地藏祠,從地藏祠向下走十八級臺階之后,即為五岳殿、十王府,或稱下院、地府。地府由五岳殿和十王府組成。在康熙五十六年《重修地獄碑記》中記載:“吾蒲東岳神祠后,有隧道拾級而下十九級,其地下幽洞,而曹冥者,所謂地獄,地藏十王府焉。”③之后在清嘉慶二十一年《續修東神山太尉廟等各處工碑序》有關地府的記載有:“閣之北而下,視見古木蓊蔚中,陰陰露牛鬼蛇神妝,即佛家所謂地府者是也,遂觸目驚心,又覺果報之不爽。”④東西兩洞各有塑像五尊,即十殿閻軍王府和地獄冥罰。殿前牛頭馬面和各種鬼卒履行職守,面目猙獰,不善之徒正在地獄受刑。刑法計有寒冰、刀山、刮皮、鋸解、挖眼、血磨、油鍋、火盤等,慘不忍睹。
總之,在清雍正《重修諸祠創建僧房碑記》中記載有:“祠下設地獄,描盡獄中折磨。”③更明確地提到設立地獄的目的,而且不斷強化了民眾的地獄因果報應、六道輪回思想。蒲縣東岳廟中將人死后在地獄所受的種種酷刑,與地獄觀念以及民間故事人物相融合,不僅宣傳了懲惡揚善的思想,而且更體現了地獄信仰文化在清代臨汾地區的地域性這一特點。換言之,“地獄變”和地獄建筑可以說是當地民眾地獄信仰的“化石”,它不僅承載了民眾對于地獄的恐懼,而且又寄托了民眾的心理期望。換言之,這一時期地獄觀念已融入民眾的生活與思想文化之中,成為該地民眾的主要信仰之一。
二、地獄信仰文化對清代臨汾地區產生的社會影響
1.倫理教化方面
由于在我國古代神在老百姓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所以“事神”就成為我國古代官員與民眾的重要活動之一,而光緒《蒲城縣新志》中記載:“古昔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之不可慢,猶民之不可虐也”,也足以見得“事神”在地方治理和教化的重要性。在康熙五十六年該廟因“年深日久,神像剝落,廟宇難以棲神明,即非所以前觀后,有心者其能安然已乎?”④。基于這樣的情形,當地的“釋子僧官福沾,發大普原,愿新斯廟,募化糾首生員張守甯,諸信士馮慶冀等,各施銀一兩”⑤。在當地士紳和僧官的積極出資出力的修繕下,不僅使得該廟香火得以延續,煥然一新,而且還發揮了社會教化的功能,特別是為當地民眾創設了一個穩定慰藉心靈和祈福的場所,達到了教化人心的目的,進而營造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
清康熙三十年《補修東山碑記》:“至于左右兩司、天堂、地獄、山門諸工,謹俟得君子量力舉行,另為碑記可也。”⑥其中提到在修繕過程中,由于修繕的經費人力等問題,地獄這部分被安排在后續的修繕上。在清雍正三年《重修諸祠創建僧房碑記》:“祠下修設地獄,……數十年來,漸次修理。”⑦從此也進一步得出該地民眾積極進行修繕,以達到“善者見之益勤,惡者觀之而知懲”⑧的目的。在清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東岳正殿并各工碑記 》中:“計自乾隆辛丑起工,告竣于乾隆丁未,閱七稔而工乃成焉。其間動大工者數次,正殿、獻亭、戲樓、地獄、禪院,并彩繪門樓,工何巨也!雖曰人事,豈非神力哉?”⑨這其中又對地獄建筑進行了修繕,足以見得這一時期民眾對地獄的信仰極為虔誠。在清嘉慶二十一年《續修東神山太尉廟等各處工碑序》中:“其補修者,東西禪院四角樓,并后土祠、昌衍宮、清虛觀、地藏祠、地府遊廊”⑩。對地府建筑的再次修繕見得地方官員與民眾對地獄信仰的重視。endprint
清后期,當地官員、士紳和民眾依舊對東岳廟中地獄建筑不斷地進行修繕,在清同治八年《重修東神山廟記》中對“地獄內窯孔樓舍,其一椽一柱,寸甓寸甍”B11重新進行補葺。在清末該地民眾依舊注重修繕地獄建筑。東岳廟修繕一直持續到清光緒二十八年,在《重修華池廟地藏祠獻亭及各處碑記》中記載由于“地藏祠傾頹為尤甚。歲甲申,家君督修……地藏祠之廈宇重為修理”B12,當地民眾個人重修地藏祠可見這一時期地方官員、士紳與民眾依舊對地獄信仰極為重視,地獄信仰已成為當地民眾的主要信仰之一。這一時期民眾已把地獄觀念融入他們的生活與文化之中,發展為這一時期具有臨汾地區特色的區域文化。
2.娛樂方面
相傳東岳大帝掌管地獄生死大權,而且人們深受地獄觀念的影響,所以其在人們心目中占據重要地位,在每年農歷三月二十八“東岳大帝”生日這天,人們在蒲縣東岳行宮都會舉行隆重的圣誕慶典祭祀活動,歷代延續。圣誕慶典儀式從三月初就開始陸續準備,農歷三月二十之后,整個東岳廟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廟內各個殿宇供奉貢品,慶典樂隊組織排練,祭祀議程規范嚴謹,其場面隆重而又神圣。后發展到清代,蒲縣東岳廟的圣誕慶典活動主要由住廟僧人和民間的監視糾首共同組織承辦,其中監視糾首負責慶典規程安排、組織策劃,而住廟僧人則負責設醮念經,祈福祭祀,等等。在大清順治戊子年三月二十八日立的《東岳神行宮還愿小記》中記載有:“茲者本邑西社居民張進等,竊謂牛斗不辰,生逢明季,天地□□極蕩,宇宙倏爾乖離,綠林兵火交加,饑餓篤于頻仍,溝壑轉填,四方流散。進等緣籍神默,并幸重睹昌辰,獲免渝胥于風波,俾脫窮途之水火,于是閏興念,僉議進與謝吉、張國槐、關愛、全宋相、楊登第等,為三會神首,糾倡眾信,各納朱提白紫虛高真,建壇禮醮,處□神庥,三年一周,九載云滿,仍企雨旸以時若,愿國泰而民安,寢造圣像行駕,傍倚二臣。丁亥春暮,已迎妥于行宮,適酬三祀一愿,兩鑄一像獨尊,更懸金匾,曰“靈震岱宗”,赫矣,前愿潔誠告謝,恢乎,愿依期圓周伏。”B13這也是該地區民眾在三月二十八日祈福還愿的期望,漸成為當地固定的民俗節日。
此外在《祝賀圣誕碑記》圣誕祭祀的神靈:“含弘廣大,覆育萬有,上則福國而享其磐石,中則福民而樂其康寧,下則福物而絕其夭扎,……故三月廿八乃圣誕辰也,蒲之士匍匐進香,竭誠享獻,不獨一歲為然。”B14《閏三月廿八日重祝圣誕碑記》中“每歲三月念八,士女云集,香火絡擇,又吾蒲一勝會也”B15。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民眾積極舉行圣誕祭祀達到“神人胥和,民物滋豐”。清嘉慶十六年《重慶圣壽碑記》中有“每逢三月二十八日為帝誕辰,合邑建醮,演樂費用浩大,較之他廟不止什佰計,相沿已久而不能或廢者,說之故也。今閏逢誕月,始而恭祝,舉舊典也;歷一月而又祝,亦舊典也”B16。
在清代,從順治一直到嘉慶民眾在每年農歷三月二十八舉行盛大的祭祀慶典,在活動規模、費用支出等方面足以見得該地民眾對地獄信仰的重視程度,也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形成的地獄信仰文化為當地民眾創設了一個穩定慰藉心靈和祈福的氛圍,也體現出其大眾化、地域化的特色。
總之,通過對清代蒲縣東岳廟的“地獄變”、地獄建筑、地方修繕以及圣誕祭祀,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清代臨汾地區民間的地獄觀念已經完全融入民眾的生活,其主要表現在影響臨汾地區民眾的生活習俗以及民眾的思想狀況。雖然我們只能探究出清代臨汾地區民間地獄信仰的一部分,不能較為全面地反映這一時期大眾所具有的時代精神,但可以大概了解那個時代民眾的生活、思想狀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這一時期該地區民間百姓的生活狀況和內心訴求,所以筆者認為這一時期該地區的地獄信仰文化更具有大眾化和地域性的特征。
注釋:
①釋道誠.釋氏要覽校注[M].富世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62.
②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116.
③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116.
④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99.
⑤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99.
⑥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84.
⑦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116.
⑧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116.
⑨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192.
⑩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103.
B11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322.
B12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342.
B13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73.
B14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74.
B15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169.
B16王東全.三晉石刻大全(蒲縣卷)[M].山西:三晉出版社,2013:218.
參考文獻:
[1]杜斗誠.地獄變相初探[J].敦煌學輯刊,1989(1).
[2]范文美.蒲縣東岳廟“地獄變”之調查與研究[D].蘭州大學,2011.
[3]張宇.蒲縣東岳廟會和“四醮朝山”[D].山東大學,2012.
[4]楊兵,馮蓋驊.蒲縣東岳廟和廟會及其思考[J].世界宗教文化,2005(4).
[5]石國偉.論蒲縣東岳信仰的地方化[J].山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
責任編輯:孫 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