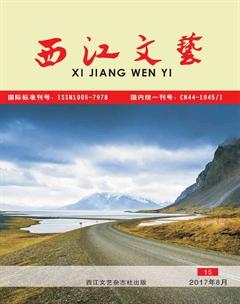哲學意味在階梯狀相關美術中的典型性體現
【摘要】:印度美術蘊含著的宗教、哲學意義十分廣闊。伴隨著各勢力的此消彼長,印度美術的發展也呈現出不一樣的階段特色。雖然印度美術發展的最初并不以單純審美情趣作為主要出發點,它往往隱喻著各類哲學思想,但是在西方美術全球化,東方美術融合化的今天,究竟東方或亞洲美術的美術血脈鼻祖淵源從何處而來,什么物質使它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沉淀出其獨有的神性審美意趣和氣質,對于今日美術又有何種教義”?筆者遂從印度宗教背景之下,對印度美術發展過程中之由來、典型為例作跨時空歷史性簡要探究。
【關鍵詞】:古印度美術;哲學思維;象征
一、 應用性——以建筑為最高水平的工藝美術載體
在古印度早期,美術品并非獨立存在。而是起到某種職能作用為具體對象服務的工具或媒介。
1.伊斯蘭教神廟與印度本土宗教融合的新意
印度文化從哲學到美術方面都具有強大的包容性。以吉雅斯一世墓葬建筑來說,雅致的格調同印度審美極其不同,而其中的文案樣式仍帶有很強的印度特色。這種新型雙重特色建筑是這一時期美術風格的典型代表,既不從屬也不對抗,是二者共通共融的發展形勢,正如同印度哲學理念一般,包容性是創造新可能的重要基點,只有不斷吸納,不斷探求摸索,事物才能呈現出新的或者隱藏的面貌。
2、奴隸時期尖塔的象征性存在人治對真理的誤讀
庫特伯·米納爾尖塔是奴隸王朝時期的代表性建筑,它也是最早的伊斯蘭風格美術之一。尖塔傲然挺立,造型獨特,自下至上逐漸變細,整體給人莊重的壓迫感。不難發現這種壓迫感是尖塔的特殊造型,是奴隸社會為了統治目的而建造的,用宗教藝術的形式來強化說服力,這種不平等的,有人性欲望的追求是一種認知自體化的體現,是對梵天的誤解,注定不能在宗教哲學領域立住腳跟。因而奴隸王朝在短暫的穩定之后便結束了,只有庫特伯·米特爾尖塔還留在今天,從她的塔身與裝飾中仍蘊含著無盡的印度歷史經驗與哲學文化底蘊。仔細觀察塔身上的紋樣,這是由印度當地工匠打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號。盡管尖塔是伊斯蘭教審美風趣的,但卻奇跡般地和印度紋樣呈現在統一的建筑體中,并且使得光滑的塔身增加了豐富性與層次感。這不得不說是文化融合的瑰寶,審美交流的創造。
二、認知性———以動物為認知媒介的造物藝術
那么古印度人民在何時享有最富足的生活狀態呢?正是在哈拉巴文化時期,經濟社會帶來的富足間接性成了藝術文化的滿足力。因而這一時期文物具有典型性。在古印度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保障的情況下,他們的精神文化又出現了怎樣的變化呢?同宗教的救贖主義相關的,在缺乏科學論證的體系下,人們選擇想象推理,人們選擇相信萬物有靈,對生命充滿敬畏,對豐產,富榮充滿了向往,形容了一位掌管生命的神—生殖女神。期初在石器和青銅器以動植物為象征手段表達這種對生殖女神的崇敬。
在許多早期或者是原始美術的描摹時期,“神牛”作為一種象征符號在印章或者壁畫藝術中被廣泛使用,它的原身牛作為農耕文明勞作文化的重要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處于被奴役的職能地位。也許正是由于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反復認識接觸,古印度人對神牛神話的信仰性會受到懷疑或消弭,基于宗教哲學體系強大的說服力量,他們體會到眼中看到的日常萬象并不能涵蓋其中所蘊含的真理性事實。這樣一來,哲學意義上的否定性思維在其中做了決定。因此在莫恒佐-達羅遺址中出土的許多印章中可以看到對神牛的描繪從早期的稚拙感不斷演變,包括對公牛形象的想象化面罩裝飾與夸張刻畫以及衍生創造的獨角獸文化、犀牛文化等;正是這種否定意識使得印度文化在今天具有了獨特的文化符號。
三、單純化——針對復雜群像的符號視覺文化美術
最初印度本土的陶塑泥塑等風土人情是跟側重于神秘而輕快地非寫實性藝術表達,這種非寫實性是由于技術水平落后不成熟嗎?應當不是,反觀同一時期的公牛形象,其中簡練高超的雕刻技法能夠體現出古印度人民在當時已經對雕刻技法有相當造詣,是審美的取向引導藝術表現。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古印度早期的巖畫,脫離了工藝載體的新行為,被稱為古印度早期的繪畫,重點在于描繪行為中“繪”這個特殊行為的產生。以工藝品為承載的藝術行為發展到了更加純粹的地步,即符號藝術,視覺文化的初次登場。不同的色塊作為畫作背景可以展示出畫面不同的內涵并應用到畫作解釋情感。它不以作畫原理為目的,而是以畫面背后呈現的解決之道為追求對象,這是印度實用主義傾向在繪畫中的體現。
四、主體化——視角轉變后更具現實意義的思路轉變
而后考古學家們又發現了人像作為完整塑造對象出現在古印度美術體系中,神像、男人、女人等等。
前面提到,但凡是存在于時空中的客體,其背后一定有時代地域族群等多元文化支撐。吠陀時代環境兇險,戰爭社會動蕩,在戰爭不斷,在物質環境難以得到保全的情況下,人類往往會在精神方面建立新的欲望訴求。因此宗教環境等是印度民族在戰爭環境主觀能動形成的一個客體。這樣解讀宗教定義同費爾巴哈的宗教觀點即”宗教世界是脫離于現實世界,二者相互割裂的主觀創造”是相悖的,印度哲學體系下地宗教美術作為載體和主體表達“本我“對梵天的反饋,是需要強烈的“我體”因子的,這種自我因子不代表藝術家的個人風格或關注點(雖然不可避免),他更強調一種反饋的力量,就是說,一個印度工匠在創作過程中,雖然會由于本民族勇敢剽悍的民族特性或者藝術家本人的身型特征,因此印度宗教藝術中的佛像人形化往往身形矮小,姿態有力。這種因素對所成造像出現一定影響,但是這些影響只是體現在線條流暢性,石材光滑度,色彩飽和度等造像藝術的格調成像;而并非造像元素,造像目的這些近當代關注的要素。那么造像藝術人形化這一關注對象的轉變是誰在起作用呢?答案就是印度哲學觀念中的“梵我合一”這一經典思想的啟迪。印度佛教崇尚多神論,認為神佛是不具備外在形象的,佛法都在心中,可以說自體才是佛法存在的客觀載體,真理意味的梵天引導客觀載體(即本我)發生活動,進行作用,才是神祗的體現,出于對神祗的崇拜,吠陀時期發展的各種奇風異俗反映到實踐活動,實用主義這一概念在關注點的轉變后顯得愈發傾向于方法論作用。
小結:
本文在個人的專業領域去探究印度美術學其實是難以避免出現狹隘經驗論的。從探究主題到論證實例,或多或少必然存在個人化的解讀。在學習了古印度宗教美術的相關問題之后,個人對古印度宗教美術有了一定了解,但又更加地明晰了自己無知的知識貯備量,因此在論證述的方面存在主觀性,這在日后還需要二次甚至多次研究,對于美術學的探索絕不能再此為止,廣博的宗教美術中還有許多經驗未曾發掘,正如文中提到的探究精神,在論文截止后仍就是筆者作為學術工作者面對知識學術的態度。
作者簡介:張艾嘉(1996.04—),女,學歷:本科,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研究方向:美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