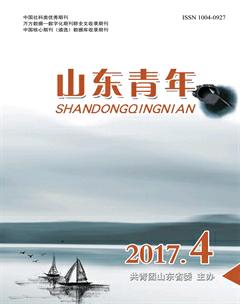誠(chéng)信在職業(yè)生涯中的作用分析
蔣雨昕++曹克亮?オ?
摘要:
學(xué)業(yè)和職業(yè)可以說(shuō)是每個(gè)人必經(jīng)的兩個(gè)階段,不同的只是在這兩方面的成就大小,在我們的學(xué)業(yè)生涯我們學(xué)習(xí)知識(shí)和技能的同時(shí)要考慮職業(yè)的導(dǎo)向作用,在學(xué)生階段就應(yīng)該有一個(gè)清晰的職業(yè)規(guī)劃和理想,對(duì)于以培養(yǎng)職業(yè)應(yīng)用型人才為目標(biāo)的高職生來(lái)說(shuō)更要認(rèn)清這一點(diǎn),理論和實(shí)踐是分不開(kāi)的,學(xué)習(xí)的知識(shí)技能與職業(yè)的規(guī)劃最后都必須有一個(gè)具體的工作來(lái)實(shí)現(xiàn),而就業(yè)便是有一個(gè)工作來(lái)檢驗(yàn),實(shí)現(xiàn)自我。
職業(yè)生涯是指一個(gè)人一生中所有與職業(yè)相聯(lián)系的行為與活動(dòng),以及相關(guān)的態(tài)度、價(jià)值觀、愿望等連續(xù)性經(jīng)歷的過(guò)程,也是一個(gè)人一生中職業(yè)、職位的變遷及工作、理想的實(shí)現(xiàn)過(guò)程。職業(yè)生涯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過(guò)程,它并不包含在職業(yè)上成功與否,每個(gè)工作著的人都有自己的職業(yè)生涯。
關(guān)鍵詞:誠(chéng)信; 事業(yè);社會(huì);國(guó)家政府
一、誠(chéng)信是個(gè)人的立身之本
誠(chéng)信是個(gè)人必須具備的道德素質(zhì)和品格。一個(gè)人如果沒(méi)有誠(chéng)信的品德和素質(zhì),不僅難以形成內(nèi)在統(tǒng)一的完備的自我,而且很難發(fā)揮自己的潛能和取得成功。程顥程頤指出:“學(xué)者不可以不誠(chéng),不誠(chéng)無(wú)以為善,不誠(chéng)無(wú)以為君子。修學(xué)不以誠(chéng),則學(xué)雜;為事不以誠(chéng),則事敗;自謀不以誠(chéng),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chéng),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誠(chéng)”不僅是德、善的基礎(chǔ)和根本,也是一切事業(yè)得以成功的保證。“信”是一個(gè)人形象和聲譽(yù)的標(biāo)志,也是人所應(yīng)該具備的最起碼的道德品質(zhì)。孔子說(shuō):“信則人任焉。”“人而無(wú)信,不知其可也。”誠(chéng)于中而必信于外。一個(gè)人心有誠(chéng)意,口則必有信語(yǔ);心有誠(chéng)意口有信語(yǔ)而身則必有誠(chéng)信之行為。誠(chéng)信是實(shí)現(xiàn)自我價(jià)值的重要保障,也是個(gè)人修德達(dá)善的內(nèi)在要求。缺失誠(chéng)信,就會(huì)使自我陷入非常難堪的境地,個(gè)人也難于對(duì)自己的生命存在做出肯定性的判斷和評(píng)價(jià)。同時(shí),缺失誠(chéng)信,不僅自己欺騙自己,而且也必然欺騙別人,這種自欺欺人既毀壞了健全的自我,也破壞了人際關(guān)系。因此,誠(chéng)信是個(gè)人立身之本,處世之寶。個(gè)人講求道德修養(yǎng)和道德上的自我教育,培育理想人格,要求以誠(chéng)心誠(chéng)意和信實(shí)堅(jiān)定的方式來(lái)進(jìn)行自我陶冶和自我改造。中國(guó)古代思想家強(qiáng)調(diào)“正心誠(chéng)意”和“反身而誠(chéng)”在個(gè)人道德修養(yǎng)中的地位和作用,認(rèn)為修德的關(guān)鍵是有一顆誠(chéng)心和一份誠(chéng)意。誠(chéng)意所達(dá)到的程度決定修德所能達(dá)到的高度,正可謂“精誠(chéng)所至,金石為開(kāi)”,“天下無(wú)不可化之人,但恐誠(chéng)心未至;天下無(wú)不可為之事,只怕立志不堅(jiān)。”所以,中國(guó)人特別強(qiáng)調(diào)“做本色人,說(shuō)誠(chéng)心話,干真實(shí)事”。
二、誠(chéng)實(shí)是取信于人、處己立身、成就事業(yè)的基石,是每個(gè)人生活的準(zhǔn)則
“誠(chéng)信”是一種世界觀,又是一種社會(huì)價(jià)值觀和道德觀,無(wú)論對(duì)于社會(huì)或個(gè)人,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duì)于一個(gè)國(guó)家而言,“誠(chéng)信”可以說(shuō)是立國(guó)之本。國(guó)家的主體是人民,國(guó)家的主權(quán)也歸于人民。中國(guó)自古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明訓(xùn),這些話至今仍然是至理名言。國(guó)家依靠什么去團(tuán)結(jié)人民呢?靠的是以“誠(chéng)信”取信于民的人文精神。
孔子的“信則人任焉” “自古皆有死,民無(wú)信不立” “人而無(wú)信,不知其可也” “民以誠(chéng)而立”;孟子論誠(chéng)信 “至誠(chéng)而不動(dòng)者,未之有也;不誠(chéng),未有能動(dòng)者也”;荀子認(rèn)為“養(yǎng)心莫善于誠(chéng)”;墨子曰“志不強(qiáng)者智不達(dá),言不信者行不果”;老子把誠(chéng)信作為人生行為的重要準(zhǔn)則:“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莊子也極重誠(chéng)信 :“真者,精誠(chéng)之至也。不精不誠(chéng),不能動(dòng)人”。莊子把“本真”看做是精誠(chéng)之極至,不精不誠(chéng),就不能感動(dòng)人,這就把誠(chéng)信提高到一個(gè)新的境界;韓非子則認(rèn)為“巧詐不如拙誠(chéng)”。總之,古代的圣賢哲人把誠(chéng)信作為一項(xiàng)崇高的美德加以頌揚(yáng),顯示了誠(chéng)信在中國(guó)人心目中的價(jià)值和地位。從古到今,人們這么重視誠(chéng)信原則,其原因就是誠(chéng)實(shí)和信用都是人與人發(fā)生關(guān)系所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規(guī)范,沒(méi)有誠(chéng)信,也就不可能有道德。所以誠(chéng)信是支撐社會(huì)的道德的支點(diǎn)。
誠(chéng)信是治理國(guó)家必須遵守的規(guī)范,維系著一個(gè)政府和國(guó)家的信譽(yù),一個(gè)政府、國(guó)家失去了誠(chéng)信,就失去了信譽(yù),失信于民,失信于天下,就會(huì)喪失民心,喪失天下。
三、誠(chéng)信是企業(yè)和事業(yè)單位的立業(yè)之本
誠(chéng)信作為一項(xiàng)普遍適用的道德原則和規(guī)范,是建立行業(yè)之間、單位之間良性互動(dòng)關(guān)系的道德杠桿。誠(chéng)實(shí)守信是社會(huì)主義職業(yè)道德建設(shè)的重要規(guī)范。誠(chéng)實(shí)守信是所有從業(yè)人員在職業(yè)活動(dòng)中必須而且應(yīng)該遵循的行為準(zhǔn)則,它涵蓋了從業(yè)人員與服務(wù)對(duì)象、職業(yè)與職工、職業(yè)與職業(yè)之間的關(guān)系。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的活動(dòng)都是人的活動(dòng),為了發(fā)展就不能不講求誠(chéng)信。因?yàn)榘l(fā)展既蘊(yùn)涵著組織本身實(shí)力和生存能力的增強(qiáng)與提升,又蘊(yùn)涵著組織與組織、組織與外部以及組織內(nèi)部各要素之間關(guān)系的優(yōu)化與完善。無(wú)論是組織本身實(shí)力和生存能力的增強(qiáng)與提升,還是組織內(nèi)外關(guān)系的優(yōu)化與完善,本質(zhì)上都需要誠(chéng)信并且離不開(kāi)誠(chéng)信。誠(chéng)信不僅產(chǎn)生效益和物化的社會(huì)財(cái)富,而且產(chǎn)生和諧和精神化的社會(huì)財(cái)富。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社會(huì),“顧客就是上帝”,市場(chǎng)是鐵面無(wú)私的審判官。企業(yè)如果背叛上帝,不誠(chéng)實(shí)經(jīng)營(yíng),一味走歪門斜道,其結(jié)果必然是被市場(chǎng)所淘汰。誠(chéng)信是塑造企業(yè)形象和贏得企業(yè)信譽(yù)的基石,是競(jìng)爭(zhēng)中克敵制勝的重要砝碼,是現(xiàn)代企業(yè)的命根子。
四、誠(chéng)信是國(guó)家政府的立國(guó)之本
國(guó)家的主體是人民,國(guó)家的主權(quán)也歸屬于人民。中國(guó)古代政治倫理強(qiáng)調(diào)“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認(rèn)為國(guó)家的領(lǐng)導(dǎo)者應(yīng)當(dāng)以誠(chéng)心誠(chéng)意的態(tài)度和方法去取信于民,進(jìn)而達(dá)到人民安居樂(lè)業(yè),國(guó)家太平清明。唐代魏征在給太宗皇帝的上疏中寫道:“求木之長(zhǎng)者,必固其本;欲流之遠(yuǎn)者,必浚其源;思國(guó)之安者,必積其德義。”(《貞觀政要·論君道第一》)治國(guó)之道,在于貴德崇義,而德義的主要內(nèi)容則是誠(chéng)信。柳宗元說(shuō):“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指出:“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guó)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wú)以使民,非民無(wú)以守國(guó)。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guó)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guó),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致于敗。”以上言論說(shuō)明誠(chéng)信是領(lǐng)導(dǎo)者治理國(guó)家的基本準(zhǔn)則,誠(chéng)信構(gòu)成國(guó)德,支配國(guó)運(yùn),沒(méi)有誠(chéng)信的國(guó)德就不能擁有長(zhǎng)久而向上的國(guó)運(yùn)。在現(xiàn)代社會(huì),民主政治成為一種潮流和趨勢(shì),更要求把誠(chéng)信作為治理國(guó)家的基本原則。政治的核心是權(quán)力。政治權(quán)力的歷史形態(tài)是私權(quán)或集權(quán),而民主政治下的權(quán)力是公權(quán)。公權(quán)意味著權(quán)力歸人民所有,本質(zhì)上是為人民服務(wù)的,權(quán)力的合法性來(lái)自人民的信任。失去人民的信任便失去了權(quán)力合法性的依據(jù)。我國(guó)是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建設(shè)高度的民主政治是社會(huì)主義政治文明建設(shè)的重要任務(wù)。
誠(chéng)信原則逐步上升為一種法律原則始自羅馬法,后來(lái)被法制史中重要的民法所繼承和發(fā)展,比如法國(guó)民法、德國(guó)民法、瑞士民法等,如《瑞士民法典》總則中的第二條規(guī)定:“任何人都必須誠(chéng)實(shí)地行使其權(quán)利并履行其義務(wù)。”誠(chéng)實(shí)信用也是我國(guó)現(xiàn)行法律一個(gè)重要的基本原則,在《民法通則》、《合同法》、《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法》中有明確的規(guī)定。由于其適用范圍廣,對(duì)其他法律原則具有指導(dǎo)和統(tǒng)領(lǐng)的作用,因此又被稱為“帝王規(guī)則”,可見(jiàn)“誠(chéng)實(shí)信用”是并非一般的道德準(zhǔn)則。在誠(chéng)實(shí)信用成為法律規(guī)范的時(shí)候,違反它所承受的將是一種法律上的責(zé)任或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這種法律后果可以是財(cái)產(chǎn)性的,也可以是人身性的;可以是民事的、行政的,甚至可以是刑罰。因此,誠(chéng)實(shí)信用又是支撐社會(huì)的法律的支點(diǎn),是法律規(guī)范的道德。
誠(chéng)信為政, “欺民”不可,所以有“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說(shuō)。唐代魏征把誠(chéng)信說(shuō)成是“國(guó)之大綱”,可見(jiàn)“誠(chéng)信”之重要。
結(jié)論
誠(chéng)信是一種人人必備的優(yōu)良品格,一個(gè)人講誠(chéng)信,就代表了他是一個(gè)講文明的人。講誠(chéng)信的人,處處受歡迎;不講誠(chéng)信的人,人們會(huì)忽視他的存在;所以,我們每個(gè)人都要講誠(chéng)信。誠(chéng)信是為人之道,是立身處事之本。誠(chéng)信是一個(gè)道德范疇,是公民的第二個(gè)“身份證”,是日常行為的誠(chéng)實(shí)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稱。即待人處事真誠(chéng)、老實(shí)、講信譽(yù),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諾千金。企業(yè)誠(chéng)信,靠企業(yè)的管理制度,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維持,更靠具有誠(chéng)信品質(zhì)的員工去實(shí)現(xiàn)。沒(méi)有誠(chéng)信的員工,就不可能有誠(chéng)信的企業(yè)。有時(shí)候,哪怕只有一個(gè)員工,甚至只有一次偶然的失信,對(duì)企業(yè)所造成的負(fù)面影響都可能是無(wú)法挽回的。正因?yàn)檫@一原因,希望謀求理想職業(yè)的大學(xué)生,必須在誠(chéng)信上下功夫,做人,做事,處事,努力做到坦誠(chéng)真實(shí)。言行一致,將是自己受益終身。
[參考文獻(xiàn)]
[1]《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
[2]《論語(yǔ)》、《貞觀政要·論君道第一》、《資治通鑒》、《瑞士民法典》。
[3]《民法通則》、《合同法》、《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法》。
(作者單位:中國(guó)計(jì)量大學(xué)現(xiàn)代科技學(xué)院,浙江 杭州 31001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