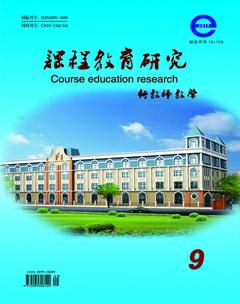重視文本意義
張學武
對于文學作品的解讀,我們可以找到許多說法。比如,美國人哈羅德·布魯姆的“誤讀”說;比如,古人的“詩無達詁”,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比如,“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比如魯迅先生關于《紅樓夢》的那段被反復引用的著名論述。這些觀點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在閱讀作品時,作為對象的文本是共同的,但不同的閱讀者因其閱讀興趣和習慣所形成的定勢不同,就會以自身的閱讀視域去選擇和同化這個閱讀對象。這樣,顯而易見,政治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眼中的《紅樓夢》,與從審美角度出發的美學家眼中的《紅樓夢》必是很不相同的。
新編高中語文教材選編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并把審美鑒賞閱讀置于了很重要的地位。這應該說是對以往教材選編原則的一種突破和矯正。如果不是我牽強附會的話,我們應該明白新教材是在告訴我們:請以審美的眼光閱讀文學作品。問題是,我們以往的閱讀方式存在著一種不容忽視的毛病,這種毛病似乎與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實質是文化觀念)中強調總體上的文化致用性和藝術致用性有關,同時,也與我們更多注重于對學生的思想教化有關,那就是往往過多地注重于作品外的背景性因素。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反復強調“知人論世”,忙于解決作家的生平、游蹤、履歷、思想意識等背景性因素,還一定要從這些背景性因素中搜求出一種符合教化意義的主旨來。彷佛這樣一來,作品的一切問題就得到了闡釋。而作品本身所蘊含的審美意義卻被遠遠拋開,打入冷宮。誠然,背景是了解作品的一種形式,但它遠遠無法替代作品的全部或主要素質,特別是審美素質。盡管再客觀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都是作者戴著“有色眼鏡”觀照世界的結果,無法排除背景性因素對作品的影響,但從背景到作品,還有作家的“有色眼鏡”——主體的內化功能。在內化行為中,背景的作用,我們把它看成是一種投影,而不是自然地生成作品素質。決定作品素質的作家感受還有很多為上述背景所無法涵蓋或替代的因素。
相信大家都有過這種體驗,平時我們閱讀文學作品,并不了解上述背景性因素,但我們依舊獲取了情感的愉悅,心靈的進化,精神的升騰。其實,這正是我們運用了體驗的審美方式,自覺地調動審美感知具體而微地體察領略了對象——文本(作品),進入了文本之中,進而跟文本所展示的境域融化為一體,找到了超越時空的感情共鳴。這大概也就是文學史中一些作品甚至一些名句經久不衰的原因。因為它表達或提純了人類的普遍心理和精神價值,使閱讀者尋求到了情緒上的共感,具有了永恒的藝術魅力。
文學作品誕生之后,就成了“社會”的“歷史”的,隨著時空條件的變化,其原初的感染力也就隨之減弱。如它還能流轉在人們的謦頦唇吻之間,應該說是因了它本身所蘊含的審美意義——以個體的獨特體驗形式表現出的人類普遍的情感意味,而不全是從背景性因素搜求到的意義。例如李清照的“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載不動,許多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是女詞人對相思情的獨特體驗和捕捉。但我們閱讀時不一定非要知道李清照是何人,作于何時、何地等背景性因素,才能體味出來。因為心心相印的相思情,是人類最重要的情感之一。
如果拋開這些,單從指導學生迎接高考的角度來說,訓練學生對文本意義探求,更是不可忽視而應該加強的。因為高考試卷中出現的文學作品,許多是無法依靠背景性因素去解讀的。
因此提出“重視文本意義”這一命題也不是荒唐的事吧。
以巴金先生的《燈》為例。在鑒賞此文時,我讓學生先不要去關注背景性因素,就作品本身閱讀后,以學習小組為單位進行討論:你覺得《燈》蘊含著怎樣的主題?結果是大部分小組認為它表達了人們在生活中應該為自己點燃一盞燈(理想也好,信念也好……),用來照亮自己的人生道路這樣一種哲理。在這里不揣冒昧地說一句,如果《燈》還能經久不衰,起決定作用的恐怕是它所蘊含著的這種哲理,而不是那個政治層面上的意義。不知然否?
最后想要強調的是,提倡“重視文本意義”,并不是排斥那些有利于了解作品的背景性因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