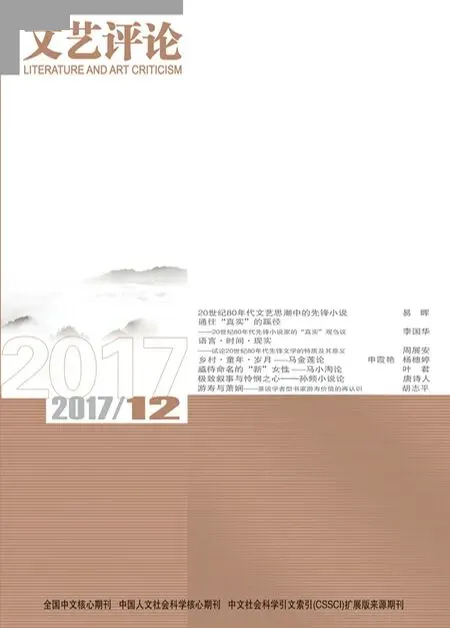通往“真實”的蹊徑
——20世紀80年代 先鋒小說家的“真實”觀芻議
○李國華
通往“真實”的蹊徑
——20世紀80年代 先鋒小說家的“真實”觀芻議
○李國華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壇,“真實”是一個畫上了胡塞爾式的刪除線的概念,不同作家的理解不僅大相徑庭,而且截然相反。即使是一些現在看起來比較相近或相似的作家,他們的“真實”觀也是不太一樣的。比如史鐵生和余華,單獨看余華的《虛偽的作品》,也許會認為他們共享著一致的“真實”觀;如果只看王朔在《王朔文集》上的序言,也會覺得王朔和余華具有很明顯的家族相似性。但實際上,從《人民文學》1989年第3期上刊布的三篇文章來看,史鐵生、余華和王朔的“真實”觀,差別極大。而且,這種極大的差別,應該說在很好地顯現了不同作家的“真實”觀的同時,凸顯了20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家的獨特之處。
一
《人民文學》1989年第3期以欄目“對話與潛對話”的方式刊登了史鐵生《“神經內科”》、余華《我的真實》和王朔《我的小說》三篇短文,意在標識三位作家在小說觀念上的分歧。史鐵生的核心意思是要找到“永遠變不了的東西”,“只起個名字,確實沒有太大的意義”①。在他看來,小說被批評家命名為“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新潮”“后新潮”什么的,并不重要,也沒有太大的意義,重要的是“真實”是否得到了確認,如同當年自己身患的疾病是否得到了確診一樣。史鐵生認為遺憾的是,當年自己的病得到了各種名目的癥斷,但并未確診,現在關于文學的討論也沒有找到那個“永遠變不了的東西”。
余華大概不會反對史鐵生對“永遠變不了的東西”的相信,因為他在《我的真實》中說“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面,是不存在混亂的,因為它沒有時間的概念”。“變化”是和“時間”緊密相關的一個概念,“沒有時間的概念”意味著沒有“變化”的概念;沒有“變化”的概念,也就意味著有“永遠變不了的東西”。因此,余華在文中說:“一個人死了,在我的精神里卻是活著的,因為我老記住他。我一記住他,就意味著他還活著。而很多活著的人我已經忘記他了,就證明他已經死了。”人死了,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但余華以記憶的方式改變了這一“變化”,并轉為“永遠變不了的東西”。這是余華和史鐵生相通之處。不過,這相通之處并不妨礙余華走上與史鐵生不同的蹊徑。余華明確表示有兩種不同的“真實”,一種是自己所有的創作都在努力接近的“真實”,另一種是“生活里的那種真實”,那種“實際上是不真實的”“真實”。簡言之,史鐵生可能不愿意花費太大力氣去進行名實之辨,更希望通過某種直觀的方式去把握“永遠變不了的東西”,而余華對名實之辨是感到極大興趣的,他要頑強地表達自己的“真實”觀,以致于不惜將“生活”斥為“一種真假參半的、魚目混珠的事物”。
王朔與余華剛好相反。雖然王朔也許是習慣性唱反調,但他在《我的小說》中所說的一些意見,仍然是有重要的討論價值的。他開篇提到一個重要的批評現象:“有人不喜歡我的小說,說我的小說不是小說。其實,只不過覺得不是新潮小說罷了。”撇開字里行間透露出的王朔對于馬原、余華等人代表的新潮小說贏得批評界更高贊譽的羨慕和不滿不論,可以看到的是,在1989年的中國文壇上,先鋒小說已經有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引起了同行的意見;而“我的小說不是小說”之類的判斷則意味著先鋒小說背后的小說觀念已經是一種有力量的排他性的觀念存在。在這樣的壓力之下,王朔表示:“我寫東西都從我個人實例出發。而我接觸的生活,使我覺得只要把它們描述出來就足夠了。所以寫的時候我總極力抹煞自己。我不想把自己的東西加到生活上去。而且要把生活寫出來,筆力就已經承擔不住……先鋒的和前衛的文學當然要有,但比例應當控制,總不能搞成這樣,讓人家說你們都弄成同性戀俱樂部了……”雖然王朔在《王朔文集》序言中的一些說法會給人王朔頗愿成為同性戀俱樂部會員的感覺,但還是應該注意到,他自覺地站到了余華們的對立面,他的言議中也可以抽繹出幾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即:
第一,從個人出發的寫作,未必就是現代主義的寫作。王朔甚至認為:“現代主義小說在文學史上地位很高,但總起來看還是現實主義小說地位更高。我倒承認我這是現實主義的。”考慮到近十年多來中國批評界的一些反復現象,有批評家開始重新看待18、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小說的價值和意義,王朔的意見也許不妨得到更多的肯定。那么,余華式的以個人“真實”為真的“真實”的觀念,就有重新討論之必要。
第二,生活與創作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唯一的。余華將生活視為“真假參半、魚目混珠的事物”,這在王朔看來,可能正好是作家意識到“筆力就已經承擔不住”“生活”,就退而求其次,逃避到個人的真實中去的辦法。在此意義上,現實主義的反映論不是失效了,而是作家失去了直面生活的魄力和勇氣。
第三,余華式的方式,可能不過是“把自己的東西加到生活上去”。所謂“把自己的東西加到生活上去”,實際上就是近些年中國批評界學步日本批評家柄谷行人反復討論的“透視法”問題。在“透視法”的作用下,作家完成了極為重要的替代性想象,即想象自己是造物主,能夠俯瞰并創造一切。這一現在被視為“現代性裝置”的觀念之物,在20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那里,恐怕是透明的、絕對的存在,是作家們自覺追求的結果。
第四,先鋒小說作為余華們的“真實”觀念的形式化,表征的乃是作家承受不住生活擠壓的心靈狀態。易言之,不是先鋒小說對生活進行了變形處理,而是生活將先鋒小說擠壓成變換了現實主義小說形式的形式。
當然,與其說王朔是在理論上意識到了上述問題的存在,不如說是一種作家的直覺讓他努力地表達自己。而通過王朔的表達,20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家“真實”觀的合法性也被懸置起來。借助同時代人的目光,20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的形象也變得立體。王朔在文中又說:“我覺得文學應當有兩種功能,純藝術的功能和流行的功能。”這其實指明了余華式的小說觀的觀念基礎是“純文學”。賀桂梅曾仔細檢討“純文學”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說明了卡西爾《人論》將人理解為符號動物的觀念以及以“現代化”取代“革命”的意識形態對“純文學”觀的根本重要性。②持此觀念的作家難免敵視反映論,并且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關聯的革命經驗表現出格格不入的狀況。因此,盡管1989年就有王朔式的反對意見,“純文學”以其知識譜系和形式形態仍能提供足夠的知識和意識形態信心,讓余華們堅決地表達現代主義式的“真實”觀,并在創作中自覺追求“透視法”帶來的虛構的滿足感。
二
所謂滿足感的問題,其實馬原小說《虛構》中的一句話即足以盡之,就是那句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格言的“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不過,馬原安插在這句話中的深意也許并未被完全打開。至少這句話與小說開頭的題記式的內容有何關系,也許還值得繼續探討。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小說家似乎是怕讀者不夠敏感,又或者是怕自己在小說中要表達的見解太深刻,因而習慣在小說文本中植入題記式的內容。馬原《虛構》的題記式內容,可能是所有先鋒小說家提供的題記式內容中最值得細讀的,試引如下:
各種神祇都同樣地盲目自信,它們惟我獨尊的意識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它們以為惟有自己不同凡響,其實它們彼此極其相似;比如創世傳說,它們各自的方法論如出一轍,這個方法就是重復虛構。
《佛陀法乘外經》③
和馬原慣常的表現一樣,《佛陀法乘外經》也是似真還假的,它并不存在,然而頻繁地出現在馬原的一些小說文本中。這虛構的經書充滿反諷的意味:首先,它的語言是典型的馬原式的小說語言,并沒有模仿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部佛經,這表明它不僅是“外經”,而且是“假經”,虛構的。其次,它強調“各種神祇都同樣地盲目自信,它們唯我獨尊的意識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與“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兩相對照,構成反諷的效果。“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一句本來的自信滿滿的感覺及所引出的后文的自信滿滿的敘述,似乎都可以說是一種“盲目自信”。而盡管是“盲目自信”,“唯我獨尊”,創世傳說卻是流傳下來了。這似乎隱喻著,先鋒小說家馬原的“自信”盡管“盲目”和“唯我獨尊”,但卻建立了小說敘述的基礎和可能。而因為“各種神祇”“各自的方法論如出一轍”,則如此建立的小說敘述的基礎和可能,也許是唯一的;就算是“盲目自信”“唯我獨尊”,也沒有什么辦法。第三,先鋒小說家的敘述行為與“各種神祇”的創世行為在方法論方面是一樣的,都是“重復虛構”。小說的名字就是《虛構》,而“我寫小說”,也就是說,作為先鋒小說家的馬原在“重復虛構”。因此,先鋒小說家馬原創作小說《虛構》的過程,其實就是“創世”的過程。而二者之間,也許在馬原看來的確并無二致,在其他人看來,也許就是不可相提并論的,那么,滑稽的意味就出現了。第四,當作家寫下“虛構”二字作為小說標題時,他也許害怕讀者不明白作者已經發現神祇創世的秘密,或者說文明起源的秘密,于是特別寫上一段題記式的文字,顯露作者神祇式的身段。而一般來說,神祇不是在自我言說中顯現自身,而是在被敘述中顯現出來的。這就意味著,盡管先鋒小說家馬原有意與神祇相比,實際上卻恰好證明了先鋒小說家并不是神祇,反諷的意味在這個層面也出現了。第五,先鋒小說家馬原自信滿滿地認為自己發現了神祇的秘密就是“重復虛構”,其實則只是說出了小說敘述的秘密,對于神祇的言說因而徹底淪為一次小說的敘述行為,并不值得進行神學意義上的對待。事實上,在小說文本中,馬原慣用的手法之一正是“重復虛構”,小說《虛構》也是“重復虛構”。那個已被作為標簽貼在先鋒小說家馬原身上的所謂的“敘事圈套”,正是源于“重復虛構”。把“重復”的部分離析,馬原的“迷宮”自然解體。
而尤為反諷的是,在這樣的“重復虛構”中,馬原建立了他小說的“真實”,或者說,馬原通過“重復虛構”接近了“真實”。這就來到了余華在《虛偽的作品》中所表達的核心內容。盡管馬原對通俗小說的愛好和余華對通俗小說的戲仿是在不同的方向展開的小說敘述行為,兩位作家在如何通過“重復虛構”接近“真實”這一蹊徑上,倒是前后同行的。而且,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批評界樂意關心馬原們背后歐美現代主義甚至后現代主義作家的身影,但也不可否認,這些先鋒小說家仍然是通過自己的寫作實踐抵達歐美前輩開拓出來的一些路向的。這一點余華在《虛偽的作品》中表達得相當充分:
在86年寫完《十八歲出門遠行》之后,我隱約預感到一種全新的寫作態度即將確立。艾薩克辛格在初學寫作之時,他的哥哥這樣教導他:“事實是從來不會陳舊過時的,而看法卻總是會陳舊過時。”當我們拋棄對事實做出結論的企圖,那么已有的經驗就不再牢不可破。我們開始發現自身的膚淺來自于經驗的局限。這時候我們對真實的理解也就更為接近真實了。當我們就事論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時,我們往往只能獲得事件的外貌,而其內在的廣闊含義則昏睡不醒。這種就事論事的寫作態度窒息了作家應有的才華,使我們的世界充滿了房屋、街道這類實在的事物,我們無法明白有關世界的語言和結構。我們的想象力會在一只茶杯面前忍氣吞聲。④
當在1989年6月表達上述意見時,余華是一位成熟的先鋒小說家,已經清楚地知道并且能夠熟練地表達自己的寫作實踐與小說觀念之間的關系。他強調自己是通過寫作實踐來認識小說、發現小說的秘密,這就如同馬原在《虛構》中表現出來的自信一樣,有著切身而來的底氣,是值得批評家重視的。不過,更為重要的問題是馬原、余華前后同行的通過“重復虛構”接近“真實”的蹊徑。當馬原強調“各種神祇”都在“重復虛構”時,內含的是關于世界的不同表述背后有著同樣的結構的意思,故而實際上表達的正是余華試圖明白的“有關世界的語言和結構”。這也就是說,馬原、余華這些先鋒小說家試圖越過“房屋、街道這類實在的事物”,突破“經驗的局限”,找到“有關世界的語言和結構”,“接近真實”。他們相信混沌的事物背后存在“有關世界的語言和結構”,這種解構主義語言學式的對世界的理解,使他們相信通過語言的虛構行為、而不是對事物的再現行為,去“接近真實”。當然,余華的表達要比馬原復雜而纏繞。在馬原那里,一個“虛構”似乎足以包打天下,而余華支使了“事實”“看法”“經驗”“真實”“事件”“事物”“想象力”等一組內涵或交叉、或互滲、或相歧的概念。很顯然,“事實”和“真實”是同義詞,也許都是“truth”的翻譯,而“事件”“事物”是被“看法”和“經驗”掩蓋的“真實”,“想象力”可以接近“真實”,但往往受困于“看法”和“經驗”。因此,所謂“事件”“事物”即意味著已被敘述過的“事實”和“真實”,已經不是其本來面目,要“接近真實”,就必須拋棄對“事件”“事物”的關注。這就是說,必須有新的觀察“事實”“真實”的方法,才能接近“真實”。而“事件”“事物”作為舊有的經驗之物,不能提供新的觀察“事實”“真實”的方法,相對而言,新的觀察“事實”“真實”的方法就顯得是“虛偽”的或“虛構”的。余華在《虛偽的作品》中繼續說:
當我發現以往那種就事論事的寫作態度只能導致表面的真實以后,我就必須去尋找新的表達方式。尋找的結果使我不再忠誠所描繪事物的形態,我開始使用一種虛偽的形式。這種形式背離了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然而卻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實。⑤
值得注意的是“接近了真實”這一表達。如馬原在小說《虛構》的結尾要表達對于剛剛結束的敘述的不信任感一樣,余華在他的所有表達中也從未像現實主義者那樣說自己的寫作抵達了“真實”,而強調接近“真實”。余華的小說《此文獻給少女楊柳》《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煙》《河邊的錯誤》等,都表明作家通過“重復虛構”,試圖接近“真實”,但卻不能提供或抵達“真實”本身。這一點在其他先鋒小說家的小說中也可以反復觀察到,這里不再贅述。
有意思的是,先鋒小說家們的“真實”觀并未引領出一種謙卑,倒是引發了王朔的“同性戀俱樂部”的嘲諷。這里也許隱藏著某種更深的病灶。
三
早在1987年,就有論者表示:
在我國目前文學環境下出現的“純文學”觀念,具體表現為上述的“非理性”論,“純感覺”論和“純語言技巧”論等等。它們見于各種對其它文學觀點的反駁,見于對各種具體作品的批評,也見于直接的理論闡述之中,帶有相當的普遍性。它們各自的具體文學主張雖有異,卻都有一個共同點:力圖從文學中將種種政治的、社會的和歷史的內容和因素統統作為“非文學”因素而排除干凈,只剩下主張者們各自心目中的那唯一的純文學因素留在文學之中。因此,對于文學作品中的所謂“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因素的貶低和排斥,對于文學研究與批評中就作品的社會原因、社會內容、社會意義及社會效果的研究和對作家的社會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的要求的淡漠與反對,就成為它們的共同態度。所以概括地說,“非社會性”便是“純文學”論的根本要求。⑥
認為先鋒小說家對“純文學”的追求即導致“對作家的社會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的要求的淡漠與反對”,肯定是言過其實的。實際上,盡管先鋒小說家每每表示疏離社會政治,在小說中甚至表現一些語言中心主義的特點,但他們不過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來疏離他們所不認同的社會政治罷了,他們有他們所認同的社會良心和責任感。否則,他們在小說中處理血腥、暴力、疾病、情欲和歷史的方式,他們引渡通俗小說或類型小說的敘述技巧到小說中去的匠心,都將是不可理解的。不過,相對于此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而言,先鋒小說的確在現代主義“透視法”的作用之下,顯得光滑而純凈,告別了“種種政治的、社會的和歷史的內容和因素”,使讀者不易了解先鋒小說所反映的具體的社會生活和內容。即以馬原《虛構》而言,讀者從中即很難讀出20世紀80年代中國麻風病的疫情、控制和社會心理方面的內容。相對于馬原所欣賞的毛姆小說《月亮與六便士》對麻風病的描寫,讀者也許不能不認為,馬原只是利用麻風病作為一個驚悚的符號植入小說文本中,以引發讀者的好奇心;對于馬原而言,麻風病完全可以是別的什么,只要能夠令人驚悚并因而好奇即可。同樣地,在格非的《迷舟》和蘇童的《1934年的逃亡》等小說中,重要的也不是小說敘述所涉及的歷史內容,而是小說敘述所呈現的對于歷史敘述的理解。也就是說,正如討論先鋒小說時人們所慣常注意的那樣,對于先鋒小說家而言,重要的不是敘述了什么,而是敘述行為本身。因此,所謂“‘非社會性’便是‘純文學’論的根本要求”,雖然斷語峻急,帶著明顯的批評先鋒小說家的意識形態訓誡,但仍然算得上一語中的,指出了馬原、余華們所“重復虛構”出來的“真實”是多么地與社會現狀相疏離的。
與社會現狀相疏離的結果是多樣的。就馬原而言,他感到的是敘述上花樣翻新的困難和逐漸失去讀者的悲哀。而其他先鋒小說家,大多是臨陣變法,變成了“新歷史小說”或“新寫實小說”的作者,也有的是進入影視行業和大專院校。作為曾經熱烈的擁躉,批評家吳亮1989年即已意識到:
純文學已經沒有什么東西了,許多作家、評論家還硬要等著看小說。在非常好的小說面前,他們自己已經無話可談了。包括我自己也這樣。老調子已經唱完,新調子也唱得差不多了。還是聽聽現實的東西比較舒服。純文學是在非常狹窄的范圍中發展的,它已經從大眾傳播中退出。再也不可能進入大眾傳播的層次。⑦
吳亮唱衰“純文學”的時間離“純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的崛起并沒有幾年,離先鋒小說的蔚然成風更是近在眼前。這也許意味著一種高度提純的“真實”觀,可能并不像余華想象的那樣,既能“自由地接近了真實”,又能喚醒事件“內在的廣闊含義”,反而導致的可能是“盲目自信”的“真實”幻覺,帶來短暫的歡娛。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悲觀。即使是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在守望先鋒,相信“純文學”是不死的。而且,諸如“已經從大眾傳播中退出”“還是聽聽現實的東西比較舒服”之類的說法,也不能算是從“純文學”或先鋒小說內部發展的脈絡得出的觀察,而是一種典型的冷眼旁觀者的所得,因此也不能說是有多么大的說服力的。在一個龐大、復雜的中國當代社會系統中,容量一定比例的“純文學”或先鋒小說的存在,實際上是毫無問題的。即使如王朔所言,成了“同性戀俱樂部”,其實也略無掛礙。那么,所可斷言的并不是“純文學”的死亡或不死,而是余華們的“真實”觀,確乎是在龐雜社會中另辟蹊徑,而他們以為因此“自由地接近了真實”。
而因為得以在龐雜的中國當代社會系統中繁衍生息,先鋒小說家們可能誤以為自己所理解的“真實”即是全部的“真實”或更高級的“真實”——很顯然,在他們的觀念中,“真實”是存在等級的,于是就以“有關世界的語言和結構”的發現者甚至創造者自居,與神祇并列,產生了一點也不謙卑的情緒。雖然在他們的修辭上,他們使用“接近真實”而不是“把握真實”,但在行為上,尤其是小說的敘述行為上,他們表現得像是他們不僅把握了“真實”,而且創造了“真實”。因此,他們沒有多少理由去謙卑。而作為一些關聯性的結果是,讀者發出了“還是聽聽現實的東西比較舒服”的反饋,先鋒小說家們對于中國當代社會的理解和研究也是相對顯得膚淺的。
正如馬原小說《拉薩生活的三種時間》結尾所寫的:
時間整個亂套了。我不說你們也看得出來,我有把條理搞得一團糟的天分。比如我先說去年十月結婚,又說三年半以前我和我老婆剛到拉薩;再比如我說明天早晨看到那個賣銀器的康巴漢子,又說今天從小蚌殼寺回來就已經見過這個人;一言以蔽之:時間全亂了。⑧
不是時間真的全亂了,而是敘述者將整個事件敘述得亂套了,是作者“有把條理搞得一團糟的天分”。先鋒小說家們以獨特的“真實”觀拼合出他們想要的“真實”,就算一切亂套,他們也是樂在其中的。
①史鐵生《“神經內科”》[J],《人民文學》,1989年第 3期。下文凡引用史鐵生《“神經內科”》、余華《我的真實》和王朔《我的小說》時的出處與此相同,不再注明。
②賀桂梅《“純文學”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文學性”問題在1980年代的發生》[J],《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
③馬原《虛構》[J],《收獲》,1986年第 5期。
④⑤余華《虛偽的作品》[J],《上海文論》,1989年第5期。
⑥秦人《“純文學”與文學的社會性》[J],《浙江學刊》,1987年第5期。
⑦趙玫《純文學與一九八八年》[J],《文學自由談》,1989年第2期。
⑧馬原《拉薩生活的三種時間》[J],《解放軍文藝》,1986年第9期。
同濟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