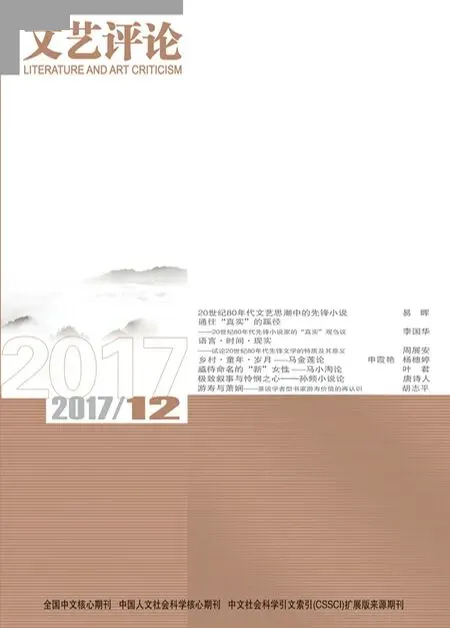文學生態學研究
——基于學術史梳理的討論
○荀利波
文學生態學研究
——基于學術史梳理的討論
○荀利波
生態學自獲得發展以來,似乎就已經因其對生命本身的關注而擔負起了重要而廣泛的使命,以至于它在多個學科領域都成為了被參照、借用、嫁接的思想和理論范式,并催生和拓展了新的研究視域。而一百五十余年的“生態學”發展,不只是對于學術研究,更是對人類自身發展已經產生并還將持續產生更為重要的影響,而生態系統科學甚至被稱為“終極的科學”。隨著人類對自我賴以生存的生態的重視及生態意識的愈發強烈,受啟于生態學的生態批評和生態文藝學理論與方法經過四十余年的探索也逐漸發展成熟,并成為文學批評研究和文藝理論發展的重要向度。文學生態學研究同樣受啟于生態學,并借鑒了埃德加·莫蘭的復雜思維范式,但不同于生態文學批評和文藝生態學的是,它關注的是文學與其所處環境間的關系,這導致了生態學在文學研究中的再次分離,或許這可以成為生態學在文學研究中一個新的生命增長極,并將“人類生態學時代”①在文學領域更推進一步。但整體上,文學生態學研究還是一個較為年輕的領域,并因其在文學生態要素構成上的模糊態度而常常被視為是對文學社會學、文學地理學等學科的克隆,因而,我們有必要在對文學生態學學術史考察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展開進一步討論。
一
生態學最初發軔于人類對自然界中有機體與其生存環境間相互作用的關注,作為學科形態的“生態學”則是1866年由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提出。到20世紀40年代以來,由于全球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導致的自然環境污染,使得生態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并溢過學科邊界,擴展到了人類文明的各個角落。文化擴張和現代性反思等全球性問題接踵而至,催逼了生態學在文學研究領域的理論旅行。這一背景下,1974年,美國學者約瑟夫·W·米克和克洛伯爾相繼在著述中提出文學的生態研究,其中,約瑟夫·W·米克在他的著作《生存的悲劇:文學的生態學研究》中提出“文學的生態學”(Literary ecology)這一術語,使生態學正式被引入到了文學研究領域中。將生態學引入文學研究,類似于列維·斯特勞斯、伊瑟爾將人類學引入文學的文學人類學研究,埃斯卡皮將社會學方法引入文學的文學社會學研究。美國著名生態哲學家羅爾斯頓更是充分肯定了生態學的理論范式意義,他認為:“生態系統科學通常被稱作終極的科學,因為它綜合了各門科學,甚至于藝術和人文學科……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學更深,也是壓倒其他科學的,有著普遍的意義。”②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文學的生態學研究在世界范圍內不斷獲得重視,特別是伴隨著后現代主義、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思想的沖擊,人與自然及其環境的關系問題的關注不斷發酵,在國內外形成了生態批評、生態審美、生態文藝學、文學生態學等多種文藝理論和文學研究實踐的學術領域。就其總體情況而言,文學的生態學研究在兩個向度獲得了發展,一個是生態文學研究,即主要包含生態文學批評和生態文藝學;另一個是文學生態研究,即生態學視域下的文學與文學所處環境間關系的研究。這兩個向度的研究既有理論的建構,也有文學研究實踐。
生態文學研究在國內外因直接因襲了作為自然科學的生態觀,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的過度攫取和破壞而將人與人所生存的環境置于平等位置,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后獲得較快發展,并在文學的生態意識和生態理念的文學審美建構、生態批評方面形成了普遍共識,產生了一大批重要成果。國外的重要著述如弗雷德里克·O·沃格的《教授環境文學》,勒特韋克的《文學中地方的作用》,約翰·埃爾德的《想象地球》,勞倫斯·布伊爾的《重評美國田園作品的意識形態》,徹麗爾·伯吉斯·格羅特菲爾蒂的《走向生態文學批評》,格倫·A·洛夫的《實用生態批評:文學、生物學及環境》等,國內的如魯樞元的《生態批評的空間》《心中的曠野——關于生態與精神的散記》《猞猁言說——關于文學、精神、生態的思考》,曾繁仁的《中西對話中的生態美學》,龍其林的《自然的詩學:中國當代生態文學新論》,華海的《當代生態詩歌》和《生態詩境》,張皓的《中國文藝生態思想研究》,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王學謙的《自然文化與20世紀中國文學》等。
值得一提的是,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曾繁仁的《生態美學導論》、徐恒醉的《生態美學》、袁鼎生的《生態藝術哲學》、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等論著,推進了中國生態文藝理論的構建,在中國生態文藝思想發展中有重要意義。魯樞元不僅與很多生態學者一樣認可21世紀是“生態學時代”,而且針對P·迪維諾的“精神污染”論提出的“地球精神圈”一說,提出了藝術能夠對人的精神進化發揮積極作用以促使人對物欲的超越從而達到緩解人與自然的對立的偉大愿景,這一思想與海德格爾提出的“詩意的棲居”遙相呼應。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一批博士研究生也加入到了生態文學的研究陣營之中,如王明麗的《中國現代文學生態主義敘事中的女性形象》、張曉琴的《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研究》、張守海的《文學的自然之根——生態批評視域中的文學尋根》、張鵬的《大地倫理的詩意呈現——世紀之交的中國生態文學研究》、吳景明的《走向和諧:自然與人的雙重變奏——中國生態文學發展論綱》、王靜的《人與自然:中國當代少數民族作家生態文學創作研究》、吳笛的《人文精神與生態意識——中西詩歌自然意象研究》、王軍寧的《生態視野中的新時期文學研究》、孫悅的《動物小說——人類的綠色凝思》、劉文良的《生態批評的范疇與方法研究》、韓玉潔的《作家生態位與20世紀中國鄉土小說的生態意識》、韋清琦的《走向一種綠色經典:新時期文學的生態學研究》等,直接冠以“生態文學”之名,顯示出其自然生態主義維度的文學批評主張。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新世紀以來以自然環境惡化為主的生態問題愈發凸顯并成為全球性公共問題,自然科學維度的文學生態研究也將隨著文學寫作對生態的自覺關注而不斷獲得新的空間和生命力。
文學生態學相比之下要落寞得多,甚至可以說還處于探索階段。相比于生態文學研究陣營而言,文學生態研究的陣營要年輕得多,而且更多的是一批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在做著這方面的探索,如余曉明2004年的博士論文《文學生態學研究》、郭萬金的博士論文《明詩文學生態研究》、彭玉斌的博士論文《戰火硝煙中的文學生態——〈抗戰文藝〉研究》、王長順的博士論文《生態學視野下的西漢文學研究》、謝鋁菁的碩士論文《碰撞·溝通·融合——新媒體文化與當代文學生態的嬗變》、羅崇宏的碩士論文《網絡傳媒時代的文學生態》、封小萃的碩士論文《中國高校校報副刊的非主流文學生態調查研究》、傅宏遠的碩士論文《1930年代前期青島的文學生態——以國立青島/山東大學為中心(1930-1937)》、陳曉敏的碩士論文《博客:消費文化背景下新的文學生態的整合》、張毓洲的碩士論文《〈南山集〉案與清代前期桐城文學生態研究》等。當然,也有單篇論文涉及到文學生態學研究,如陳玉蘭的《論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文學生態學途徑》、俞兆平和羅偉文的《“文學生態”的概念提出與內涵界定》、張均的《1950—70年代文學制度與文學生態》、蔣寅的《科舉陰影中的明清文學生態》、邢海燕的《文學生態觀與當代土族文學生態研究》、郭萬金的《明代文學生態與帝王的詩歌態度》、佘愛春的《桂林文化城與抗戰時期文學生態》和《抗戰時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學生產》等。文學生態研究是生態學引入文學研究領域的一次再拓展,受啟于生態美學思想中對“生態鏈”相互關系與效應的認識和埃德加·莫蘭“復雜思維范式”影響,所以又并非是對文學文本的自然生態維度的生態審美批評,而是對文學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間關系的研究。
二
較早對文學生態的內涵和研究策略做出系統闡述的是陳玉蘭,她在2004年發表在《文學評論》的長篇論文《論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文學生態學途徑》中,在生態學和文學都是以人為最根本出發點的前提下,以生態學對生命系統和環境系統的關系的研究為參照,提出文學生態學是:“從作為人學的文學的作家生物圈出發,以系統網絡的觀點,全面分析各種生態環境(包括自然的、社會的、文化的)對作家生存狀態、精神心態——合言之,即文學主體生態(包括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的個體生態、群體生態、生態系統)———的決定性影響,進而研究文學主體生態對文學作品本體生態(即作品形態)的作用機理和作用規律,以及文學家的個體生態、群體生態和生態系統與文學產生、存在和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③在理論和方法上對文學社會學、文學心理學、文學地理學等理論和方法有較強包容性和涵蓋性,這并不違背文學生態學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提出。陳玉蘭在對“新批評”一味從文本分析出發、無視創作本源、排斥任何參照系的批評方法的駁斥中提出:“任何作品都不是無父無母的私生子,它是創作主體在具體的生存狀態之下由特定的精神心態醞釀孵化的……來自于特定時代廣大人民群眾向宇宙人生的自然和社會人生的政治、經濟、文化索取的生存需要。”④,只有將文本解讀或主體考察等放入這個系統,才能獲得較科學的結論。陳玉蘭所提出的中國古典詩歌的生態學研究明確了從文本入手,并在對文本創作動因、創作目的、文本內涵等的追問之中,完成對詩歌創作主體生態、接受主體生態的考察,并特別強調由于個體存在借助“互文本性”為中介,對自我做出調適以適應生態系統,從而影響文學群體和流派的形成,因而,文學生態研究在文學群體和流派研究中的意義更為突出。陳玉蘭對文學生態學內涵和研究策略的闡述,在后期的文學生態學研究的理論闡述和批評實踐中影響十分深遠。
彭玉斌在他2006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戰火硝煙中的文學生態——〈抗戰文藝〉研究》中,同樣對文學生態研究方法在抗戰文學研究中的意義做出了充分肯定,他認為借助文學生態學方法還原文學發生的歷史,剖析抗戰文學在其生成過程中于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等多種因素間的多維互動關系,便于擺脫固有的單一文本視角局限。他借用生物生態學中的“生態”內涵對文學生態和文學生態環境作出界定,認為文學生態:“是指文學在一定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以及文化心理環境中的生存和發展狀態。”⑤而文學生態環境“則是指文學生存和發展賴以實現的文學場域內外環境的總稱,它是由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文化心理環境三大要素構成的有機整體。自古以來,任何文學生產都是在一定的文學生態環境中進行的。”⑥由于社會環境和文化心理環境的不可預見性,所以文學生態環境具有更大的不穩定性,是結構復雜、內容豐富的龐大社會系統,因而使得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心理環境等文學生態環境的主要構成要素間又是相互滲透和交織,但在具體環節和具體方面,他們所能發揮作用和施加影響的程度大小、深淺上存在著差異。
俞兆平、羅偉文在2008年撰寫的《“文學生態”的概念提出與內涵界定》中,特別強調文學生態的系統,也就是“相互制衡、衍生循環的‘文學生態鏈’”⑦,主張從生態鏈、生態系統的角度考察文學現象。他們將文學看作一個生態系統,認為文學生態學就是“從相互制衡、衍生循環的‘文學生態鏈’的角度,來考察與判斷文學作品、文學史、文學理論,以及作家生存與創作、讀者接受與批評等的一種理論體系”⑧。他們還特別強調:“如果說時代背景、生存環境是整體的面(背景、環境)與個體的點(作家個體)的關系;那么‘文學生態’所關注,則是如網絡中多個節點與節點之間的循環往復、相互制衡的系統。”⑨應該將文學生態從政治、經濟、文化、人性等方面進行劃分。他們對文學生態鏈和系統的提法較為恰當,并貼合了“生態”的本來特征,但他們所提出的多個節點與多個節點的循環往復、相互制衡將文學生態復雜化的同時,僅僅立于社會結構層提出影響文學的幾個主要因素,卻并未能對如何進入和解讀這個文學的“網”狀生態狀態提出辦法,將文學生態研究的實踐路徑又還原為社會歷史背景解讀。
郭萬金2007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明詩文學生態研究》則以與明詩關系密切的政治經濟、思想學術、社會文化、士民心態、生活觀念等環節為構架,依據史料,以大文學觀、大歷史觀、大文化觀構擬和還原了明詩嬗變的歷史情態。該文雖未從理論上構建明詩的生態結構,但他從外部環境進入對明詩生命存在、精神內涵和文化意義的開掘與詮釋,以詳盡的筆墨繪制了明詩發展的生態圖譜,對文學生態學的理論構建和具體研究都有重要啟示意義。其后,劉毓慶、郭萬金在2008年發表的《科學主義思潮下文學的無奈與訴求——近百年古代文學研究觀念與方法之反思》一文中結合古典文學研究對文學研究中唯物論、進化論、遺產論等科學主義思潮進行了批判,認為文學不是“科學”,也并非單純的“古典文學知識”,科學主義導致了文學研究的“機械形態”,抹殺了“文學鮮活的生命激情”,認為文學是“活的”。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文學的文學生態研究,并闡明了文學生態和文學生態研究的內涵,其中,文學生態是“在認定文學為一種生命現象的前提下,對其所作的環境觀照……是對一種特殊生命的產生及其意義的關切”⑩,而文學生態研究“是將文學當作一種生命體,以一種有機融合的宏觀視角,通過對有可能影響這一生命體生存、變化的諸多因素的考察,還原、構勒文學的原生體,即此以觀察、反思文學的演變軌跡、整體風貌,診釋、開掘深藏其后的生命存在、時代精神、文化底蘊”?。如果說郭萬金2007年完成并被評為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的《明詩文學生態研究》是在明詩研究中對這一路徑所作的探索與研究實踐,那么,反觀之,《科學主義思潮下文學的無奈與訴求——近百年古代文學研究觀念與方法之反思》對文學生態研究的闡述,更像是一次艱難跋涉后的總結,某種程度上,它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王長順在他201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生態學視野下的西漢文學研究》中從生態、生態學、生態環境、文化生態等概念的梳理進入到對文學生態內涵的界定,即“文學生態就是把生物學中‘生態’范疇引入文學研究領域,將文學自身及其所處的外部環境都看作一個生態系統,從而探究文學在產生、發展、嬗變過程中其內部諸要素(本體與主體、理論與實踐)與外部環境(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等相互影響、相互制約關系的規律,并進一步認識各種環境如何對文學產生積極影響和負面制約”?,他認為文學與文學所處的外界環境間進行符號交換的同時,也與其所處環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意識形態等之間發生著關系,而這種關系會對文學發展產生積極的或負面的影響。王長順基于內涵的梳理,對文學生態的構成做了整理,并進而在否定文學的社會環境研究與文學的社會背景研究相同、文學的生態鏈研究偏重于文學本體研究、文學的生態圈研究接近于文學生態環境研究后,認為文學生態研究應關注對文學的政治生態、文化生態、意識形態生態研究。綜合陳玉蘭、彭玉斌、俞兆平、羅偉文等人的觀點來看,這一思路有值得商榷之處。文學并非能夠包打天下,但究竟從什么樣的角度切入,能夠較好地反映文學自身發展的獨特狀態,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影響并不能孤立地獨自存在,也不能孤立地在文本中顯現,相反的是,任何一種文本都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文學生態學是文學研究中對生態學思維,甚至是理論、方法的習得和借鑒,文學的生態鏈、生態圈的構想在某種程度上筆者恰恰認為有其合理之處。
還有一些其他成果中也或多或少對文學生態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做過討論,具體篇目前文有所提及,此處不再贅述。但正如俞兆平、羅偉文2008年在《“文學生態”的概念提出與內涵界定》一文中所指出的,目前的文學生態研究產生了一種明顯趨勢,即“把‘文學生態’理解為時代背景、時代氛圍、歷史語境,或作家的生存環境”?,這樣不僅導致概念的重疊,而且將文學生態復歸為文學的社會歷史文化細節研究,而尚未完成文學生態體系的構建。與這些理論上的檢討幾乎同步在進行著的研究實踐中,也顯示出了這一理論構建中的跋涉路徑,彭玉斌的《戰火硝煙中的文學生態——〈抗戰文藝〉研究》、王長順的《生態學視野下的西漢文學研究》等成果似乎已經意識到了文學生態內部研究會導致的局限,甚至是陷入社會歷史文化研究的窠臼,所以他們在研究中將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都糅合進研究整體構架中。但值得一提的是,余曉明2011年出版的《文學研究的生態學隱喻:文學與宗教、政治、意識形態及其他》與俞兆平、羅偉文觀點有一定承續性,該著對文學生態學理論的闡述中承繼生態學的系統性和文學作為一個“類生命”個體的觀念,延展了對文學的有機性、關系性和整體性認識,借鑒和吸收了埃德加·莫蘭的“復雜思維范式”思想,認為文學生態學是文學的生態學隱喻,是“用生態學的方法來觀察、研究和解釋文學以及文學與‘文學的環境’之間的關系”?,不應該只是傳統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簡單整合,因為內部研究會導致研究實踐偏向于形式化,外部研究則會產生決定論傾向而導致將文學歸結為政治、經濟等某個外部因素的變化。為此,余曉明提出文學生態學研究應該像生態學所強調有機體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與滲透那樣,將文學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貫通起來,使文學研究構成有機的整體。基于這一構想,余曉明闡述了文學與宗教、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法律、地緣的回環或錯綜復雜的網狀關系。可以說,《文學研究的生態學隱喻:文學與宗教、政治、意識形態及其他》是一次真正意義上對文學生態學理論和方法的系統性建構與闡釋,但必須指出的是,作為理論的建構與闡釋,作者期待的是產生普適性的理論范式意義,某種程度上反而導致了它在一定程度上的復雜化。
綜而言之,文學生態學作為對文學與文學所處環境間的關系的研究,并且在這個關系網絡中,將文學看作一個生命個體,這已經成為十余年來文學生態學在理論和研究實踐中不斷闡述和建構的基點。但正如前文所說,文學生態學研究剛剛起步,作為一種文學研究新的理論視野,雖已經在一批青年研究群體中引起了共識,并對拓展文學研究空間產生了重要意義。但是,文學生態學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建構,仍然還亟待新的拓展,例如,文學生態學研究在涵蓋文學社會學、文學地理學及文學的社會歷史批評等理論與方法的同時,如何更鮮明地顯現自身在文學研究中的新的開掘;文學生態學在理論話語的體系建構上,如何形成較為一致的話語表述形式;文學生態學研究方法上,如何搭建一個更具備實踐操作可能的方法體系等。在筆者看來,其中一個尤為急迫的問題是文學生態從自然、社會到文學自身的諸多構成因素,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結構呈現出來,各自在這一結構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如何形成相互間的關聯和作用,這成為制約文學生態學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這或許也是文學生態學研究確立自身與其他學科領域相區別、使文學生態學之所以為文學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內容。
三
就文學生態學學術發展整體情況來看,文學生態學研究的核心思想在于將文學看作一個生命體,對文學與文學所處的環境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成為了學術界對文學生態研究的基本共識。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方式,這個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它和周圍外部自然界的不斷新陳代謝。”而這種新陳代謝的發生,就在于它所處的環境與它所發生的關系,從而導致對它產生作用、帶來影響。那么,構成文學生態環境的要素是什么?這種文學生態的環境又該以何種方式呈現,才能使其與文學社會學、文學地理學等的研究有所區別并顯現出自身作為一種新的學科和研究領域所具有的獨特性?這仍然是文學生態學亟待解決的基本問題。
余曉明在《文學研究的生態學隱喻:文學與宗教、政治、意識形態及其他》中為了形象地區分文學生態學與幾個相關領域的差異,曾做過這樣一個圖式:
生態學:有機體——環境關系
深層生態學:人(主體)——自然環境關系
生態美學:人(主體)——自然+社會環境審美關系
生態批評:人(主體)——自然環境主體關系
文學生態學:文學——文學環境的隱喻關系?
也就是說,在文學生態學中,所研究的是文學與文學環境間的隱喻關系。他在這里并未使用生態學、生態批評等中所使用的自然環境,顯然在他看來,文學環境并不同于自然環境,而是一種“精神圈”,這一提法也與魯樞元1996年發表的《文學藝術與生態學時代——兼談“地球精神圈”》中的“地球精神圈”一說有一定承續。而余曉明在具體闡述文學與其生態環境的關系時,主要選取的對象是宗教、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法律、地緣,某種程度上也表明了他對構成文學生態的文學的環境因素的基本限定。與他相類似的還有郭萬金、王長順等人,他們也基本從相同或相近的領域確定構成文學生態的文學的環境構成要素。但陳玉蘭、彭玉斌則與他們有一定差異,他們主要把自然、社會、文化三大范疇作為文學生態的環境構成。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宗教、教育、法律、意識形態等,固然都與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就文學生態環境構成來講,我們忽略了他們之間的涵蓋與被涵蓋關系,將文學生態環境過于復雜化。例如,就社會來講,它的構成因素本身就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內容。政治、經濟、文化是構成社會整體的因素,也是作為整體的社會局部的顯現,是涵蓋與被涵蓋的邏輯關系。所以,就紛繁蕪雜的人類生存的環境來看,我們并不能把它放在一個平臺之中,忽略整體與個體、個體與個體間的關系,而要綜合地從相互間的組合與連接,來構建作為文學所身處的文學生態環境,并將其以系統的結構呈現出來,這或許也是文學生態學研究的一個主要任務。
文學生態學研究發展至今,雖然多有人提到文學生態系統,但大多只是零散的構成要素的列舉,并未注重對生態系統結構的探討和呈現。生態學認為:“生態系統(ecosystem)就是在一定空間中共同棲居著的所有生物(即生物群落)與其環境之間由于不斷地進行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過程而形成的統一整體。”?而生態系統生態學又進一步強調:“結構是生態系統內各要素相互聯系、作用的方式,是系統的基礎。”?而事實上,作為生態學啟示下的文學研究,我們要確立該研究的學科獨立屬性,就必須建立文學生態的系統結構。陳玉蘭、俞兆平、羅偉文等人的論述中也提到文學的“生態系統”,其中,陳玉蘭將文學生態系統看作是以文學活動為中心、圍繞創作主體、作品本體、接受主體這些互相關聯的因素作用所形成的一個整體,將文學的生態學研究回歸到了文學本身,這也是本文考察文學生態的一個重要視角;余曉明對文學與其環境間回環與錯綜的關系從結構性隱喻的角度做了復雜的闡述,并繪制了以一種概念結構構建另一種結構概念的結構隱喻圖式。他雖然十分強調文學與宗教、政治、經濟、社會的回環與錯綜關系,但忽視它們之間存在的涵蓋與被涵蓋關系,在強調社會因素相互間的復雜關系,并將文學置于與政治、宗教、經濟等的同一結構平面的同時,卻淡化了文學在文學的生態環境中的主體性位置。
文學生態系統是文學與其所處的生態環境構成的結構整體,主要包含了人類生存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中處于不同層級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的生態要素。不僅包含“精神圈”,也包含物質的自然環境。“精神圈”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總和,也就是綜合地顯現和構成了與自然環境相對的人類社會。在文學生態學研究中,自然、社會并不直接地對文學生成作用和影響,所以,在文學生態系統結構中,我們同樣面臨對構成這個整體的各個部分要素的擇選。生態學在文學中之所以走向歧路,對于要素選擇的差異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生態文學批評和生態文藝學將自然作為其批判的旨歸,強調文學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揭露、批判與反思;而文學生態學則側重強調文學作為社會關系的產物,突出對文學與其所處環境間關系的研究,導致了生態學在文學研究中走向兩個不同發展向度。自然環境與社會不是矛盾的兩極,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在文學生態研究中,自然環境并非與文學生態沒有關系,而是作為文學的地理空間的規定性存在,這一點與文學地理學相似。空間的轉移,必然導致文學生態的變化和新的文學生態的形成。
文學的自然環境生態和文學的社會生態,是文學在時空上加以區分的重要參考依據,例如中世紀歐洲文學、古希臘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等的命名和范疇的界定,其中就依賴了文學的自然環境生態和文學的社會生態要素。在某種程度上,文學的自然環境生態和文學的社會生態成為了對文學自身整體形態的規定與描述,因而,我們把它看作是文學生態系統中的整體層。整體作為部分要素的綜合,文學也只是這個整體中微小的一個部分。作為文學生態的整體層,也只是一個相對的而并非固定不變的時間與空間范圍,它因我們所研究和考察的對象決定我們所要考察的與文學相關的自然與社會范圍的大小、疏密。可以說,作為“關系的總和”的社會,包羅萬象,是多個領域構成的整體,而這些領域之中又包含多重要素,顯現為不同的層級,具體體現為縱向垂直的包含關系和橫向并列的平行關系。在自然與社會的整體層之下,政治、經濟、文化等是社會的基礎領域,既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是對社會獨特特征的顯現。它們直接或間接的、或多或少的與文學間發生聯系,相互間發生作用、產生影響。因而,政治、經濟、文化等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構成了文學生態的社會層,顯現為文學所身處的特定時代特征,同時,它們相互間又構成平行并列的關系,相互影響和作用。在文學生態的社會層中,文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文學、音樂、繪畫、舞臺表演等共同成為文化的構成要素,它們有自身獨特的范圍、顯現方式和社會功能,因而,文學、音樂、繪畫、舞臺表演等共同又構成了文化垂直層。同時,音樂、繪畫、表演等是與文學處于同一層級的平行并列關系,相互影響和作用。文學作為文學生態學研究的主體對象,雖然在整個系統中,它只是龐大的系統中一個環節,但它自身同樣有著復雜的結構。就當下較為普遍的觀點而言,我們通常還將文學按照文體來進行區分,不同的文體在不同時代、不同空間范圍,也會因受它的生態環境的影響,或生態環境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因而,文學的垂直層級還應該包含了不同的文體,如小說、詩歌、報告文學、戲劇等,它們共同構成了文學生態的主體層,相互間形成平行關系相互作用和影響。
文學的生態環境并非一個模糊、不可知的對象,而是實實在在的人類社會的多種要素的組合,我們不應該回避這樣的事實,而在文學生態研究中將文學的生態環境當作歷史文化背景的雜糅,更不能機械照搬文學生態系統的結構對文學現象作生硬的解讀。由于文學與文學所處的環境間的關系在整個系統中存在垂直和平行的關系,所以,文學與文學所處環境間關系的發生既會在不同層級中發生垂直的關系,也會在平行的結構中形成相互的影響;處在生態系統中的要素并不會均衡的作用于文學,它會因整體生態的發展狀態而在一定的層面發生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一些要素在有的時期會占據主要位置,而在另一時期則有可能是別的要素占據主要位置等。特別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中,這種關系體現得尤為明顯,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我們將文學看作一個生命個體它本身的復雜性,但也給我們進行文學生態研究帶來很大的困擾。一方面,從外部進入,對文學所處的整體環境及其自身在這一環境中的狀態作出描述,這顯然是可以的,甚至也是必要的,便于我們形成一個對文學及其存在狀態的整體感。但是在另一方面,就文學與文學所處的生態環境間的關系研究來說,從外部進入顯然困難重重,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的主要領域,以及音樂、繪畫、表演藝術等文學的平行結構層,都或多或少與文學發生著一定的關系,但又不是單一的關系,從任何角度進入,都必然導致對文學自身與其生態環境間的割裂。
陳玉蘭在《論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文學生態學途徑》一文中指出:文學生態學的核心是要把文學的存在方式看成一個生態系統,而這個生態系統“是以文學活動為中心,讓創作主體、作品本體、接受主體這些互相關聯的因素,按邏輯序列做出動態組合的一個整體”?,也就是說,文學是處在一定生態系統中的文學活動的結果的顯現,而這個結果其實具體就體現在了創作主體、作品本體和接受主體上,而陳玉蘭在文中也從創作主體、作品本體、接受主體等角度作了文學生態的具體分析。這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示,創作主體、作品本體、傳播載體、接受主體是文學活動的四要素,文學是這些要素的總和。也就是說,作為整體的文學生態系統是文學獨特性生成和顯現的重要前提,但只有通過對文學為主體,以文學創作主體、接受主體、作品本體、流派等的文學生態考察,才能使文學生態系統得以完整呈現。
結語
事實上,文學生態學更應當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帶著生命的溫度,而并非解構或是建構對象的技術。在對文學生態的具體研究中,不能將文學對象套入文學生態系統做機械的批判,而是應該將文學放置和還原到它所處的生態系統中,分析文學之所以呈現這一狀態的文學生態。文學是創作主體、作品本體及文學的傳播與接受在文學活動中的總和,同時,構成文學這個總和的創作主體、作品本體及文學的傳播與接受這些部分之間又相互連接,他們既可以獨立地成為我們探尋這一時期文學活動中的文學生態的重要路徑,也可以整體地構擬作為文學活動的整體生態。作為文學的生態系統,是在自然與社會的整體生態環境中對與文學活動緊密相關的要素的選擇下進行的建構,也就是說,文學生態系統的構成本身只是與文學的發生、發展相關的要素的集合體,是以多種要素構成的“生態圈”結構上的系統,并非如“食物鏈”般的存在。文學必然是存在于一定的生態環境之中,并將其與這一生態環境間的獨特關系在文學活動中顯現出來,因此,以創作主體、作品本體及文學的傳播與接受等文學活動的主要內容為切入口進行的文學生態研究,既要注重外部環境的整體描述,同時也要抓住對呈現文學生態最為關鍵的文學生態系統要素,才能在復雜系統中顯現文學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本真生存狀態。
①[美]E·拉茲洛《即將來臨的人類生態學時代》[J],《國外社會科學》,1985年第10期,第41頁。
②[美]霍爾姆斯·羅爾斯頓《哲學走向荒野》[M],劉耳、葉平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頁。
③④?陳玉蘭《論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文學生態學途徑》[J],《文學評論》,2004年第5期,第 116頁,第 117頁,第116頁。
⑤⑥彭玉斌《戰火硝煙中的文學生態——〈抗戰文藝〉研究》[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6年版,第 4~5 頁,第 4~5 頁。
⑦⑧⑨?俞兆平、羅偉文《“文學生態”的概念提出與內涵界定》[J],《南方文壇》,2008年第3期,第50頁,第51頁,第51頁,第50頁。
⑩?劉毓慶、郭萬金《科學主義思潮下文學的無奈與訴求——近百年古代文學研究觀念與方法之反思》[J],《中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 2期,第 10頁,第13頁。
?王長順《生態學視野下的西漢文學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第9頁。
??余曉明《文學研究的生態學隱喻:文學與宗教、政治、意識形態及其他》[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 4頁,第 22~26頁。
?李博等主編《生態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頁。
?蔡曉明《生態系統生態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頁。
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滇黔桂雜居少數民族文化適應研究”(項目編號:13XMZ064);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團隊科研項目“西南大后方詩歌文學生態研究”成果]
曲靖師范學院人文學院;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