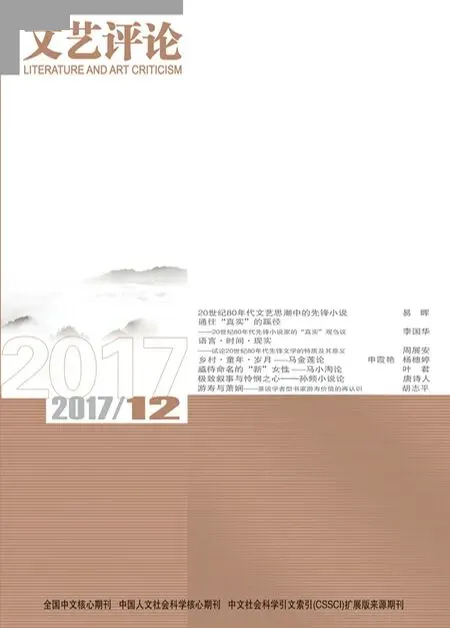在現實與想象中糾葛:賈平凹《極花》的敘事藝術
○程 華
在現實與想象中糾葛:賈平凹《極花》的敘事藝術
○程 華
秘魯偉大的作家加爾克斯·略薩認為,任何虛構文學都是“由想象力和手工藝技術在某些事實、人物和環境的基礎上樹立起來的建筑物”①。這么說來,當作家對某一現實生活中的素材發生興趣,并要依此素材完成一件虛構性的文學作品時,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發揮想象力,使這件緊貼現實的素材飛起來,使想象和現實融合。賈平凹近幾年關于農村題材的作品都是指涉現實的,他也總能借助文學手法,在現實和想象之間進行很好的調度,這部《極花》也不例外。原始素材是作者十年前聽到的真人真事,對類似社會新聞事件的想象和編織需要高超的技巧,《極花》不論是敘事視角的選擇,還是超越現實的敘事,以及作品中的象征和隱喻等暗示手法的使用,都有想象力參與其中,作者借助這一系列敘事手法,企圖完成對真實事件的超越,同時在想象的背后,注入作者對人生內容和社會歷史的思考。
一、限知敘事視角及其現實指涉
小說一開始即透過女主人公胡蝶的視角描繪出這樣一幅畫面:金鎖因為媳婦被蜂蟄死而瘋了,順子爹因為兒媳婦被外地人拐跑而自殺,這兩件事的背后就可看出這個近乎封閉的圪梁村里彌漫著非同一般的空氣,男人們對女人的非正常死亡或離去的恐懼。在賈平凹看來,“原來是經濟可能把一個村子毀掉,現在是從性上徹底毀掉,從人種上徹底把村子毀掉,這是從根子上把人毀了”②。這是現實農村生活的實景呈現。農村的消亡一部分是因為撤村并鄉城鎮一體化的發展,另一部分是在那些貧窮偏僻的鄉村,因為種種原因未在城里謀生的男人逐漸淪落為光棍而在人們的視野里消亡。賈平凹是從人種難以繁殖為繼的層面,關注光棍村,也從這里打開缺口,引入被拐賣婦女胡蝶的故事。當農村的女人們不愿回到出生地,呆在村子里的光棍會以擄掠的方式,維系自身及村子的生存與延續,這是真實的事件。這真實的事件背后似乎有這樣的聲音:這種野蠻擄掠的暴力行為,是傳統農村在現代化背景下掙扎與反抗的一種方式。賈平凹用文學的方式,將城市與農村并置在這個時代面前,也并置于讀者面前。
胡蝶,因其波折的經歷,被賈平凹賦予極豐富的想象。同時,也在敘事層面具有其他人物不可替代的作用。胡蝶作為千萬離鄉者的一員,見證了城市化不可摧毀的力量;胡蝶又以非正常的方式被暴力挾裹到農村,充當生殖繁衍的工具;在這個大時代下,胡蝶這個形象就成了農村最后走向滅絕的見證者;在文學的想象中,胡蝶也成為聯系城市和農村兩種文化力量的關鍵人物。在小說中,圪梁村是胡蝶被拐賣進的村子,如果把圪梁村看作是中國最后一個農村,那么這個村子里的文化生態是值得關注的,小說通過猴子、黑亮等人說明農村找不到女人,是因為城市將農村的女人都卷走了。這也說明,作者其實欲將胡蝶作為農耕文明和城市文化在最后較量中的見證者,從而思考城鄉發展何去何從。作為見證者的胡蝶,就是敘事的關鍵元素。如何敘事,才能提供如親歷般的真實經驗,作者選取了以胡蝶作為第一人稱限知敘事視角。賈平凹在和韓魯華的訪談中談到:
寫《極花》的時候,也想用個第三人稱來寫,第三人稱的好處就在于它可以鋪開來寫,但是寫著寫著就覺得畢竟拐賣如果把它鋪開來寫,它就是一個單純的故事,這個故事不可能涉及到更多更多面,這個故事不可能涉及到我剛才說的整個農村的這種情況。那就說是換一個第一人稱,就只能把它篇幅寫小,它這個故事情節簡單,主要是心理的東西,心理的東西在寫的時候,就寫短一點,就以她這個眼光,看她在村子里看到的一些情況,就這樣寫。所以這一切都要看你想寫啥,再者題材就把你決定了。③
小說以胡蝶的視角敘寫其在圪梁村經歷的事實。胡蝶作為被拐賣婦女在圪梁村經歷的慘痛經歷無疑是獸性對人性的摧殘,作者突出了群體勢力對胡蝶個人身體的戕害。小說中兩次寫胡蝶身體遭暴力侮辱:一次是胡蝶企圖逃出窯洞,被村里的光棍們凌辱,在胡蝶的眼里,他們已經變成了一群狼;一次敘寫黑亮在全村人的幫兇下,凌辱和占有了胡蝶。胡蝶作為黑亮買來的媳婦,在小說中是在群體力量的幫助下,完成了生殖和繁衍的行為,突出群體的獸性和殘暴。在農村和城市的對抗中,這種群體參與的嗜血的暴力暗含農村的衰微。
賈平凹絕不僅僅只是在敘說對女性凌辱的暴力行為,暴力的背后是城鄉文化的較量,包含有在較量中呈現出的復雜的文化和心理因素。胡蝶被拐賣和禁閉后,自身所遭到的慘痛的事實,主要是以圪梁村光棍們的行為呈現出來。作者運用暗示和隱喻的手法,突出了男人們的內心焦慮。小說中出現的血蔥,可以激發生殖的力量;黑亮父親雕刻的石女人,也是村民對女人的臆想,這都“暗示了性苦悶在農村的普泛性、焦慮感”④,村民們集體對胡蝶的暴力性侵犯,也未嘗不是男性欲望無法實現的一種報復性心理。作者透過女性視角,正視圪梁村的男人們的現實問題,將城市與農村的對立與沖突表現出來,農村的野蠻性存在,未必沒有城市文明的壓迫與侵犯,圪梁村光棍們的現實生存是通過正常的渠道找不到媳婦,因而也就會有胡蝶們被拐賣、被凌辱以及被禁錮的事實。賈平凹從兩性層面,凸顯村莊的滅絕,這是一種關乎人性、關乎歷史也關乎文化的獨特而深刻的視角。經濟貧窮,文化落后,導致女人們離鄉出走;為了避免村子的滅絕,就會產生滅絕人性的交易和野蠻獸性的行為;人性的野蠻和道德的淪喪是城市文明的壓抑,這是惡性循環的結果,這也是賈平凹所關注的落后農村的現實存在。
二、民間文化資源與小說的超越性想象
如何敘事才能使作品既指涉現實,又具有超越現實的力量,這是對作者虛構能力的考驗。如若只是純粹敘寫胡蝶在圪梁村的真實經歷,作品因為貼近現實無法承載更多的思考。賈平凹之前的作品,多用非正常人的視角達到一種超越現實的敘事和想象,比如《秦腔》中瘋子引生的視角,《古爐》中的兒童視角,《老生》中能穿越生死的唱師的視角,非正常人視角的運用,突破了現實的拘囿,可以承載更多想象的空間。在《極花》中,胡蝶是一個受過高中文化教育的正常人,胡蝶眼中的事實,比較近于生活真實,胡蝶作為第一人稱限知視角還是很難發揮出更多超越現實的想象內容。
一個作家的文學想象,總是受制于其思想認識和對文學的看法。莫言作品中充滿奇幻的歷史傳奇,源于具有奇幻文學源頭的齊文化背景,動蕩的民間歷史和傳奇故事能激發莫言的創作欲望。賈平凹的文學接受與傳統文化淵源頗深,其對民間道德和傳統文化思考較為深入,傳統和民間文化資源能給賈平凹提供更多的文學想象。比如《極花》中關于“分星分野”的插入,和《老生》中《山海經》內容的大段插入有異曲同工之妙。再往前追溯,《秦腔》里的秦腔片段的插入,《古爐》里善人說病文字的插入,這些素材多源自民間,恰說明賈平凹的文學創作特征。在現實的敘事中加入奇幻的想象,和將現實敘事納入到悠遠的歷史和深廣的民間中一樣,都是文學的超越性想象。賈平凹的小說多取材現實,如若從現實素材講故事,容易使人對號入座,故事很難超越現實,這種具有民族歷史特點或是具有民間文化含義的意象,充當小說敘事內容,與故事緊密聯系,與人物和情節自然粘合,不僅使當前故事具有悠遠的民間與歷史意蘊,也是一種超越性的想象,給作品增添迷離神秘的意味。
老老爺關于“分星分野”的論述,出現在胡蝶被禁閉在窯洞里六個月后,順子爹死后,全村人都去吊唁,胡蝶被禁閉在窯洞,與窗外的老老爺對談,老老爺說:“天上的星空劃分為分星,地下的區域劃分為分野,天上地下對應著,合稱星野。”⑤“分星分野”的論述在作品里是很自然的鍥入。胡蝶被蒙著眼帶入圪梁村,在現實中,其對自己處所的認知是蒙昧的。引入“星野”的說法,時間上可回溯,空間上可定位,還與中國遠古的民間有了聯系,這樣的藝術設置和安排,就拉長了作品事件背后的歷史空間和隱喻空間,就像《老生》中的《山海經》一樣,具有歷史淵源的文化意象的插入,“如同站在歷史的高處俯瞰歷史”⑥,賈平凹通過藝術構思,讓其作品具有豐富的表現和闡釋空間。
在胡蝶的視野下,老老爺的思維和城市文明的思維相對立,是一種反現代的思維觀念,比如:
瞎子看天,拴牢說:“他看天?他能看見天?”老老爺說:“天可看他么。”……我往好豆子里撿壞豆子,老老爺說,你往出撿好豆子么……黑亮買來瓷碗,劉全喜喊叫讓我挑碗,老老爺說,不是人挑碗,是碗要挑選人。⑦
老老爺代表的思維觀念不是從人的維度看天地與自然,在他那里,是天地神人共同存在于一個世界之中。老老爺說:“地下一個人,天上一顆星。”⑧天地人間,萬物有靈,人的精神世界在現代社會尤其需要神的照護。在胡蝶受到屈辱、魂魄不能安位時,神的力量就顯現出來。小說中,老老爺讓黑亮他爹找麻子嬸為胡蝶招魂,招魂的方式是將用紙剪成的小紅人貼在房間各處,剪紙原本是祭祀鬼神的方式,是一種與神對話的方式,最后使胡蝶神情安然。老老爺說:“戲是要給神唱的,安頓下神了,神會保佑咱村子的。”⑨對神的敬祈,使老老爺的形象更像是民間的巫者。氏族時代,巫師是與神鬼溝通的法師,巫的作用如同君王,“巫君合一”是氏族文化時期的巫史傳統。⑩賈平凹之前的作品中也出現過類似能與神靈溝通的巫者,但其旨在營造神秘的氛圍。自《古爐》中的善人,《老生》中的唱師,以及《帶燈》中自始至終的寺廟線索,再到《極花》中的老老爺,賈平凹的興趣已經不是在作品中營造巫的氛圍,而是在思考民間宗教對醫治現代人心的作用。老老爺身上的天地神人一體的整體思維觀念更為賈平凹所看重,其將天地人納入到大自然中,有生態反思的意識,還有更為素樸的民間宗教意識。
作為民間巫者的老老爺,同時也是鄉村的智者,其智慧的背后有民間道德和傳統文化的支撐。他“按照仁、智、德、義、信、孝、理等給村人起名”“每年還用毛筆撰寫筆畫異常繁多的古漢字送給村人,寓意各種吉祥幸福。每年二月二,老老爺把用五彩的細線編成的彩花繩兒,一一拴在全村人的手上,寓意平安興旺”?。老老爺就如同李澤厚先生所說的巫史,起著溝通天人、凝聚人心、保持秩序的作用,他是圪梁村里的精神治愈師。
胡蝶經過暴力蹂躪后的精神歸位正是受到老老爺的影響而發生變化的。胡蝶懷孕后,在圪梁村的上空找到了屬于她和孩子一大一小的兩顆星,也就在找到自己歸屬的星之后,胡蝶的生活中有了光:
我看著我的身子,在窗紙的朦朧里是那樣的潔白,像是在發光,這光也映著黑亮有了光亮,我看見了窯壁上的板架,板架上的罐在發光,方桌在發光,麻袋和甕都在發光,而窯后角的凳子上爬著了一只老鼠,老鼠也在發光。?
老老爺連同他的民間智慧和鄉土文化,作為想象性的存在,成為賈平凹用以對抗城市對農村的壓迫的一種方式。老老爺作為超越現實的想象,也給我們更多的思考,在科技現代化的今天,在人類的生殖繁衍都成為危機的現代,人應該獲得怎樣更好的存在?是在利益的世界里蠅營狗茍,還是獲得精神的棲居?在物質和精神的天平中,是物質更為強大,還是精神更為重要,現代人需要為人性注入什么力量?老老爺身上所具有的天地神人整體思維觀念值得我們思考。
三、結構的象征和詞語的隱喻
胡蝶作為《極花》的絕對主角是毋庸置疑的。她是小說的敘事者,又是悲劇命運的經歷者。加諸她身上的慘痛經歷一方面以實景描繪的方式呈現出農村無以為繼的現實;而她在圪梁村的所見所感,作者以想象參與其中的敘事方式又使她有了遙望星空的夢想。被拐賣的胡蝶到底該何去何從,無論如何,賈平凹也要給胡蝶一個選擇。
賈平凹在小說中寫到胡蝶做了一個夢。夢,在賈平凹以往的作品中是很少涉及的,特別是將夢作為結構性的支撐元素,在《極花》中還是第一次。要通過敘事因素完成作者對現實的認識,可以有很多技巧,比如之前說到的敘事者的設置,超越性想象,但以主人公做夢方式進行敘事是比較直接地表現作者對故事的思考。
夢在小說的結尾出現,主人公胡蝶夢見被家人從被拐賣地解救回來,但不堪忍受在城中村的生活,又回到被拐賣地。這和賈氏聽到的現實故事如出一轍。在《極花》的后記中,賈平凹敘述了小說的素材來源,作者十年前聽到老鄉的女兒被拐賣后,家人歷經千辛萬苦將女兒從被拐地接回,沒想到女兒又回到被拐地。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事件為什么會在作品中以夢境的方式處理?這就體現出作者的敘事技巧,是講述真實的被拐賣婦女的故事,還是借助這個故事,講述超越故事本身的作者對故事和生活的思考?如果對夢這個敘事形式進行分析,“夢”的形式,就是文學敘事的手法和技巧,作者想要借助夢這種潛意識的心理呈現,完成他對胡蝶命運的設定,表達他對整個作品所要呈現的主題思想的思考。
如果對夢中內容進行分析,那么,這就涉及到一個非常關鍵的詞匯——“回去”,“回去”是關涉到胡蝶命運的重要的關鍵詞,對“回去”的想象和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人物的思考,也是對主題的探索,是賈平凹處理、想象以及借用這個素材進行文學創作最重要的一個詞語。對于主人公而言,如若回到父母家,這是大部分讀者的共同愿望,那么社會正義得以伸張,但這就成為一個純粹的社會事件。對回去的處理,賈平凹沒有如常理所見,而是想象胡蝶回到了被拐地——圪梁村。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原始素材的主人公回到封閉野蠻的地方?這是作者審慎思考的,而他的小說,其實就是要通過胡蝶被拐賣的事實,揭示這背后的原因,同時,也是站在更開闊的地方,對農村與城市做進一步的文化觀照。
賈平凹說,“《極花》中寫那個叫胡蝶的女人,何嘗不是寫我自己的恐懼和無奈呢?”?賈平凹多年以來的創作,始終未曾離開過農村,也始終對老百姓的生存充滿憂患。在《秦腔》中,他通過秦腔衰微影射了傳統農耕文化的沒落,也觸碰到農村的現實,農村的年輕人逐漸遠離農村,土地荒蕪,農村逐漸成為空心村。賈平凹在寫完《高興》后,面對記者采訪時,他幾次說明,城市終歸不是農民的家,農民的根據地依然在農村,農村要發展壯大,還需要農民自己的力量,所以在作品里,五福死后,劉高興背尸還鄉,不僅僅是草民戀土、魂歸故土的說法,而是從那時起,賈平凹就通過小說情節,表達他對農村現狀的思考以及農民命運的探索。寫完《高興》的十年之后,面對他熟悉的農村現狀,在農村城鎮化的必然趨勢下,通過胡蝶的經歷,宣示作者這十多年的思考。圪梁村,或許是最后一批農村,將面臨著族戶的絕種而無以為繼,這種絕種比經濟的貧窮更可怕。
城市文明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是社會現代化和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人們的觀念逐漸趨于“利”而舍去“義”,導致了現代性的野蠻。“現代性的野蠻是從人類為自己謀利這個角度來講的。現代性所有的義,是用利來解釋的,義是相對的,利是絕對的,是最高原則,資本主義是有史以來最激烈的社會思潮,它摧毀過去的一切,使世界荒原化和簡單化。”?以利為本的工具理性與美好的人性、人情愈來愈遠,人的素樸的道德情感被人的私利欲望控制,這也是近代以來人類道德的墮落、社會的邪惡和苦難的根源。在《極花》中,胡蝶敘寫夢中被母親解救回來,面對城市小報記者和周圍人的異樣眼光,作者寫道:“我覺得他們在扒我的衣服,把我扒得精光而讓我羞辱。”?比起圪梁村的農民們用暴力摧殘身體,精神上的侮辱更為痛苦而難以彌合,賈平凹在《后記》中也談到,“這些失蹤的婦女兒童,讓人想的最多的,他們是被拐賣的。這些廣告在農村很少見,為什么都集中發生在城市呢?偷搶金錢可以理解,偷搶財物可以理解,怎么就有拐賣婦女兒童的?社會在進步文明著,怎么還有這樣的荒蠻和野蠻?”?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賈平凹,他看到了社會劇變過程中人們道德觀念的淪喪。
鄉村的衰亡是必然趨勢,但胡蝶在夢中選擇衰亡的鄉村,是賈平凹在這里看到了鄉村在衰亡過程中,仍有令人溫情的一面,而這恰是城市過度發展中被忽略的。優質文明在發展過程中,對農耕文化的破壞力是巨大的,但這種破壞是良莠不齊的,作者借助胡蝶的眼睛,通過老老爺的一系列行為說明,圪梁村中殘存著的傳統道德和民間風尚是不應被席卷而毀壞的。如同上節所述,對于傳統民間道德,賈平凹在他的小說創作中有堅定的引線。從《秦腔》中的秦腔,到《古爐》中的善人說病,以及《帶燈》中的寺廟,這都是賈平凹在農村頹敗和沒落過程中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想象。這種想象,在《極花》中也是以隱喻和象征的方式出現。比如,極花——象征傳統民間道德,這個原本的蟲子,經過冬天的蟄伏,也可以蛻變成花。極花或許是賈平凹對傳統和民間道德在現代社會的想象,它在具有巫史身份的老老爺身上得到集中表現,并得到主人公胡蝶的認可,在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中,極花雖然很難找到,但誰又能否認傳統在現代化的轉化中不需要經歷陣痛?
①[秘魯]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給青年小說家的信》[M],趙德明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頁。
②③韓魯華,賈平凹《虛實相生繪水墨極花就此破天荒——〈極花〉訪談》[J],《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3期。
④楊友楠《二元結構的設置與個人立場的懸擱——對賈平凹長篇小說〈極花〉的一種解讀》[J],《文藝評論》,2016年第11期。
⑤⑦⑧⑨??賈平凹《極花》[J],《人民文學》,2016 年第1期。
⑥程華《語言本體論的寫作探索:賈平凹〈老生〉中的反抒情話語與方言寫作》[J],《文藝評論》,2017年第8期。
⑩李澤厚《由巫到禮 釋禮歸仁》[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8-33頁。
?梅蘭《〈極花〉:巫史傳統下的和解與暴力》[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
?賈平凹,舒晉瑜《寫胡蝶,也是寫我自己的恐懼和無奈》[N],《中華讀書報》,2016年 3月3日。
?張汝倫《狂者的世界》[N],《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 4月20日。
?賈平凹《〈極花〉后記》[J],《人民文學》,2016年第 1期。
陜西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基金項目“賈平凹與中國文學傳統研究”(17JZ028)]
商洛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