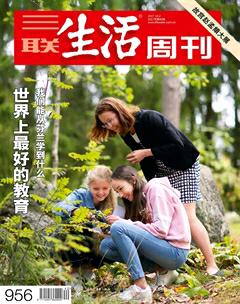真相既不理想也不完整,但它是最好的
孫欣
在患者的眼里醫生全都神通廣大,但醫生經常是在信息不確定、不完備、不精準的情況下努力做出正確的決策。
醫生的直覺比檢查更有效?

普通人對“真相”有何期待?如果“醫學的真相”是個真人秀節目,大概會拍攝這樣的內容:醫生日常生活里的一天,觀察診斷治療一個接一個的病人,與同事的合作與爭端,大到診療方案生出不同意見,小到為一支筆斗氣,應付成堆的表格和報告,還要抽空寫論文。健康人不必進醫院的時候,對醫學真相的期待,大概可以通過電視節目的焦點推知一二。
所謂“真相”,總是意味著不美好的圖景,否則就會被稱為“理想”了。理想和真相合一的情況,可能還沒發生過。醫學的第一個真相是:醫生如何在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下做出決定。卡索爾醫生是一個充滿人格魅力、技術已入化境的外科醫生。他訓練實習外科醫生的方法是放手讓他們去做,因為他總能預言到并及時挽回實習醫生手術中犯的錯誤。這是好醫生成長的必由之路。“根據完備的信息做出完美的決定很容易,醫學卻要求你用不完備的信息做出完美的決定。”由于知識和經驗以及檢查手段的限制,信息永遠不可能完備。臨床上遇到的情況看起來雜亂無章,沒有規律,難與書本知識做出對應,因此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癌癥醫師悉達多·穆克吉提出了三條法則,作為醫學學識和臨床智慧之間的橋梁。
第一條法則是:敏銳的直覺比單一的檢查更有效。被病痛折磨的人往往會把醫生當成救死扶傷的圣手。正因如此,醫生的錯誤似乎不可饒恕——難道醫生不是有世界上一切手段、能看穿人的里里外外嗎?自從抗生素、疫苗、X光透視、核磁共振被發明以來,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幾近被尊為魔術師。在理想的情況下,醫生只要把能做的檢查給病人都做一遍,就像《星際迷航》里的醫生手持儀器一掃,就可以得出合理結論。但是現實中的醫生不可能做無限的檢查,因為檢查不僅耗時費力花成本,也不是百分百可靠。醫生必須先通過“直覺”下一個大概的判斷,才能找到合理的診斷方式。
穆克吉遇到過一個病人,波士頓燈塔山的卡爾頓先生,是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因為體重急劇下降來醫院就診。初步判斷是癌癥,但所有的體檢指標都排除了癌癥的可能。直到穆克吉瞥見他在醫院的咖啡廳里與一名毒販交談時,才恍悟卡爾頓先生也是癮君子。這下判斷轉了一個大彎,指向艾滋病。檢驗結果證實了穆克吉的猜想。
醫學檢測有假陽性的可能,任何假陽性的結果都可能將醫生引入歧途。考慮到醫生要處理很多案例,假陽性的誤導會耽誤所有人的診療,甚至使檢測變得毫無指導意義。要使檢測具有指導意義,醫生必須“先大致了解答案,才能真正獲得答案”。經驗豐富的醫生看起來用直覺做出判斷,其實他們所憑借的是多年積累的知識。有經驗的腫瘤醫生會問病人一些看似無關的奇怪問題,甚至用口誤來測試病人的認知反應能力。比如糾正別人脫口而出的錯誤日期,需要“注意力、記憶力和認知力的共同協作”。穆克吉認為,貝葉斯的概率論和基于先驗知識的應用是將醫學規范化為科學的重要基礎之一。
第二條法則是:不同的人對同一種藥物的反應不同。“個體醫療”目前是研究熱點。對醫生來說,發展個體醫療的訴求一直都存在。很久以來,藥物研究致力于找到普遍有效的藥物。這種方法不是沒有成功的例子,但失敗次數比成功次數多得多。隨著案例的積累,醫學界認識到大多數疾病的成因是混合的,因此進一步的目標變成將混合的因素一一分辨出來。隨著基因研究和分子生物學的大幅進步,臨床醫學在一點點接近這個目標。治療膀胱癌的實驗藥物“依維莫司”在44個病人身上都沒起作用,在第45號病人身上——一個年過七十的老人——卻令她的腫瘤細胞幾乎完全消失了。通過研究第45號病人的腫瘤樣品,科學家和醫生鎖定了一個關鍵性的基因Tsc1。后來的研究果然發現,依維莫司對攜帶有Tsc1突變的病人有一定療效。醫學正在由只研究“常態”向著注重“個體”轉變,并期望借助對個體的研究,修改完善甚至全盤新建模型。開普勒用這種方法將布拉赫提出的行星圓形軌道修訂為橢圓形,醫生們也在用這種方法重新審視被歸為同一類的癌癥,甚至最簡單的傷口愈合。
醫生的錯誤
最誠懇的、也是最讓讀者不放心的是穆克吉總結的第三條法則:對于每個完美的醫學實驗,都有一種完美的人類偏見。為什么看似有益的醫學方案卻是有害的?這是因為醫生和普通人一樣,容易充滿“希望”。“希望”在病人或許是一種好的安慰劑,卻可能使醫生執迷不悟,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失去尋找更佳方法的時機。犯錯誤的醫生越是德高望重,受害的人就越多。巴爾的摩的杰出外科醫生威廉·霍爾斯特德認為乳腺癌復發是因為手術沒有將癌組織切除干凈,因此他主張切除病人的乳房和乳房之下的大量組織,達到徹底清理手術區域的目的。由于他的權威地位,一代代訓練出來的外科醫生都遵循著“根治”的思想。直到隨機對照實驗的方法廣泛推行開來,數據對比有力地證明了“根治切除”并不能根治乳腺癌,接受了根治切除手術的患者復發概率和接受保守手術或局部放射治療的病人復發概率一樣。以幾十萬例錯誤手術為代價之后,乳腺癌的“根治性手術”終于被拋棄。
來自病人或實驗對象的偏見也會強烈地左右醫學研究。日常生活中有一個常見的“孕婦偏見”:一個女人懷了孕,就會忽然發現生活中到處都是懷孕的女人。有個笑話說當代心理學研究的都是常青藤院校20至30歲之間的白種人,因為各種需要志愿者的實驗沒有能力在社會上廣泛尋找研究對象,只能在大學各院系和學生宿舍里貼小廣告。既然偏見很難消除,糾正由人類偏見和樣本偏差引入的錯誤就成了現代醫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有些研究者的工作是開拓,有些研究者的工作是糾正。做研究的人都知道開拓的工作比糾正的工作要吸引眼球,但正是因為有糾正的工作,醫學這門最年輕的科學才得以一直保持在科學道路上前進。
讀罷穆克吉總結的三條醫學規則,讀者會通過他的雙眼看明白何以用這樣的方式描述醫學的真相。一個經驗豐富的醫生,經歷了醫學院的苦讀、住院醫的錘煉、科室輪轉的走馬燈、專科的深入練習和鉆研,在獨當一面地診療和教學,成為業界翹楚以后,自然和病人甚至普通醫生的視角很不同。穆克吉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腫瘤醫生之一,發表過多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甚至還寫過大獲成功的科普暢銷書。他看出來,醫學的真相不只是十年寒窗的辛苦、每日例行工作的瑣碎,也不只是失去病人的淚水和救活人命的笑容。這本書里描述的真相,是百萬醫學從業者每日面對的無法回避的處境,決定著醫療體系和操作是現在這個樣子。這樣的真相既不理想也不完整,但它是醫生和病人共同努力所能達到的最好的現狀。把醫學的真相在醫生和病人面前攤開來,才有可能讓他們加深相互了解,從根本上改變并提升常規醫療體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