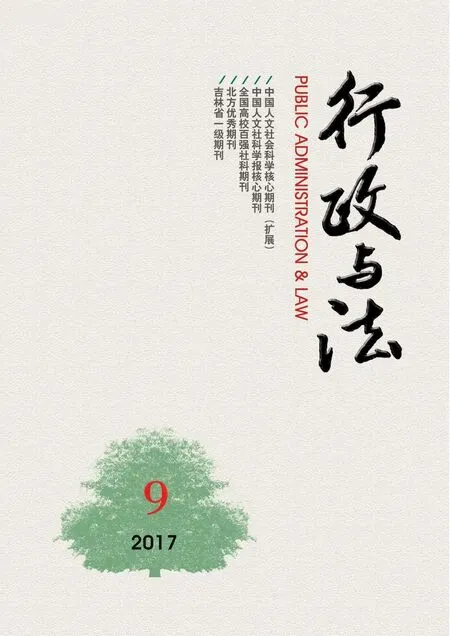我國城鄉規劃地方立法問題研究
□ 侯廣紅,汪 棟
(山東農業大學文法學院,山東 泰安 271018)
我國城鄉規劃地方立法問題研究
□ 侯廣紅,汪 棟
(山東農業大學文法學院,山東 泰安 271018)
我國自2008年1月1日實施 《城鄉規劃法》以來,各地紛紛依照 《城鄉規劃法》制定城鄉規劃地方法規,特別是2015年修改后的 《立法法》將城鄉規劃立法權擴大到所有設區的市之后,制定城鄉規劃地方法規的城市日漸增多。通過對城鄉規劃地方立法情況進行梳理后發現,受立法體制、城鄉二元結構、立法專業化水平、公眾參與意識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仍存在缺乏地方特色、可操作性不強、部門利益傾向、行政機關主導立法等諸多問題。對此,本文提出了更新立法觀念、提升立法質量、改進各主體訴求表達方式、構建立法配套程序等建議,以期為完善我國城鄉規劃地方立法提供參考。
城鄉規劃;地方立法;立法質量;立法理念
2015年3月,我國修改后的《立法法》將擁有地方立法權的主體擴大到所有設區的市,這表明所有設區的市均可以就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事項進行立法。城鄉規劃是城鄉建設與管理中的重要事項,指的是政府為了實現城市、鄉村經濟社會共同發展而協調城鄉的空間布局和基礎建設的綜合部署。城鄉規劃具有綜合性、全局性和戰略性,規劃得當能夠確保城鄉的土地資源和公共設施得到合理配置與充分利用。換言之,合理的城鄉規劃通過立法能夠得到保障,立法是規范城鄉規劃的根本之道。
目前,學界從立法角度對城鄉規劃的研究成果頗多,但大都是對《立法法》修改之前的研究。隨著修改后的《立法法》的頒布,城鄉規劃地方立法擴容,對該問題的研究內容將變得更加豐富。
一、我國城鄉規劃地方立法狀況
城鄉規劃地方立法就是各地方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制定地方性的城鄉規劃條例、辦法或實施細則等,用于指導本行政區域內的城鄉規劃。
在《立法法》修改前,享有地方性法規制定權的“較大的市”有49個,包括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27個,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18個以及經濟特區所在市4個,與此對應,“設區的市”中尚沒有地方立法權的有235個。[1]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權擴大到所有設區的市。因此,擁有地方立法權的主體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市及其他設區的市五類。
(一)省、自治區、直轄市城鄉規劃立法
目前,我國共有23個省、5個自治區和4個直轄市。這一類主體的城鄉規劃立法狀況如下:

表1 省、自治區、直轄市城鄉規劃立法狀況
除我國臺灣省以外,其他22個省、5個自治區和4個直轄市均制定了城鄉規劃地方法規。已進行城鄉規劃立法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占比情況如下:

圖1 省、自治區、直轄市已立法占比情況
(二)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市城鄉規劃立法
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市共有27個,這一類主體的城鄉規劃立法狀況如下:

表2 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市城鄉規劃立法狀況
到目前為止,拉薩、太原、蘭州、長沙4市未制定城鄉規劃地方法規,其他23個市均已制定城鄉規劃地方法規。已進行城鄉規劃立法的城市占比情況如下:

圖2 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市已立法占比情況
(三)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城鄉規劃立法
為了解決地方立法權問題,國務院于1982年創設了較大的市這一概念。自此,獲得較大的市稱號的城市就擁有了地方立法權。國務院先后分四次共批準了19個較大的市,其中,重慶市于1997年設立為直轄市,不再屬于較大的市。因此,目前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共有18個。這一類主體的城鄉規劃立法狀況如下:

表3 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城鄉規劃立法狀況
到目前為止,除吉林市和本溪市未制定城鄉規劃地方法規外,其他16個城市均已制定城鄉規劃地方法規。已進行城鄉規劃立法的城市占比情況如下:

圖3 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已立法占比情況
(四)經濟特區所在市城鄉規劃立法
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為我國4個經濟特區(1980年成立),這一類主體的城鄉規劃立法狀況如下:

表4 經濟特區所在市城鄉規劃立法狀況
到目前為止,深圳市未制定城鄉規劃地方法規。除深圳市外,其他3個經濟特區所在市均已制定城鄉規劃地方法規。已進行城鄉規劃立法的經濟特區所在市占比情況如下:

圖4 經濟特區所在市已立法占比情況
(五)其他設區的市城鄉規劃立法
目前,我國共有284個設區的市,包括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27個,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18個以及經濟特區所在市4個,其他設區的市235個。這一類主體的城鄉規劃立法狀況如下:

表5其他設區的市城鄉規劃立法狀況
由于獲得立法權的時間較短,到目前為止,只有7個城市制定了城鄉規劃地方法規。已進行城鄉規劃立法的城市占比情況如下:

圖5 其他設區的市已立法占比情況
根據以上統計可知,截止到目前,擁有地方立法權的主體有80個已頒布地方城鄉規劃條例(規定)。其中,省、自治區、直轄市31個;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市23個;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16個;經濟特區3個;其他設區的市7個。各類主體城鄉規劃立法占所有城鄉規劃地方立法的百分比情況如下:

圖6 各類主體立法占比情況
如圖所示,其他設區的市所占比重較小。地方立法權擴容之后,其他設區的市將成為立法的主要主體,未來將陸續制定城鄉規劃地方法規。
二、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中存在的問題
(一)內容設置不科學
⒈缺乏地方特色。地方性是地方立法的靈魂和標識。[2]城鄉規劃具有很強的地域性,《立法法》賦予地方立法權,就是為了讓地方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出具有地方特色、符合地方實際的城鄉規劃法規,以更好地指導本行政區內的城鄉規劃。但在城鄉規劃地方立法過程中,由于人力、物力及財力有限,立法人員缺乏專業知識,導致一些城鄉規劃法規缺乏地方特色,照抄照搬上位法現象嚴重。城鄉規劃地方法規在結構上與《城鄉規劃法》高度一致,或是改變其語句表達方式,或是重新調整條文順序,大多沒有結合地方實際,使地方立法容易淪為形式主義的文本,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進而降低其權威性。[3]同時,這種缺乏地方特色的重復立法也不利于我國的法制建設。
⒉可操作性不強。可操作性就是要求城鄉規劃地方法規具有可執行性,能解決實際問題。但到目前為止,我國大多數城鄉規劃地方法規都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可操作性不強是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乃至所有地方立法普遍存在的缺陷。現行的城鄉規劃地方法規在內容上對規劃編制作了較多規定,但對規劃管理、操作程序、監督檢查、法律責任規定得較少、較籠統,操作性不強。[4]例如:某市城鄉規劃法規中未對公眾特別是利害關系人的城鄉規劃監督作出規定,沒有統一的信息公開平臺,未建立信息公開、查詢制度,公眾很難知曉城鄉規劃管理的有關事項。一旦遇到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實際問題時,利害關系人就會發現法規條文規定得不明確,難以維護自身利益。
⒊鄉村規劃立法相對滯后。長期以來,我國的法律制度和規劃管理體系實行的是城鄉分離的二元體制,“城市中心主義”思想濃厚,重“城市規劃”、輕“農村規劃”現象嚴重。[5]即城鄉分離,城鄉在規劃管理上的標準不一致。城鄉規劃地方法規中對城市規劃作了詳細的規定,而鄉村規劃嚴重滯后。鄉村規劃立法的滯后導致鄉村建設規劃及管理相對遲緩,在鄉村建設規劃中甚至出現了以村容規劃代替鄉村建設規劃的現象,嚴重影響了鄉村建設與發展,導致城鄉差距愈來愈大。
(二)各方主體利益表達不均衡
⒈部門利益傾向。在地方立法中,法規草案由政府相關部門工作人員起草,容易產生部門利益傾向。即在起草法規時,規劃部門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讓部門利益通過法規得以體現,從而實現利益的法制化。具體而言,草案起草完畢經起草部門初步討論同意,報送主管機關批準同意后形成征求意見稿,征求相關各方意見。在征求意見稿中,如若存在對其他部門不利的規定,相關部門就會建議對法規內容進行修改,以維護這些部門的利益。各部門對草案提出修改意見,會導致一些具有創新性、實效性但有違各部門利益的內容被刪改。因此,法規草案往往會帶有較深的政府職能部門痕跡,成為擴大政府職能部門職權和自身利益的手段。[6]
⒉行政機關主導立法。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發揮人大和人大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明確立法權力邊界,從體制機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可以說,加強地方立法工作機制創新,改變行政機關主導立法為人大主導立法,既是我國深化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7]立法權是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要職權,在理論上,應由人大主導立法,而且這種主導作用要體現在立法的每一個階段,即從立法初衷到立法建議的提出,從立法調研到立法協商,每一個過程都應該有人大的身影,也都離不開人大的引領。[8]但現實中,行政機關被賦予了很大的權力,具有主導地位,體現在立法過程中即行政機關往往擁有絕對話語權,是掌握立法信息的絕對主體。由于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資源有限,法律草案一直由行政機關相關部門負責起草,審議和表決等過程也由行政機關主導,因而人大及其常委會難以發揮主導作用。
⒊公眾參與嚴重不足。當前,我國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中公眾參與處于“象征性”參與階段。在立法過程中,如若公眾廣泛參與,他們的意愿能最大程度地受到尊重,則制定的城鄉規劃地方法規就能最大程度地維護公眾利益;但在實際的城鄉規劃地方立法過程中,公眾表達意見渠道不暢,其訴求得不到充分的表達,當然就談不上維護公眾利益。城鄉規劃地方法規草案一般由城鄉規劃部門的領導、專家和實際工作者起草,普通公眾難以參與其中。征求意見,一般采取書面征求意見或召開聽證會的方式。這一階段,公眾參與只能對法規草案中的某一部分提出意見或建議,并不能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法規草案的修改過程大多是公眾意見表達的空白期,同時,過于單一的表達渠道也嚴重影響了公眾參與城鄉規劃地方立法的積極性。
三、存在上述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體制的影響
我國的立法體制統一而又分層。統一即下位法不得與上位法相抵觸。我國的地方立法大致分為兩類:執行性立法和創新性立法。在地方立法實踐中,由于受傳統思想以及我國單一的政治體制的影響,地方立法更多的是執行性立法。[9]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也屬于執行性立法。由于下位法不得與上位法相抵觸,因此,受保守、缺乏創新的立法體制的影響,地方不愿意冒風險去創新,導致地方立法很容易成為國家立法的翻版。例如:城鄉規劃地方法規依據《憲法》《立法法》及《城鄉規劃法》制定,不僅缺乏地方特色,可操作性不強,而且重復立法現象嚴重。
(二)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
我國是典型的二元社會,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嚴重影響了鄉村建設與發展,導致城鄉差距日益加大。城鄉二元結構,在經濟上體現為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的差異;在社會發展上體現為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異;在行政管理上體現為城鄉分治,重“城市規劃”、輕“農村規劃”現象嚴重。體現在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中,則是忽視鄉村建設規劃,導致鄉村規劃立法相對滯后。然而,城鄉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只有城鄉協調發展,經濟社會才能協調健康發展。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鄉二元結構已不適應城鄉統籌發展的需要,城鄉一體化發展已成為趨勢。
(三)立法專業化水平不高
地方立法是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城鄉規劃又具有很強的技術性,因此,城鄉規劃地方立法的難度系數較高。城鄉規劃地方立法涉及各主體、各部門、利益集團和普通公眾,關系比較復雜。前期的立法調研工作量大,草案起草水平要求高,之后的城鄉規劃地方法規的修改與完善等都要求立法主體在具備城鄉規劃技術性知識的同時,還應掌握豐富的法律知識,擁有良好的法律素養。然而,在實際工作中,立法人員素質相對較低,規劃專業知識不足,法律知識匱乏。同時,地方立法人員固守傳統的“政府管理”思維,認為地方立法就是地方政府規章,不重視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地方立法體制中的重要作用。[10]以上種種,導致城鄉規劃地方立法質量不高,部門利益傾向嚴重,行政機關主導立法,人大難以發揮作用。
(四)公眾參與意識不強
在我國,傳統“官本位”思想還很嚴重,公眾參與有限,表現為法治意識不強、參與積極性不高。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管理公共事務、調節社會矛盾主要依據相關政策,法律的作用居于次要地位,加之一些干部習慣于用政策,不善于用法律,因而人們對立法的需求和監督沒有那么迫切,對條文規定的內容沒有那么關心,認為法規規定是否具體關系不大,主要還是要靠政策。[11]公眾法治意識比較淡薄,這種認識反映到立法工作中就是參與嚴重不足。近年來,隨著公眾知識水平的提升,法治意識有所增強,其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積極性有所提高,已通過聽證會的方式加入到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中,但由于城鄉規劃地方立法對專業知識、法律知識要求較高,因而公眾參與還存在一定的難度。
四、城鄉規劃地方立法完善路徑
(一)更新立法觀念
⒈統籌城鄉規劃。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中鄉村建設規劃相對滯后。從立法角度解決問題,就要轉變觀念,統籌城鄉規劃,在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中將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規劃分析,對城市和鄉村中的各發展要素進行合理布局,向城鄉一體化邁進,促進城鄉共同發展。
⒉樹立開門立法觀念。城鄉規劃地方立法由規劃部門起草,行政機關主導,各部門之間相互博弈,部門利益傾向嚴重,導致立法機關缺少話語權。在法規出臺之前,通過聽證會的方式向公眾征求意見,但因公眾參與嚴重不足,使得聽證方式流于形式。因此,城鄉規劃地方立法應樹立開門立法觀念,集思廣益,讓不同利益群體之間開展協商對話,以遏制部門利益。開門立法將立法全過程公開,有利于接受社會監督,使得城鄉規劃部門在起草草案時較少摻雜部門利益,更多地考慮公眾利益。
⒊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發達國家地方立法起步早,城鄉規劃地方立法體系相對完善,有許多先進經驗值得學習和借鑒。例如:英國自第一部《城鄉規劃法》(1932年)頒布以來,雖經歷了多次修改,但其核心內容并沒有改變,即把城、鄉視為空間上相互關聯的整體,在規劃上予以同等對待,各層次的規劃政策或文件中必須包括城、鄉兩方面的內容。[12]韓國積極完善公眾參與程序,大力支持非政府組織參與立法。因此,在城鄉規劃地方立法工作中,應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分析總結我國城鄉規劃地方立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結合當地實際,這樣,才能制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鄉規劃法規。
(二)提升立法質量
⒈立法前進行充分調研。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部反映民情、代表民意的良法,不是主觀臆造出來的,而是來自于對實際情況的充分了解和把握。在立法之前,如果不進行充分調研,就難以作出正確的決斷,制定的法規就可能存在脫離實際的可能。因此,要加強立法調研和準備工作,研究法規的可行性,做好草案起草工作,提高立法質量,使立法符合地方實際。
⒉增強立法的可操作性,即把提升立法質量這一要求貫徹到法規的立項、起草、征詢、審議等過程中。城鄉規劃地方立法講求實用,不要一味追求完整性而照抄照搬上位法,而是要根據地方實際情況,需要幾條制定幾條。號召性條款盡量少些,規劃管理、操作程序、監督檢查、法律責任等內容盡量細化。同時,法規的語言表述應力求準確、簡練。
⒊注重立法創新。地方立法往往缺乏可操作性,對此,要注重立法創新,體現地方特色,增強立法的針對性、可操作性。例如:加強立法機關與公眾的溝通,制定針對性強的地方法規,規范和完善城鄉規劃的編制審批程序與內容、行政許可審批與決策程序和要求、行政執法與司法程序、規劃的公眾參與程序和規劃實施監督制約機制等,完善各項具體實施細則。[13]
⒋提高立法人員專業化水平。城鄉規劃地方法規起草擬定亦或修改、完善,都要求立法者擁有良好的法律素養、豐富的法律知識和較高的立法技術。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說,立法人員的專業化水平能夠決定立法質量的高低。在實際立法工作中,由城鄉規劃部門人員起草規劃法規草案,其法律知識相對匱乏。因為較高的立法技術不是普通規劃部門人員可以輕松掌握的,需要通過系統的法律知識學習,有一定的法律專業知識積累。針對這一現象,可以建立地方立法助理制度,聘請具有立法專門知識的人員協助立法機關及其組成人員履行立法職責、完成立法工作。[14]
(三)改進各主體訴求表達方式
⒈加強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城鄉規劃地方法規由城鄉規劃部門負責起草,容易產生部門利益傾向。其他相關部門在征求意見稿中表達意見,如若法規中有對其部門不利的規定,就會提出修改建議,以維護本部門的利益。但當規劃部門與其他部門意見出現分歧時,就會出現各方爭執、互不妥協的情況,嚴重時還可能導致立法擱淺。為了確保立法工作的順利進行,各部門應加強立法協調,建立協商與對話機制。當出現意見不一致的情況時,應積極溝通協調,爭取達成一致。同時,通過各部門之間的相互牽制能夠減少部門利益傾向,維護公眾利益。在立法過程中,要著眼于全局利益和公眾的根本利益,運用“立法決策同改革決策、發展決策相統一”的原則,以法律法規為依據,認真做好協調把關工作。[15]
⒉發揮人大的主導作用。人大主導立法,其主導作用應體現在立法的每一個階段。立項、起草、審議、修改、表決等過程都應該由人大引領。因此,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改進工作方式,優化人員構成,讓人大的立法權真正發揮主導作用。在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中,雖然立法機關的立法資源有限,由城鄉規劃部門起草立法草案,但并不代表不需要人大參與其中,而是需要人大提前介入立法的各個環節。
⒊完善公眾參與機制。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不僅需要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的參與,也要充分聽取公眾的意見。賦予公眾參與權與表達權,可以解決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中涉及公眾利益的問題,從而保障立法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對此,可以通過書面征求意見,召開座談會、論證會等多種途徑和方式聽取公眾意見,增加公眾參與的方式、途徑等。在采用公開方式進行立法時,要考慮規劃的性質、公示的期限、公示成本、公示效果等因素,對公眾權益影響越大的規劃越要采取便于公眾知曉的途徑,或規定至少采用某種方式以便于公眾知曉。[16]
(四)構建立法配套程序
⒈強化憲法監督制度。《立法法》修改后,立法主體增多,所有設區的市都可以進行城鄉規劃立法,這樣,憲法監督即被提上更緊迫的日程。對城鄉規劃地方立法進行憲法監督可以實現國家、地方與個人多方利益的平衡。憲法監督或稱違憲審查制度的核心要義是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發現具有違憲嫌疑的事實,二是如何對違憲事實作出判定和處理。[17]城鄉規劃地方立法具有極高的法治價值,但在立法過程中仍存在地方保護主義、部門利益傾向。因此,要強化城鄉規劃地方立法的憲法監督制度,按照“有法必備、有備必審、有錯必糾”的要求,建立備案審查制度和違憲、違法專門審查制度,以提高地方立法質量。
⒉完善立法信息公開機制。信息公開是公眾參與的前提。城鄉規劃地方法規與公眾息息相關,對于立法的各程序步驟,公眾都有權知曉并參與。立法信息公開可以保障公眾的知情權,提高公眾參與立法的積極性。城鄉規劃地方立法中規劃部門將法規草案送交審議之前要進行公告,征求公眾意見,草案通過之后應將定稿向公眾公布。但在現實中,地方在城鄉規劃立法的起草、審議、修改及完善各環節都沒有及時向社會公開,公眾對于立法內容是否侵害了他們的利益等一無所知。因此,在城鄉規劃地方立法過程中,應采取公告、宣傳等多種方式及時公開立法各階段的信息,這樣,才能充分保障公眾的知情權,為公眾參與城鄉規劃地方立法提供便利條件。
⒊完善法規配套制度。地方城鄉規劃條例只是地方城鄉規劃的主干法,依然需要相關配套的法規、規章與其配合,所以,“地方立法機關應當適時更新和完善其他法規、規章以及相關的規范性文件、技術標準等,建立以地方城鄉規劃條例為主體的完整的地方城鄉規劃”。[18]這樣,才能促使地方制定科學的城鄉規劃,確保城鄉土地資源與公共設施的合理配置與充分利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⒋設立立法聯系點。立法聯系點即在基層建立的協助立法單位,是公眾直接參與立法的重要載體。作為一個平臺,立法聯系點可以收集基層的社情民意。設立基層立法聯系點,可以直接聽取公眾的意見,更好地開展立法工作。因此,可以在高校、社區、企業等設立立法聯系點,通過聯系點收集城鄉規劃立法及其他方面地方立法的信息,反饋公眾的意見和建議,協助相關部門開展立法工作。
⒌成立立法專家咨詢庫。專家參與可以確保更好地立足于實際,將法學理論知識與立法實踐結合起來,以保證立法的科學性、提升立法質量。成立立法專家咨詢庫,擴大與公眾的接觸范圍,加強各主體之間的溝通協調,能夠確保立法的民主性。為保證專家具有代表性、專業性,各地應聘請各行業的立法專家庫成員,如在公檢法部門、高校、律師事務所等擇優篩選立法專家庫成員。
修改《立法法》,授予地方立法權、規范授權立法,標志著我國已進入由“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階段。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因此,堅持立法先行,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體系,能夠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基本遵循。
[1]鄭磊,賈圣真.從“較大的市”到“設區的市”:地方立法主體的擴容與憲法發展[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04):86-99.
[2]姚愛國,凌冰,吳偉.設區的市開展城鄉規劃地方立法若干問題之思考[J].規劃師,2015,(12):25-30.
[3]林琳.對實施性地方立法重復上位法現狀的原因分析和改善設想[J].人大研究,2011,(01):35-39.
[4]方慈,王金山,張俠,陳紅娟,黃志英.河北省城鄉規劃立法研究[J].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3):50-55.
[5]舒沐暉,扈萬泰,余穎.基于城鄉統籌思想的重慶市規劃編制體系構想[J].城市規劃,2010,(06):31-35.
[6]孫育瑋等著.完善地方立法立項與起草機制研究[M].中國計劃出版社,2007.
[7]石佑啟,潘高峰.2015年度中國地方立法評析——以地方性法規為觀察對象[J].地方立法研究,2016,(01):78-91.
[8]王秀才.地方立法規范化發展問題研究[J].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3):184-188.
[9]楊君杰.城鄉規劃地方立法研究——以《云南省城鄉規劃條例》為例[D].昆明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10]任爾昕,宋鵬.關于地方重復立法問題的思考——正確理解并遵循立法的科學原則[J].法學雜志,2010,(09):90-93.
[11]李高協.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問題探討[J].人大研究,2007,(10):33-36.
[12]炳榮,易崢,錢紫華.國外城鄉統籌規劃經驗及啟示[J].規劃師,2014,(11):121-126.
[13]郭新天,陳靜超,趙玉磊,吳瑕.關于地方城鄉規劃法規體系建設的探討———以天津市為例[J].城市,2012(08):11-14.
[14]吳大英,任允正.比較立法制度[M].群眾出版社,1992.
[15]唐英.城鄉規劃地方性立法探索[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3,(12):118-119.
[16]李倩.城鄉規劃公眾參與立法研究[A].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轉型與重構——2011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C].東南大學出版社,2011.3928-3936.
[17]焦洪昌,馬驍.地方立法權擴容與國家治理現代化[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4,(05):41-46.
[18]劉鴻.論我國地方城鄉規劃制定法規的完善[D].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責任編輯:高 靜)
Abstract: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Law in 2007,since January 1,2008,all localities have formulated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Law.In particular,the new “legislation” in 2015 will extend the legislative power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o the cities all districts.Based on the summary of local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legislation,found by the legislative system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two Yuan structure,legislation of professional level,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other factors,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of local legislation in China there is a lack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operability is not strong,prone to many problems,departmental interest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leading legislation.To solve these problems,put forward legislative ideas,updat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improve the legisl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demands of expression,supporting the program path to improve the local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legislation,in order to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legislation in China to make a modest contribution.
Key words:urban and rural planning;local legislation;legislative quality;legislative idea
A Study on Local Legisl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 China
Hou Guanghong,Wang Dong
D922.297
A
1007-8207(2017)09-0022-09
2017-06-15
侯廣紅 (1992—),女,山東臨沂人,山東農業大學社會管理與政府法治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地方政府法治建設;汪棟 (1968—),男,安徽肥東人,山東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法學系主任,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憲法與行政法。
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 “法治中國建設視野中的憲法實施與監督程序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5CFXJ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