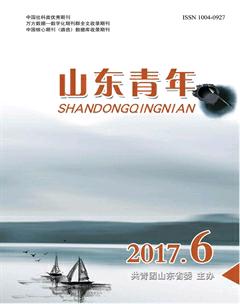論孔子“中庸”思想的當代價值意蘊
李萍
摘要:“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方法論原則,主要包括“過猶不及”的適度原則、“和而不同”的尚和原則、“執中知權”的權變原則等特征。當今,我國正處于社會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整個社會正經歷著深刻的變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致使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道路,已為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關鍵。因此,作為儒家文化核心之一的孔子的“中庸”思想在當代社會建設中便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中庸思想;當代價值
考古學家蘇秉琦說:“中國是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啟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統一實體。”然而隨著全球化浪潮,西方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價值觀念的滲透,強烈的沖擊著這個古老的民族。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然而切合時代精神的民族優秀價值觀缺失和主流文化引導的乏力使人們對各種外來文化的包容達到了無原則的地步,只要滿足人們的需要,不管是低俗的還是高尚的文化都有其生存的土壤,文化正在成為一種大眾產品被人們瘋狂的消費著,當人們在享受文化這種繁榮的時候,我們傳統的仁、義、禮、智、信等精神追求的意義和價值不斷被貶低,甚至在大多數國人的眼中都認為,以孔子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是腐朽、落后的代名詞。事實證明,對傳統文化的拋棄和背叛意味著文化發展的斷裂,意味著文化發展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當前社會轉型的關鍵期,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同時也預示著兩者的對話。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儒家文化,仍然有其強大的生命力和遠大的發展前途。正如杜維明先生曾說過的:“儒家傳統是人類精神文明之一,像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一樣,也許能為解決當前人類的困境提供一些精神資源。”孔子的“中庸”思想對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便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孔子“中庸”思想的釋義
“中庸”思想起源甚古。相傳早在氏族社會,帝啻便“溉執中而遍天下”。堯舜時代,又有所謂“允執厥中”的說法。成書于殷周之際的《周易》一書,更是鮮明的體現了尚“中”的傾向。春秋之際,孔子從前人論述的“尚中”、“尚和”的哲理中,吸取思想營養,首次提出了“中庸”之德:“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庸也》)“庸”,本來具有變更、改革之義,但在這里對“中”起修飾作用,不能只是一般的“變更”、“改革”而是使“中”能夠根據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主動向最好的方面“變更”、“改革”,使“中”的哲理顯得更透徹,更具體,更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孔子言論中的“中庸”,主要闡明這樣的觀點:
1、“中庸”是一種最高尚的道德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可見,在孔子看來“中庸”作為一種最高尚的道德,只有圣人才具備這種道德人格,或者說具備了這樣道德人格就能成為圣人。孔子說“君子依乎中庸,也不見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禮記·中庸》)也就是說“君子處事依據中庸之道,遠離世俗不被世人賞識也不后悔,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2、“中庸”是為政者實行最佳的惠民政策
孔子認為古代的圣明帝王,都是因為“執中”而興盛。“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論語·堯曰》)另外,孔子還多次講到古代帝王應遵行“執中”之道而深受人民愛戴。“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禮記·中庸》)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3、“中庸”之道的堅守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禮記·中庸》)可見,堅守中庸之道是一項多么復雜而艱巨的任務,不僅需要有大無畏的勇氣,更要有堅定地道德意志和理性的政治智慧,才能真正的做到中庸。另外,在當時社會歷史條件下,中庸之道的推行遇到許多障礙,孔子曾多次哀嘆:“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陷阱之中,而莫之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禮記·中庸》)又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尚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禮記·中庸》)
誠然,孔子“中庸”思想的闡述中,可以看出“中庸”思想既是一種世界觀,又是一種方法論。它不僅能作為一個國家的思想指導,同時也能成為個人的行為準則。
二、孔子“中庸”思想在當代社會的價值
毛澤東同志說過:“孔子的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大范疇,值得好好解釋一番。” 可以說,“中庸”思想不只是一種為人處世之道,更是治國安邦之道,它對當代社會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提倡“中庸”思想有利于尋求和諧、科學的當代社會發展之路
和諧社會絕不是一個沒有利益沖突的社會,相反,和諧社會應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并由此實現利益大致均衡、公正的社會。而作為“中庸”思想,它要求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協調矛盾,達到事物的平衡與穩定,對于我們和諧社會中存在的社會問題具有這樣的指導意義。
1、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以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
著眼于我國社會發展中產生的種種問題,我們應以“和”為起點,不是消滅社會發展中存在的所有矛盾,而是正確把握最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現階段群眾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體的特殊利益關系,統籌兼顧各方面群眾的關切,用“和”的原則化解社會發展中的不和諧,從而在矛盾和對立中協調社會各階層利益,整合社會資源。同時要根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在制定大政方針的時候針對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區域情況做到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2、把握分寸,無過無不及,以實現社會的均衡發展
在建國后,我黨曾犯過“左”“右”的錯誤,鄧小平同志指出:“右”會葬送社會主義,“左”同樣也會葬送社會主義。而我們黨所犯的“左”“右”錯誤,歸結起來都可以說是沒有把握好“中”。現在我們正處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雖然國民經濟的發展要保持較快的速度和較高的效益,但其發展速度也要“適中”,速度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快是有條件的,要講效益,講質量;快是有區別,各地發展速度可以有所不同,要做到速度與效益的統一,微觀活力與宏觀控制的統一以及總量增長與結構優化的統一,另外,我們在抓緊經濟建設的同時要把握好政治文化建設,不能急功冒進,也不能停步不前,所以,“中庸”的適度原則給我們保持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了指導意義。endprint
3、天人合一,共同發展,以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的和諧是中庸思想的內在追求,是中庸所要達到的理想社會和所追求的一種境界。當今,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社會發展的一大瓶頸,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不能走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兩極性道路,也不能放棄發展經濟,而是應該尋求一條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重的“中庸之道”,即可持續發展道路,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真正實現天人合一,共同發展。可見,作為中庸思想所推崇的“天人合一”理念所具有的現代生態倫理價值,即對于維護現代人類所處的整個生態系統平衡,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所具有的現實道德意義正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二)提倡“中庸”思想能為和諧社會建設營造一個安定和諧的國外環境
1、政治上,我們需要“執中知權”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但同時也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溝通的有力橋梁,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國的迅速崛起曾經引起世界其他一些國家的恐慌,盡管我們宣稱:中國永不稱霸。然而,“中國威脅論”仍在世界舞臺上盛行。那么,在這個復雜動蕩的國際環境下,中國要和平崛起,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就需要用“和而不同”的原則來處理好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不僅要合乎時宜地去協調解決各國之間的矛盾,但同時也要隨機變通處理好中國在國際局勢中的影響。
2、經濟上,我們需要“合作共贏”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市場一體化格局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而世界的經濟合作也需要中國的推動,在這樣的發展形勢下,我們要本著中庸“不為拘泥,不為偏激,尋求適度、適當”的要求,在樹立全球競爭意識時,不能單純的考慮經濟效益,而應該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生態效益,把發展調控在生態系統的承載范圍內。另外,不能以犧牲他國利益來換取本國的效益,而是在不造成別國利益損失的基礎上,實現與他國的合作共贏。
3、文化上,我們需要“求同存異”
20世紀20年代初印度國父甘地有句名言:“我希望各地之風都盡情的吹到我的國家,但我不能讓它把我連根帶走。”在世界多元文化得到空前交流和聯系的今天,不無啟發。我們都是和諧社會建設中的一份子,凝聚在一起就形成了社會。我們應以海納百川的胸襟,以開放的心態積極應對未來的文化的侵入,但同時要以“和而不同”的原則來保存我們文化的“根”。積極吸取外來文化的精華,努力傳承傳統文化的理念,做到適度地跟隨我們時代的潮流,而不是堅定地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用優秀的傳統價值觀念武裝我們自己的頭腦,用時代的精神理念推動我們的行為,讓自己成為全面、均衡發展的個人,真正為和諧社會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當然,“中庸”思想作為一定時代的產物,必然有其歷史的局限。孔子主張以“仁”治天下,幻想社會各階級“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子取其中”,希望在和平中損益,害怕革命性的變革,這樣在處理矛盾的過程中只過分強調矛盾的統一、調和,保持中立穩定而忽略了矛盾對立面的斗爭與轉化對事物的自我否定,妨礙了發展的飛躍。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對于“中庸”思想積極的一面我們要加以繼承和弘揚,并結合當前社會發展的形式不斷進行重新闡釋、重新發掘、重新利用,以便其更好地促進社會和諧和個人全面發展,另外一方面也要剔除其與現代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東西。
中國的今天作為昨天的延續和承接明天的起點,我們當代人只有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開拓,才能展望更美好的未來。“中庸”思想作為影響中國數千年甚至至今還影響著我們的學說,只有最大限度發揮其積極作用而消滅其負面影響,中國思想的精髓才能綻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作者單位:大理大學,云南 大理 67100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