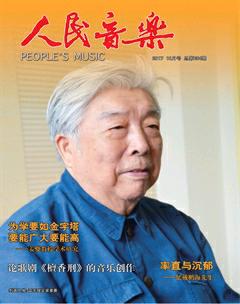相西源交響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的地域性風(fēng)格特征
一、引 言
相西源是在青藏高原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中國(guó)當(dāng)代作曲家,曾在西安音樂(lè)學(xué)院和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習(xí),并獲博士學(xué)位,現(xiàn)為星海音樂(lè)學(xué)院作曲教授。相西源出生于青海,前后共在青藏高原生活、學(xué)習(xí)、工作了近三十年,在青藏高原多民族、多文化人文環(huán)境的長(zhǎng)期浸染下,其音樂(lè)創(chuàng)作植根于這片熱土,具有濃郁的青藏高原所特有的地域性風(fēng)格特征。甚至在筆者看來(lái),相西源作為作曲家所獲得的關(guān)注與認(rèn)可也與其音樂(lè)中突出的青藏高原地域風(fēng)格密不可分。
通常而言,作曲家的音樂(lè)風(fēng)格是綜合其時(shí)代風(fēng)格、民族風(fēng)格、地域風(fēng)格及個(gè)人風(fēng)格的結(jié)果。對(duì)于中國(guó)當(dāng)代作曲家來(lái)說(shuō),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的地域性風(fēng)格主要是指由于作曲家在某一地理區(qū)域內(nèi)長(zhǎng)期生活而受到該區(qū)域內(nèi)特定文化的熏陶與影響而形成的音樂(lè)風(fēng)格特征。比如郭文景音樂(lè)中的蜀地風(fēng)格特征和趙季平音樂(lè)中的黃土高原文化特質(zhì)就分別與兩位作曲家長(zhǎng)期在四川和陜西生活息息相關(guān)。
相西源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始于上世紀(jì)70年代,至今已創(chuàng)作交響曲、協(xié)奏曲、管弦樂(lè)、交響合唱、室內(nèi)樂(lè)、廣播影視音樂(lè)、藝術(shù)歌曲等各類體裁的音樂(lè)作品數(shù)百部(首),而地域性風(fēng)格特征在其交響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從描寫巴音河畔蒙古族人民艱苦奮斗、開(kāi)拓進(jìn)取的輝煌歷史的《巴音河的回憶》(1988年),到對(duì)宗教哲理進(jìn)行深邃思考的《第三交響曲“宗”》(2003年),無(wú)論是使用微復(fù)調(diào)、偶然音樂(lè)、十二音等現(xiàn)代音樂(lè)創(chuàng)作技法,還是復(fù)合調(diào)性、色彩性和聲、極限音域等多樣化的技術(shù)手段,每一部作品都蘊(yùn)含著豐富的青藏高原地域文化氣韻,明顯地表現(xiàn)出作曲家自覺(jué)追求地域文化內(nèi)涵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理念。
二、題材的地域性
相西源的音樂(lè)風(fēng)格整體以深情、寬廣、淳樸、抒情為特征,頗為符合青藏高原高亢、嘹亮的民間音樂(lè)風(fēng)格。就題材而言,或歌唱青海的高山大湖和荒原沙漠,或贊美這里的民族風(fēng)韻與風(fēng)土人情,具有明顯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特征的作品所占比重極大。
交響音詩(shī)《巴音河的回憶》是作曲家早年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用西洋管弦樂(lè)隊(duì)、單樂(lè)章交響音詩(shī)的體裁和豐富的作曲技法,以深沉、凝重的筆觸,回憶了青海西部蒙古族人民可歌可泣的抗?fàn)帤v史和對(duì)美好生活的追求與憧憬,音樂(lè)委婉而悠長(zhǎng),深情而豪邁,具有濃郁的且不同于其他地區(qū)蒙古族民間音樂(lè)的風(fēng)格特征。
鋼琴與樂(lè)隊(duì)組曲《青藏寫生》(1990年)四個(gè)樂(lè)章的小標(biāo)題分別為“情歌”“轉(zhuǎn)經(jīng)”“酒歌”“節(jié)日”,猶如四副濃墨重彩的水墨畫卷,悠揚(yáng)的山歌、虔誠(chéng)神秘的宗教氣息、粗獷的藏族舞蹈、詼諧風(fēng)趣的土族酒曲,各樂(lè)章間形成鮮明的動(dòng)與靜、剛與柔的色彩對(duì)比,展現(xiàn)出青藏高原的風(fēng)土人情與樂(lè)觀豪放的精神風(fēng)貌。
交響組曲《河湟》(2007年)由五個(gè)樂(lè)章組成,分別以“花兒風(fēng)情”“古村印象”“牧場(chǎng)寫生”“山原之歌”和“河湟抒情”為題,從不同側(cè)面表現(xiàn)了青海東部河湟谷底的大自然風(fēng)貌,謳歌了當(dāng)?shù)貪h、藏、土各民族淳樸的風(fēng)土人情與美好的生活圖景。
被譽(yù)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多高山大川,還是長(zhǎng)江、黃河與瀾滄江的發(fā)源地,相西源的前兩部交響曲便分別以“山頌”與“江河源”為題,熱情而自豪地贊揚(yáng)了青海的高山與江河。《第一交響曲“山頌”》(1987年)為常規(guī)的四樂(lè)章交響套曲,分別以“山的追憶”“山的戀歌”“山的蘇醒”“山的沉淪”為題;《第二交響曲“江河源”》(1993)由三個(gè)樂(lè)章組成,分別為“江情”“河夢(mèng)”“源歌”。
《第三交響曲“宗”》(2003年)由三個(gè)樂(lè)章組成,主要表達(dá)了作曲家對(duì)人生、宗教、哲學(xué)的深刻理解與感悟。雖然樂(lè)曲中使用了偶然音樂(lè)、無(wú)調(diào)性、微復(fù)調(diào)等大量現(xiàn)代音樂(lè)創(chuàng)作技法,在其全部音樂(lè)作品中地域性風(fēng)格表現(xiàn)得相對(duì)較弱,也更為內(nèi)在,但音樂(lè)所具有的神秘、原始的東方宗教氣息與藏文化意蘊(yùn)等,仍然區(qū)別于一般的宗教性題材。
三、主題旋律的地域性
音樂(lè)作品的題材內(nèi)容需要通過(guò)具體的音樂(lè)表現(xiàn)力要素加以呈現(xiàn),音樂(lè)形態(tài)則是作曲家所使用的各種表現(xiàn)力要素的直接體現(xiàn)。相對(duì)于作品的題材內(nèi)容,音樂(lè)形態(tài)方面的地域性風(fēng)格往往表現(xiàn)得更加深刻,而對(duì)于中國(guó)音樂(lè)而言,由于線性化審美觀念等原因,在構(gòu)成音樂(lè)形態(tài)的諸多要素中,旋律成為了最能展現(xiàn)地域性風(fēng)格的要素之一。
相西源深受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與審美觀念影響,極為重視旋律自身的美感及其在音樂(lè)表達(dá)中的作用,因而旋律便成為其創(chuàng)作中展現(xiàn)地域性風(fēng)格的核心要素。在交響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他十分注重對(duì)主題旋律的提煉與升華,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氣息悠長(zhǎng)、優(yōu)美動(dòng)聽(tīng)、流暢連貫的主題旋律。
相西源長(zhǎng)期生活的青藏高原東北部是我國(guó)重要的多民族聚集區(qū)與雜居地,除漢族外,還生活著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多個(gè)少數(shù)民族,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同時(shí),長(zhǎng)期互相影響,而這種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在相西源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也有所反映,特別是在其作品的旋律方面的體現(xiàn)得尤為清晰。
《青藏寫生》整部作品的基本創(chuàng)作素料均取材于青海民間音樂(lè)。第一樂(lè)章“情歌”的主題便以琵琶和弦式的上行音調(diào)開(kāi)始,音樂(lè)具有濃郁的西北民間“花兒”的風(fēng)格特征(見(jiàn)譜例1),中部則直接以該主題的倒影形式開(kāi)始,使樂(lè)章整體的音樂(lè)風(fēng)格獲得統(tǒng)一;第二樂(lè)章“轉(zhuǎn)經(jīng)”低音聲部多次出現(xiàn)的逆分型節(jié)奏(xx.)的音調(diào)明顯模仿了藏傳佛教寺院宗教儀式活動(dòng)中筒欽的音響;第三樂(lè)章“酒歌”在3/4節(jié)拍中的主題旋律則明顯具有河湟谷地特有少數(shù)民族“土族”民間歌曲“酒曲”的音樂(lè)風(fēng)格特征,輕松、詼諧、幽默;第四樂(lè)章“節(jié)日”的音樂(lè)熱烈而奔放,2/4節(jié)拍中以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為主的主題旋律借用藏族民間舞蹈“堆諧”的節(jié)奏素材,并配合樂(lè)隊(duì)突出節(jié)奏律動(dòng)的織體,及在回旋曲式結(jié)構(gòu)中主題多次重復(fù)或再現(xiàn)時(shí)的變奏,凸顯出粗獷豪邁奔放的藏族舞蹈音樂(lè)風(fēng)格。
譜例1 《青藏寫生》第一樂(lè)章“情歌”主題
交響音詩(shī)《巴音河的回憶》以單樂(lè)章的奏鳴曲式結(jié)構(gòu)為主導(dǎo),其主副部主題均采用具有蒙古族音樂(lè)風(fēng)格的旋律,尤其是如怨如訴、深情纏綿的副部主題旋律近似蒙古族長(zhǎng)調(diào),但與內(nèi)蒙古地區(qū)的蒙古族音樂(lè)有著明顯的不同。(見(jiàn)譜例2)endprint
譜例2 《巴音河的回憶》副部主題
青海是“花兒”的故鄉(xiāng),具有“花兒”音樂(lè)風(fēng)格的旋律在相西源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十分常見(jiàn)。除前述《青藏寫生》第一樂(lè)章“情歌”外,其單樂(lè)章的管弦樂(lè)作品《西北之歌》(1998年)中,幾個(gè)主題的旋律也均借用了青海“花兒”的某些音調(diào)素材,展現(xiàn)出自由、高亢、舒展的音樂(lè)特點(diǎn)。如28小節(jié)開(kāi)始的雙簧管演奏的主題就以青海“花兒”[麻青稞令]為基本旋律素材,并放慢后改寫而成(見(jiàn)譜例3)。交響組曲《河湟》第一樂(lè)章“花兒風(fēng)情”和第四樂(lè)章“山原之歌”的基本旋律素材也均源自青海“花兒”。
譜例3 《西北之歌》主題
除各類民歌外,相西源對(duì)青海河湟谷地的曲藝音樂(lè)十分熟悉,尤其是其早年在青海平弦劇團(tuán)的工作經(jīng)歷,使其對(duì)青海平弦頗有研究。如交響組曲《河湟》第五樂(lè)章“河湟抒情”的旋律創(chuàng)作就以平弦音樂(lè)素材為基礎(chǔ),表達(dá)出作曲家對(duì)河湟地區(qū)的熱愛(ài)與留戀。
難能可貴的是,相西源在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從不直接完整借用已有的民歌或其他民間音樂(lè)的旋律,而總是在充分地吸收消化某些民間音樂(lè)元素的基礎(chǔ)上,提煉其核心音調(diào)素材,進(jìn)行再創(chuàng)作。一方面,將具有不同民族民間音樂(lè)元素的音調(diào)重新進(jìn)行加工,創(chuàng)作出具有多民族融合性但不單獨(dú)突出某一民族風(fēng)格的新旋律,這與施光南的旋律創(chuàng)作手法頗有幾分類似;另一方面,在借用青藏高原特色的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間音樂(lè)旋律素材進(jìn)行旋律創(chuàng)作時(shí),通過(guò)專業(yè)的音樂(lè)發(fā)展手法等作曲技術(shù)手段,在保證旋律進(jìn)行流暢性的同時(shí),結(jié)合大跳來(lái)突出旋律的器樂(lè)性,創(chuàng)作出兼具民族性與作曲家個(gè)性的全新旋律。如《第三交響曲“宗”》第一樂(lè)章的主部主題便是如此,通過(guò)七度音程的大跳使音樂(lè)的張力增加,音域跨度較大,同時(shí)也更加凸顯出高原的開(kāi)闊、高亢與粗獷,極大地加強(qiáng)了音樂(lè)的表現(xiàn)力。(見(jiàn)譜例4)
譜例4 《宗》第一樂(lè)章主題
四、創(chuàng)作觀念的地域性
作曲家作為社會(huì)的一員,其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所受到的教育以及生活過(guò)程中的自然、人文、社會(huì)等環(huán)境會(huì)潛移默化地對(duì)其文化身份認(rèn)同與思維觀念產(chǎn)生影響,從而成為其音樂(lè)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創(chuàng)作觀念會(huì)更加持久、深層地作用于作曲家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實(shí)踐,相較于旋律、調(diào)式等外在的音樂(lè)形態(tài)而言還會(huì)表現(xiàn)得更為深刻與內(nèi)在。
相西源在交響樂(lè)創(chuàng)作中特別強(qiáng)調(diào)音響的色彩變化與織體的線性化處理,通過(guò)精妙的構(gòu)思與精致的配器,不僅表現(xiàn)出生動(dòng)而具體的音樂(lè)形象,反映出作曲家豐富而細(xì)膩的內(nèi)心情感世界,更重要的是以音樂(lè)來(lái)表達(dá)其對(duì)生命的思考和對(duì)深邃的宗教、哲學(xué)思想的感悟,并體現(xiàn)出明顯的地域性特征。
熟悉相西源教授的人都很了解,出生于文化世家的他從小受到了家庭的熏陶與影響,不僅知識(shí)面極廣,且勤于思考,加之其長(zhǎng)期生活的青藏高原東部地區(qū)是典型的多宗教、多民族聚居地區(qū),使其對(duì)宗教、哲學(xué)等有著相當(dāng)?shù)母形颉⒗斫夂蛡€(gè)人的獨(dú)立思考,其音樂(lè)中的純凈、神秘、虔誠(chéng)、超凡脫俗等氣質(zhì)大多與他精神追求中受到藏傳佛教的影響不無(wú)關(guān)系。《宗》的第二樂(lè)章甚至直接以在青藏高原人民精神生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象征作用和意義的萬(wàn)字符“卍”①的符號(hào)外形為基礎(chǔ),并對(duì)其進(jìn)行視覺(jué)轉(zhuǎn)化后形成樂(lè)譜(見(jiàn)譜例5)。縱向的豎線代表對(duì)應(yīng)樂(lè)器在指揮的提示下整齊地演奏任意音,橫向演奏的音符由主題旋律開(kāi)始的音調(diào)(參見(jiàn)譜例4)接全音階構(gòu)成,低聲部則以倒影形式與其對(duì)應(yīng),從而將不協(xié)和的現(xiàn)代感音響、偶然音樂(lè)創(chuàng)作技法等與具有明顯地域性特征的宗教文化進(jìn)行有機(jī)結(jié)合,表達(dá)出作曲家對(duì)藏傳佛教純粹、神秘、虔誠(chéng)的教義與特質(zhì)的冥思與敬意。他的《青藏寫生》第二樂(lè)章“轉(zhuǎn)經(jīng)”、《第一交響曲“山頌”》第四樂(lè)章等音樂(lè)中也清晰地體現(xiàn)了藏傳佛教的影響。
譜例5
除此之外,黑格爾、波普爾和老子的哲學(xué)思想都對(duì)相西源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產(chǎn)生過(guò)重要影響。音樂(lè)不同于雕塑、繪畫等其他藝術(shù)形式的重要一點(diǎn)便是其更注重表達(dá)精神層面的內(nèi)容,黑格爾認(rèn)為:“音樂(lè)形成了一種表現(xiàn)方式,其中心內(nèi)容是主體性的,表現(xiàn)形式也是主體性的……音樂(lè)不用客觀事物的形象,只表現(xiàn)內(nèi)心生活,也只訴諸內(nèi)心生活。……音樂(lè)不能像造型藝術(shù)那樣讓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外形變成獨(dú)立自由而且持久存在的”②,老子主張“無(wú)為而治”“大音希聲”,這些觀念都被作曲家運(yùn)用到《第三交響曲“宗”》的創(chuàng)作中。
《宗》是相西源哲學(xué)思考的總結(jié),源于對(duì)生命本質(zhì)的思考,“宗”就是“生命之源”。相西源雖然深受藏傳佛教和中國(guó)古典哲學(xué)的影響,但《宗》并不僅僅是作曲家對(duì)藏傳佛教的教義和以老莊為代表的哲學(xué)理念的轉(zhuǎn)述,而是作曲家摒棄一切世俗雜念后,在對(duì)各種宗教思想和中西方古典哲學(xué)思想,尤其是以藏傳佛教為代表的青藏高原地域宗教思想,進(jìn)行融會(huì)貫通的基礎(chǔ)上,對(duì)人的生命本質(zhì)的冥想與深思。通過(guò)音樂(lè)與靈魂的對(duì)話,從“形而下”到“形而上”,把最樸素的音樂(lè)內(nèi)容凝練到哲學(xué)的高度。
結(jié) 語(yǔ)
相西源認(rèn)為,音樂(lè)是文化的載體,偉大的音樂(lè)都飽含文化內(nèi)涵,每一部音樂(lè)作品都是一種文化的體現(xiàn)。③相西源的大部分交響音樂(lè)作品無(wú)論在題材上還是在音樂(lè)語(yǔ)言上,都具有鮮明的青海地域特色,青海的山水、文化、民俗、音樂(lè)已深深地融入到作曲家的血液之中,高原的神秘、西海的多情、雪山的威武、草原的曠達(dá),構(gòu)成了獨(dú)具青藏高原精神與地域文化的音樂(lè)風(fēng)格。相西源的交響音樂(lè)不僅體現(xiàn)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征,還是東西方文化碰撞的結(jié)果,他用專業(yè)的作曲技術(shù)把具有東方韻味和青藏高原地域特征的音樂(lè)元素轉(zhuǎn)化為自己的音樂(lè)語(yǔ)言,也體現(xiàn)出“技術(shù)”為“音樂(lè)”服務(wù)的創(chuàng)作宗旨。相西源的交響音樂(lè)不僅含有豐富的創(chuàng)作技術(shù),藝術(shù)格調(diào)高雅,而且整體曲風(fēng)淳樸深摯、優(yōu)美抒情,符合聽(tīng)眾(尤其是西北地區(qū)民眾)的審美習(xí)慣,可謂雅俗共賞。通過(guò)將專業(yè)創(chuàng)作技法與中國(guó)民族文化(特別是青藏高原地域文化)加以有機(jī)地融合而形成的地域性風(fēng)格是相西源交響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其作品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萬(wàn)字符“卍”,藏語(yǔ)稱作“雍仲”,是雍仲本教(藏傳佛教的源頭)的
吉祥標(biāo)志,在青藏高原的寺院、民居、服飾等方面使用十分廣泛。
② 黑格爾《美學(xué)》(第三卷·上冊(cè)),朱光潛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4年版,第330頁(yè)。
③ 王珂琳《中國(guó)東方神韻的交響性表達(dá)——析相西源〈第三交響曲“宗”〉的創(chuàng)作特色及內(nèi)涵》,《中國(guó)音樂(lè)》2013年第3期。
(項(xiàng)目基金:星海音樂(lè)學(xué)院2017年度“創(chuàng)新強(qiáng)校”科研類重大項(xiàng)目“當(dāng)代廣東作曲家群體及其作品研究”。)
楊正君 博士,《星海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執(zhí)行副主編
(責(zé)任編輯 張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