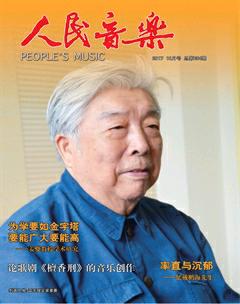戴鵬海教授與“三合一”的情緣
2017年6月25日,從一個老師也是摯友的微信空間看到上海音樂學院資深教授、音樂學家戴鵬海先生因病在紐約皇后醫院逝世,深感震驚和悲痛!剎那間,戴老對武秀之教授“三合一”事業的無私支持以及在河南期間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在腦際中躍然而出,仿佛就像昨天剛剛發生的事情。
說起和戴老的緣分,還得從武秀之教授的“三合一”說起。那是1995年,武秀之教授為了更好地進行民族聲樂和歌劇音樂劇的教學、科研、創演實踐,與慕名而來的歌劇音樂劇理論家居其宏教授一起帶領我們河南大學1992級民族歌劇畢業班(我本人當時就是該班畢業生)以及1995級在校民族歌劇班從開封奔赴鄭州西郊馬寨經濟開發區,成立“武秀之藝術教學研究實習實驗基地”,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創業生涯,居其宏教授也與我們一起搬到馬寨長期駐扎。為了更好地培養“三合一”歌劇音樂劇表演人才、創作出優秀舞臺藝術作品,居老師動用他的人脈關系邀請一批高級專家如王安國、繆也等到馬寨講學并參與武老師的“三合一”事業,其中與我接觸最多、印象最深的就是戴鵬海教授。
一、戴老的“馬寨故事”
武老師和馬寨師生對戴老最初的了解,是從居老師口中得知的,只知道他是我國一位著名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專家。直到1998年他第一次來到鄭州西郊馬寨,我們才有幸見到他本人;更幸運的是,我秉承武老師和居老師的授意,在戴老客居馬寨的日子里,全程陪同并專門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二位領導反復叮嚀:戴老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一定要悉心照料。我既激動又膽怯地接受了任務。我的工作其實很簡單:每天早晨六點半叫戴老起床、量血壓,陪同他吃早飯,然后送他到武老師辦公處,與武老師、居老師和周雪石老師討論“三合一”教學和《中國蝴蝶》的創作問題,我在旁幫著端茶倒水,然后到里屋等著,隨時聽候幾位老師的召喚;有時會議開得晚了,我就下廚炒幾樣小菜,戴老與幾位專家喝幾杯小酒,在飯桌上繼續談藝說戲。
因為曾聽居老師說戴老對事認真,有時會發脾氣,訓起人來不講情面,所以我非常擔心照顧不周,內心充滿了忐忑。通過一個階段的陪伴,我原本忐忑的心逐漸放了下來,在馬寨師生眼中,戴老是一位可敬的長者,平日里沒有架子,和藹可親、笑容可掬。既認真又隨和,有時顯得十分可愛。比如在吃飯問題上,他認為葷葷素素都是菜,吃不完可以倒掉,唯有米飯,一粒都不可浪費。每遇此事,他必定要吟誦古人詩句“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來告誡大家,尤其把最后一句語速放慢、音調提高,以示重要;這類事例經歷多了,大家心領神會,每當戴老吟到最后一句前,在座的各位專家都會不約而同地加入進來,與他一起高聲吟誦,然后大家相視而笑,顯得開心而和諧。
1999年年初,由居其宏編劇、周雪石作曲的大型原創音樂劇《中國蝴蝶》一度創作完成,武、居兩位老師經過長時間考察和挑選,正式成立《中國蝴蝶》劇組——由上海歌劇院副院長張遠文擔任導演,山西省歌舞劇院舞蹈家岳麗娟擔任舞蹈編導,武老師特別邀請戴老親臨馬寨指導,當然也是由我負責他的全程接待。戴老對劇組人員和排練等提出不少合理化的想法和建議,也就導演和舞蹈編導發表點評意見。因為是新劇,在排練過程中需要邊探討邊磨合的狀態下進行,主創團隊成員難免會在藝術上出現不同意見,有時會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有一次爭執,張遠文導演提起行李要回上海。別看戴老是個急性子,這時卻顯得格外冷靜,力勸雙方都要心平氣和、理性思考;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大家一定要把不同意見當面說出來,進行面對面討論,相信一定能夠找到更好的處理方案。
戴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耐心勸說,頓時使爭執雙方都冷靜下來,張遠文導演當即放下行李,全身心地投入到緊張的排練中。記得有一天剛下過小雨,院里有很多積水,張遠文正在給主要演員說戲并親自做示范動作,滿地滾爬渾身被泥水濕透。這動人一幕恰被戴老和武老師看到,二人一致認為:馬寨條件雖苦,但有如此團隊,何愁此戲不成?
舞蹈在《中國蝴蝶》里占有相當的分量,在排練中是一場攻堅戰,當時,舞蹈編導岳麗娟向武老師反映,對馬寨團隊的舞蹈表演非常不滿意,不少演員無法按照她的設想將動作做到位。戴老得知后很生氣,對岳麗娟有意見,有種袒護馬寨師生的“護犢子”意味。武老師當然知道自己團隊的舞蹈基本功什么樣,也了解岳麗娟做為一個專業舞蹈家是怎么看待成品舞蹈的,同樣知道戴老對岳麗娟不滿的意圖,于是就和戴老溝通,說岳麗娟對演員不滿意完全理解,因為同學們多是戲曲出身,動作難免做不到位,岳麗娟的態度是負責任的,為了讓舞蹈達到滿意效果,她每夜會備課到深夜,甚至吃飯走路也在比劃,有時想好的動作演員做不到位而不得不重新設計動作。武老師的這番話確實打動了戴老;又通過幾天的觀察,戴老對岳麗娟的態度開始有了較大轉變。
經過大家共同努力,1999年年底音樂劇《中國蝴蝶》隆重上演,得到河南省委省政府、國內部分知名專家和廣大觀眾的充分肯定和認可。武老師和馬寨團隊都知道,其中也浸透了戴老的心血和智慧。
二、戴老的西亞斯之行
為了更好地發展“三合一”事業,武、居兩位老師經過多方面考察和比較,于2002年毅然作出抉擇,率領“三合一”團隊離開馬寨,來到位于新鄭市區的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找到了一個新的發展平臺,西亞斯理事長陳曉純博士經過四年誠懇邀請,承諾要把“三結合”專業推向一個新的發展水準,為此成立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歌劇專業,后來又創建了“歌劇音樂劇學院”。在這個決策過程中,戴老一直關心“三合一”的前途,經常打電話給武老師,探討專業隊伍的建設和《中國蝴蝶》的修改,并提出過不少建議。
2004年5月,經修改加工過的《中國蝴蝶》在西亞斯羅馬劇場舉行匯報演出。戴老和居其宏、周雪石老師都來了,戴老還邀請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劇系主任、作曲家金復載一起來河南,這是戴老首次光臨西亞斯國際學院。我當然也是全程陪同。
觀看新版《中國蝴蝶》演出后,舉行了專家座談會,對該劇在創作、表演上的成敗得失進行評估,戴老的發言,充分肯定了新版的進步,但也提出一些修改建議。之后,其他專家紛紛返回,唯獨戴老主動留下,就關系到“三合一”未來發展的兩個重大問題與武老師做了連續一周的促膝長談。endprint
戴老認為,“三合一”所具有的綜合性優勢來源于一個基礎,這就是“三合一”的主要生源是戲曲演員,這就為唱法上的“三合一”發展為歌唱、舞蹈、表演的“三合一”奠定了基礎。如今,由于受教育主管部門的招生制度所限,導致戲曲生源逐年減少,師生復合型表演技能嚴重下降,將不利于“三合一”的未來發展和提高。鑒于這種招生制度一時難以改變,戴老建議,應當增加戲曲表演課程,聘請戲曲表演專業教師,對青年教師和學生進行戲曲“四功五法”的系統訓練。戴老的這一建議,當即被武老師采納,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戴老還和武老師商議,如何通過三組演員把西洋歌劇《茶花女》、原創豫劇《走出一線天》和音樂劇《中國蝴蝶》這三種不同風格的戲演好,條件成熟時舉行匯報演出,在全國同行面前檢驗“三合一”的教學成果。兩人連續幾天就這個問題的方方面面,從每部戲主要演員的選定,到排練和匯報演出時間的安排,都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討論。可惜,當時因豫劇大師常香玉病重,在彌留之際想見武老師一面。戴老知道情況后,執意要告別回滬,兩位老師的討論不得不就此中止。我當即安排了車,送戴老到火車站,就此揮手作別。
三、戴老的“蝴蝶”情結
2008年,首屆中國校園戲劇節在上海舉行,河南選派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歌劇音樂劇學院創制的音樂劇《中國蝴蝶》參演。武老師因健康原因未能率團來滬,特地打電話給戴老,拜托他對劇組在上海的演出及專家座談多予關照。
戴老將《中國蝴蝶》來滬演出的消息看作是一件大喜事,立即以主人翁姿態主動承擔起組織聯絡的責任,積極跑前跑后,邀請朱踐耳、何占豪、陸在易、朱世瑞等作曲家觀看演出并出席劇目創演座談會;戴老親自坐鎮,做了熱情洋溢的發言,對改版后的《中國蝴蝶》給予高度肯定和認可,到會專家也紛紛對《中國蝴蝶》的演出成功表示由衷的祝賀,給劇組主創團隊和參演師生以極大的鼓勵。
此后的十余年間,戴先生與武秀之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始終如一地關心、愛護《中國蝴蝶》的演出和“三合一”事業的發展。即便在移居美國之后,戴先生仍常常通過國際長途與武秀之聯系,了解“三合一”和《中國蝴蝶》的每一項進展,為其未來前景出謀劃策。大約兩年前,他在電話中對武老師說:“我來美國之后,靜下心來仔細好好地想了想,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好的音樂劇之一就是《中國蝴蝶》。你們一定要記住,想辦法把《中國蝴蝶》推出去,推向世界舞臺。它表現的是永恒的主題具有國際意義。在我們中國,是梁山伯與祝英臺;在西方國家,則有羅密歐與朱麗葉。我們的故事、音樂和表演都有特色,在世界任何地方演出都會受歡迎,因此一定要深加工,提高質量,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中國氣派和‘三合一風范。”武老師聽了,十分感動,將戴老的囑咐、鼓勵和鞭策看作是對“三合一”事業和《中國蝴蝶》今后努力、前進的方向。
戴老和武老師當初議定的由三套班子演出三部不同風格劇目的設想,如今在武老師的帶領下有了新的發展——從“三合一”到“一演三”,即由同一團隊在一天內連續演出西洋歌劇《茶花女》、豫劇《走出一線天》、音樂劇《中國蝴蝶》這3部風格迥異的大戲,并于2016年12月24日在鄭州成功上演,國內一些專家同行觀摩之后都激動不已,認為這是舞臺戲劇和表演藝術上一個罕見的奇跡!可惜,當時戴老身居異國且病情加重,無法親臨現場指導,令武老師以及我們“三合一”團隊的每個人都感到遺憾。今天,倘若戴老天上有知,也會為此而感到由衷欣慰的吧。
近二十年來戴老多次來河南都由我陪同和接待,彼此既是師生,也是忘年之交,我從他那里學到了如何對待藝術,如何待人處世,老人家永遠是我心中的楷模。
安息吧,尊敬、慈祥的戴老,我和武老師“三合一”團隊的每個人永遠想念您!
趙獻軍 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歌劇音樂劇學院聲樂講師
(責任編輯 榮英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