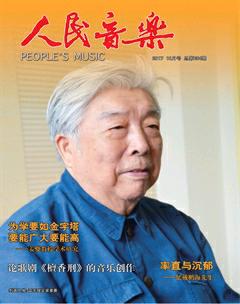“古苗疆走廊”上的漢傳音樂文化敘事
年來,關(guān)于“古苗疆走廊”多有討論,作為“走廊學(xué)”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學(xué)者們從概念的提出,到歷史演進(jìn)、制度、市場(chǎng)、教育、文化以及西南地區(qū)非漢族群的“國(guó)家化”“內(nèi)地化”、族群性、區(qū)域性等內(nèi)涵,再到這一走廊在當(dāng)下“一帶一路”海外文化走廊視角下的現(xiàn)實(shí)意義等等均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學(xué)術(shù)探討。{1}龍曄生曾談到:“這條走廊從一開始就是在國(guó)家先軍事后政治再文化等外力介入下,以驛道為中心,在文化上形成既有族群多樣性,又具有地域共性,并在沿線保留了歷史積淀的、呈帶狀相連的區(qū)域。”{2}筆者以為,如果說國(guó)家軍事、政治治理開辟和穩(wěn)固了“走廊一線”的話,那么,真正使當(dāng)?shù)胤菨h族群由“苗”而“民”,其文化認(rèn)同由“疆域”而“版圖”以及西南地域“一體多元”文化網(wǎng)狀格局的形成,應(yīng)是古代中華文化在該區(qū)域傳播、滲透、交融、接納以及融合的結(jié)果。
從文化傳播及其“空間結(jié)構(gòu)”來看,“古苗疆走廊”的開辟對(duì)西南地區(qū)民族遷徙及其分布格局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曹端波從市場(chǎng)體系的角度分析了貴州地區(qū)“民族經(jīng)濟(jì)圈”的特點(diǎn),{3}楊志強(qiáng)探討了“古苗疆走廊”和明清時(shí)期國(guó)家整合之間的關(guān)系,{4}田書青梳理了明清之際貴州進(jìn)士的分布特點(diǎn)以及“古苗疆走廊”對(duì)其的貢獻(xiàn),{5}而吳正彪則分析了古驛道上“跨族性”的語言共享——族際互動(dòng)與語言接觸。{6}上述研究表明,“古苗疆走廊”帶動(dòng)的是整個(gè)西南地區(qū)的文化振動(dòng)和歷史變遷,正如楊志強(qiáng)對(duì)廣義“古苗疆走廊”的定義:它包括了“由云南昆明經(jīng)曲靖、沾益過貴州威寧、畢節(jié)、赤水至四川瀘州下長(zhǎng)江的‘西線、由水西奢香夫人開辟的‘龍場(chǎng)九驛、徐霞客從廣西進(jìn)入貴州的‘南線以及貴陽經(jīng)遵義至四川綦江的‘北線,水路還可以將清水江、都柳江、烏江流域的河道等包括進(jìn)去”,{7}這里討論的漢傳音樂正是在這一“空間結(jié)構(gòu)”中的文化敘事。
一、“古苗疆走廊”上的禮樂教化及用樂
音樂學(xué)者項(xiàng)陽的研究表明:“中國(guó)音樂文化傳統(tǒng)在歷史上有著整體一致性,而這種整體一致性來源于制度上的機(jī)構(gòu),其本體核心是律調(diào)譜器。”{8}有明以來,西南苗疆大力推進(jìn)土司制度,或改土歸流,興辦儒學(xué),推動(dòng)了西南苗疆官府禮樂和民間禮俗用樂在律、調(diào)、譜、器等方面與古代宮廷禮祭用樂和宴享用樂的一致性。
明代苗疆興辦儒學(xué),主要采用特恩、歲貢、選貢等辦法招收土司子弟進(jìn)行教化,其課程分為“禮、樂、射、御、書、數(shù)6科,學(xué)生專修1科”。{9}儒學(xué)的興辦和教化使得西南苗疆“文士濟(jì)濟(jì)”,《赤雅》(卷下)載:“予游諸夷,有搞文而宗淮南者,有稱詩(shī)而薄少陵者……于戲!禮失而求諸野。”至明末清初,滇東地區(qū)“禮樂頗盛”,順治時(shí)人陳鼎《滇黔土司婚禮》載:龍氏其族“通漢書漢語者十九,而秉周制,翩然風(fēng)雅,浸浸乎禮樂之鄉(xiāng)矣”。
貴州石阡明初設(shè)立儒學(xué),禮儀用樂漸次深入當(dāng)?shù)胤菨h群體之中,并依附于民間戲劇——木偶戲的演繹教化民眾。流傳在石阡的木偶戲唱腔曲牌有[大漢腔][小漢腔][鎖南枝][柱云飛]和[風(fēng)云松]等。{10}石阡木偶戲傳自辰河高腔,在辰河高腔中,業(yè)界有“四宮八調(diào)”之說,其中“八調(diào)”即為曲牌基本調(diào)的八種母曲,分別是[風(fēng)入松][駐云飛][鎖南枝][紅衲襖][錦堂月][漢腔][新水令]和[漢入松],{11}這些曲牌均與《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中的曲牌有關(guān),其中大小[漢腔]出自其中的佛曲,[鎖南枝][柱云飛]出自其中的宋元南戲,[風(fēng)入松]出自其中的唐宋詞曲。{12}《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系乾隆六年(1746年)下詔開律呂正義館,編纂《律呂正義》(后編)時(shí)同時(shí)編纂的,《律呂正義》屬于清朝宮廷雅樂制度的經(jīng)典,而《九宮大成》則是燕樂音樂的曲譜集,當(dāng)時(shí)的編纂者周祥鈺序言中說:“因念雅樂、燕樂實(shí)相為表里……乃新定《九宮大成》。”{13}
宮廷禮樂亦在“古苗疆走廊”的末端昆明地區(qū)的武定祿勸彝族土司王府的禮儀儀式中上演。據(jù)記載,祿勸彝族土司最有代表的是鳳氏土司,鳳氏土司最盛時(shí)期是明朝正德到嘉靖年間,“以鳳氏為首的土司們聘漢儒為師,習(xí)六藝,衣服冠帶如漢儀,喪葬多如漢禮。”{14}祿勸彝族土司府設(shè)有專門的樂工,改土歸流前的土司府禮儀樂隊(duì)有16人之多,其禮儀用樂有曲牌曲八十多首、枝調(diào)曲49首、本枝小調(diào)18首。“這些樂曲,從曲牌曲的名稱來看都是中原的漢文化,一些樂曲名稱來源于唐、宋、元、明、清歷代使用的詞曲牌,如[雁兒落][雁兒合][雁兒落大枝][朝陽歌][朝天子][小鷓鴣][桂枝香][傍妝臺(tái)][哭皇天]等。一些樂曲與中原的鼓吹樂、吹打樂樂曲同名,如:[將軍令][水龍吟][大開門][小開門][沽美酒][鎖簧枝]等。一些樂曲則是明、清以來的時(shí)令小調(diào),如[鬧元宵][倒垂簾][春臺(tái)][五買酒]等。”{15}
然而上述土司府禮儀用樂并非僅僅只是曲牌名稱相同,而是在樂曲結(jié)構(gòu)、音階、調(diào)式、落音、旋律架構(gòu)等方面均有較多的一致性,現(xiàn)僅以該土司府曲牌[朝天子]與乾隆下旨新撰丹陛大樂《御制律呂正義后編》的欽頒導(dǎo)迎大樂比較說明(譜例1:祿勸[朝天子];譜例2:欽頒導(dǎo)迎大樂)。
上述兩曲至少存在三個(gè)主要相似點(diǎn):其一是兩個(gè)樂曲的起句幾乎完全相同;其二,兩個(gè)樂曲前半部分的調(diào)性質(zhì)和落音結(jié)構(gòu)基本相同;其三是兩個(gè)樂曲的音階完全一樣,均為la 、xi、do、re、mi、sol、la的帶變宮的六聲音階。[朝天子]是唐代教坊樂曲名,用作“詞調(diào)名”,據(jù)《清朝文獻(xiàn)通考》記載:“國(guó)初教坊司樂,凡筵宴進(jìn)果,丹陛樂奏《喜得功名》;進(jìn)酒,丹陛樂奏《朝天子》。”{16}作為一首宮廷宴享、禮儀樂曲,在遠(yuǎn)離王朝的云南土司王府上演,并在用樂的本體特征上如此相似,原因何在?在筆者看來,這種相似性絕非偶然,“古苗疆走廊”的開通使得西南各族群的國(guó)家認(rèn)同意識(shí)不僅沉淀在他們的心理結(jié)構(gòu)之中,而且還通過禮儀的儀式及其用樂的一致性彰顯出來。
二、“古苗疆走廊”上漢傳民歌母曲——趕馬調(diào)
民族音樂學(xué)的調(diào)查研究表明:趕馬調(diào)是貴州地域上廣泛流傳的民歌曲調(diào),是穿行在“茶馬古道”上的“馬幫”創(chuàng)用的一種民歌體裁,由于其適用場(chǎng)合、流傳范圍廣,往往被統(tǒng)稱為“貴州山歌”。“茶馬古道”是指在中國(guó)以馬或者其他牲口為主要交通工具的陸路商貿(mào)通道,隨著學(xué)界對(duì)“茶馬古道”研究的深入,穿越貴州的“茶馬古道”也在諸多文獻(xiàn)中零星出現(xiàn),包括貴州南部的百越古道、廣西經(jīng)獨(dú)山至貴陽的古道貴陽經(jīng)遵義至綦江的古道。其中橫穿貴州中部至湖廣的商貿(mào)通道,幾乎與“古苗疆走廊”重疊,現(xiàn)今湖南安化還有眾多馬幫后代,據(jù)調(diào)查,他們的先輩往往放棄沅水、清水江、舞陽河等水道,沿武陵山陸路進(jìn)入貴州進(jìn)行商貿(mào)交易。“古苗疆走廊”開通后,國(guó)家在貴州推進(jìn)商屯、民屯政策,一部分馬幫因而在當(dāng)?shù)刂玫囟ň酉聛恚D(zhuǎn)商為農(nóng)。由之,趕馬調(diào)這一流動(dòng)在馬道上的山歌小調(diào),便也隨著“馬幫哥”生產(chǎn)行為方式的轉(zhuǎn)變而“定居”下來,轉(zhuǎn)變?yōu)檗r(nóng)事生產(chǎn)的薅秧歌、打柴歌、墾荒歌、薅草歌,甚至是婚俗歌、酒歌、情歌等。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貴州學(xué)者王立志的調(diào)查研究提供了例證。endprint
王立志曾對(duì)貴陽地區(qū)的趕馬調(diào)進(jìn)行了較為詳細(xì)的調(diào)查和研究,得出了趕馬調(diào)是貴州高原漢傳民歌母曲的結(jié)論。{17}他認(rèn)為,趕馬調(diào)的傳統(tǒng)母曲情緒開朗、曲調(diào)樸質(zhì),帶有念唱性質(zhì),四句體曲調(diào),純五度音域,sol、la、do、re四聲徵調(diào)式。譜例如下:
“馬幫哥”沿“古苗疆走廊”屯田定居下來后,由于地域環(huán)境、勞動(dòng)方式以及民族接觸的不同,趕馬調(diào)出現(xiàn)了諸多變異,并在不同非漢群體中流傳,形成了“古苗疆走廊”各族群共同認(rèn)同的“山歌共同體”。王立志調(diào)查和分析了貴陽地區(qū)漢民族趕馬調(diào)的變體情況:1.旋律曲調(diào)變得流暢優(yōu)美,使得趕馬調(diào)從念唱的形式中解脫出來;2.曲調(diào)變長(zhǎng)或縮短,小節(jié)數(shù)增加或減少,小節(jié)中拍數(shù)增加,出現(xiàn)變拍子;3.曲調(diào)的節(jié)拍出現(xiàn)三拍子,沖破節(jié)拍單一性的母曲;4.曲調(diào)的音域擴(kuò)展到六、八度;5.曲調(diào)調(diào)式產(chǎn)生變化;6.曲調(diào)結(jié)構(gòu)由四句變?yōu)閮删洌褑螖?shù)句歌詞緊縮在兩小節(jié)中,而在雙數(shù)句歌詞上以一個(gè)主音的自由拖腔,使曲調(diào)前緊后松的特點(diǎn)更為突出;7.曲調(diào)改變拖腔的音級(jí),用宮音或者徵音拖腔;8.角音進(jìn)入,曲調(diào)變?yōu)槲迓曇綦A;9.曲調(diào)在中間加入新的樂段,如夾垛等。
“馬幫哥”的定居與當(dāng)?shù)氐姆菨h族群產(chǎn)生了長(zhǎng)期且較為固定的接觸,作為一種族際交流的文化媒介,趕馬調(diào)逐漸在貴州高原上“網(wǎng)狀擴(kuò)散”,被當(dāng)?shù)胤菨h群體所借用,并在此過程中逐漸“族群化”,使得趕馬調(diào)再一次脫離母體,在貴州形成了一張“趕馬調(diào)山歌文化網(wǎng)”。許甜甜的田野調(diào)查和對(duì)《中國(guó)民族民間歌曲集成·貴州卷》(以下簡(jiǎn)稱《集成》)的量化分析為我們呈現(xiàn)了這樣一張結(jié)構(gòu)性的山歌文化網(wǎng)絡(luò),其分布情況如下:{18}
苗族:趕馬調(diào)涉及到苗族飛歌、游方歌、酒歌等體裁,《集成》共收錄苗族民歌288首,其中趕馬調(diào)的子體民歌曲調(diào)總數(shù)為13首,占5%,直系趕馬調(diào)3首,占該民族趕馬調(diào)子體民歌總數(shù)的25%,旁系趕馬調(diào)10首,占75%。
布依族:趕馬調(diào)涉及到布依族浪哨歌、山歌、酒歌等體裁,《集成》共收錄布依族民歌183首,其中趕馬調(diào)的子體民歌曲調(diào)總數(shù)為28首,占15%,直系趕馬調(diào)3首,占該民族趕馬調(diào)子體民歌總數(shù)的11%,旁系趕馬調(diào)25首,占89%。
侗族:趕馬調(diào)涉及到侗族“嘎拜今”(山歌)、“阿外炎”(玩山歌)、婚俗歌、佛歌等體裁,《集成》共收錄侗族民歌317首,其中趕馬調(diào)的子體民歌曲調(diào)總數(shù)為17首,占5%,直系趕馬調(diào)1首,占該民族趕馬調(diào)子體民歌總數(shù)的6%,旁系趕馬調(diào)16首,占94%。
土家族:趕馬調(diào)涉及到土家族山歌、禮俗歌等體裁,《集成》共收錄土家族民歌129首,其中趕馬調(diào)的子體民歌曲調(diào)總數(shù)為14首,占11%,直系趕馬調(diào)2首,占該民族趕馬調(diào)子體民歌總數(shù)的14%,旁系趕馬調(diào)12首,占86%。
彝族:趕馬調(diào)涉及到彝族“曲各”“阿碩”等體裁,《集成》共收錄彝族民歌232首,其中趕馬調(diào)的子體民歌曲調(diào)總數(shù)為55首,占24%,直系趕馬調(diào)1首,占該民族趕馬調(diào)子體民歌總數(shù)的2%,旁系趕馬調(diào)54首,占98%。
仡佬族:趕馬調(diào)涉及到仡佬族“勾朵以支豆”(勞動(dòng)山歌)、“勾朵以”(山歌)、“達(dá)以”(情歌)、“哈祖阿米”(禮俗歌)、“達(dá)以萊諾”(祭祀歌)等體裁,《集成》共收錄仡佬族民歌186首,其中趕馬調(diào)的子體民歌曲調(diào)總數(shù)為28首,占15%,直系趕馬調(diào)8首,占該民族趕馬調(diào)子體民歌總數(shù)的29%,旁系趕馬調(diào)20首,占81%。
上述有關(guān)趕馬調(diào)在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等民族中的流布,從一個(gè)側(cè)面說明了貴州高原民族文化的“區(qū)域性結(jié)構(gòu)”特征以及各民族族群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
如果再?gòu)牡乩砜臻g考察趕馬調(diào)的分布及其密度,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趕馬調(diào)主要分布在威寧、納雍、赫章、大方、石阡、黎平、天柱、獨(dú)山、荔波、晴隆、水城、貴陽等縣市。這一空間分布特點(diǎn)說明了趕馬調(diào)的流播和民族間的融合與廣義上的“古苗疆文化走廊”有關(guān),其中威寧、納雍、赫章、水城屬于廣義“古苗疆走廊”的“西線”,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這條線上曾設(shè)“烏撒衛(wèi)”治理威寧;石阡、晴隆、貴陽則在“古苗疆走廊”的主干道上;黎平、天柱處在清水江、都柳江流域,明代即在此地開辟了五開衛(wèi)(洪武十五年)、天柱千戶所(洪武二十五年);大方則是明代“水西九驛”的必經(jīng)之路;獨(dú)山、荔波自古就是貴州通往粵桂的“販馬道”。
三、“古苗疆走廊”上的漢傳戲劇文化
在現(xiàn)今的云貴高原上灑落著眾多民間戲劇文化,這些民間戲劇多數(shù)屬于漢傳戲劇,在明清一帶沿著連接域外的東、南、北向通道流入西南。考察相關(guān)文獻(xiàn)和田野調(diào)查的資料顯示,如果以江南、中原民間戲劇文化為參照,那么,流入云貴高原的民間戲劇在傳播形式上可以分為“流播”和“借入”兩種類型,并在本體特征上表現(xiàn)出來,以下僅以地戲、花燈戲、侗戲的音樂唱腔說明之。
(一)地戲
地戲主要流傳在貴州安順一帶。對(duì)于地戲的來源,庹修明的觀點(diǎn)非常明確:“地戲?qū)儆谥袊?guó)軍儺”。{19}他提出貴州地戲與一則文獻(xiàn)相關(guān):“桂林儺隊(duì),自承平時(shí)名聞京師,曰:靜江諸軍儺”,并認(rèn)為儺文化的主體本是中原文化,早在明軍里盛行的軍儺和中原民間傳承的民間儺,隨明代南征軍和移民進(jìn)入貴州,與當(dāng)?shù)氐拿袂椤⒚袼捉Y(jié)合,就形成了以安順為中心的貴州地戲。貴州地戲傳入貴州一帶的傳播路線“基本上或主要是沿著南征軍的行軍路線及屯田駐軍分布的,呈現(xiàn)明顯的帶狀結(jié)構(gòu)。”劉懷堂不贊同的庹修明的“軍儺說”,但他同樣認(rèn)為,貴州地戲與明清時(shí)期貴州的軍屯、民屯有關(guān),他認(rèn)為,“早期的地戲是明代寓兵于農(nóng)的兵屯產(chǎn)物”。{20}
貴州地戲是江南戲劇文化在貴州的“流播”,是當(dāng)時(shí)漢民族群體在異地生存的一種主體性自為行為。關(guān)于貴州地戲與江南內(nèi)地明清時(shí)期音樂文化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我們可以從傅利民的調(diào)查研究中管窺一二。
傅利民認(rèn)為,貴州地戲在唱腔音樂方面是江西弋陽腔的“活化石”。{21}首先,地戲傳承了弋陽腔高腔“錯(cuò)用鄉(xiāng)語、改調(diào)歌之”的創(chuàng)腔辦法,曲牌聯(lián)綴為音樂結(jié)構(gòu),通過各種具有相對(duì)獨(dú)立性的曲牌聯(lián)綴,不同地方用地方方言演唱,曲調(diào)來自于當(dāng)?shù)氐拿窀琛⑿≌{(diào)等;其次,地戲繼承了弋陽腔“一人唱而眾人和之”的徒歌形式,進(jìn)而發(fā)展成幫打唱三者結(jié)合的表演形式;第三,地戲與弋陽腔還有一批同名的傳統(tǒng)劇目,如《楚漢相爭(zhēng)》《三國(guó)》《封神》《東周列國(guó)》《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薛剛反唐》《三下河?xùn)|》等等;第四,地戲中使用的與弋陽腔同名的曲牌“在旋律、音調(diào)上還是能看出他們的同宗性”,繼承了弋陽腔旋律級(jí)進(jìn)、五聲音階、羽徵調(diào)式的傳統(tǒng),如地戲《說岳》中“陸文龍雙槍戰(zhàn)五將”中的唱腔就是這種特征:endprint
在地戲的發(fā)展過程中,由于屯田的漢民與當(dāng)?shù)夭家雷宓纳a(chǎn)生活接觸,地戲逐漸傳入布依族族群中。但是據(jù)肖可研究,這種跨族際的傳播經(jīng)歷了一個(gè)漫長(zhǎng)的過程:“在明代,屯堡人與黔中各少數(shù)民族基本上是處于嚴(yán)重軍事對(duì)抗中……雖然屯堡地戲被周邊的布依族時(shí)常接觸,但是不會(huì)被引進(jìn)布依族村寨中,也不會(huì)被布依人所認(rèn)可。”“入清以后,作為明王朝的遺民,屯堡人原先高尊的身份和地位開始跌落……這樣就為屯堡地戲進(jìn)入布依族村寨提供了情感基礎(chǔ)。”同時(shí),肖可的研究還呈現(xiàn)了這種文化接觸的特點(diǎn):首先,布依族地戲的劇目少于屯堡地戲的劇目;其次,地戲劇本的行文格式都是按照說唱底本的格式,布依族地戲也不例外,以七字唱詞句為主,間歇處雜以半文半白的敘述句,有時(shí)七言的唱詞也轉(zhuǎn)成五字或十字句。{22}
(二)花燈戲
花燈戲遍及云貴高原各民族中,在貴州,花燈被分為“東、南、西、北、中”五路。在云南,花燈被分為九個(gè)支系,具體為環(huán)滇池流域花燈、玉溪花燈、彌渡花燈、姚安花燈、元謀花燈、建水花燈、曲靖花燈、文山花燈以及其他邊疆地區(qū)的花燈。云貴花燈不僅流傳在漢民族族群中,而且還廣泛地流傳在不同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族群中,如貴州中路花燈還在當(dāng)?shù)氐拿缱濉⒉家雷逯辛鱾鳎F州東路花燈亦在當(dāng)?shù)氐耐良易濉⒍弊濉⒚缱濉⒇罾凶逯辛鱾鳎颇鲜〉囊Π不簟⒋笠簟⒊刍簟⒌撠S花燈由于受到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影響,保留的民歌多,歌舞多,但卻沒有明清俗曲。
云貴花燈戲自明清時(shí)期由湖廣漢民族的花燈音樂傳入,這在各地的方志文獻(xiàn)和口傳資料中得到了較為翔實(shí)的例證,如云南環(huán)滇池流域的花燈和黔東土家族花燈即是如此。
據(jù)研究,云南環(huán)滇池流域的花燈緣起與明代沐莫平定云南有關(guān),明洪武十四年,沐莫平定云南,并派遣四五十萬內(nèi)地民眾進(jìn)入云南,實(shí)行軍屯、民屯,后來由于經(jīng)商等原因,前后進(jìn)入云南的人數(shù)約有四百萬人之眾。漢民族的進(jìn)入自然帶入了湖廣江漢一帶的民俗文化,內(nèi)地起源甚早的“村田樂”“社火”“秧歌”從明代起就在云南十分盛行。{23}
環(huán)滇池流域的花燈音樂多半來自于流傳在湖廣江漢一帶的明清俗曲。明代文學(xué)家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篇》中記載:“嘉、隆間(1522—1572),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天皇][干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絞絲]之屬……比年以來,又有[打棗干][桂枝兒]兩曲,其腔調(diào)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xí)之,亦人人喜聽之。”
黔東土家族花燈廣泛流傳在酉水流域的龍山、永順、保靖、吉首、古丈、桑植、沅陵、銅仁、江口、德江、沿河、思南、印江、石阡等地。黔東民間口傳,土家族花燈歌舞起源于唐代京都民間“燈兒戲”,并流傳有“土王娛樂”“祭祀祖先”“民俗生活”“漢族傳入”等起源說。清乾隆三十年《辰州府志》卷十四(風(fēng)俗)中記載:“元宵前數(shù)日,城鄉(xiāng)多剪紙為燈,或龍或獅,及各鳥獸狀。十歲以下童子扮演采茶秧歌諸故事。”清道光四年《鳳凰廳志》卷七(風(fēng)俗)記載:“元宵前數(shù)日,城鄉(xiāng)斂錢扮各樣花燈,為龍馬禽獸,魚蝦各狀,十歲以下童子扮演采茶秧歌諸故事。至十五夜,笙歌鼎沸,燈燭輝煌,謂之鬧元宵。”以上兩則記述說明了明清時(shí)期黔東湘西地區(qū)花燈的盛況。
熊曉輝在對(duì)黔東土家族花燈表演程序、舞蹈形式、唱詞句式、音樂形式進(jìn)行調(diào)查研究后,結(jié)合相關(guān)文獻(xiàn)和田野口述資料提出:“土家族花燈歌舞起源于北宋年間,原屬于祭祀、風(fēng)俗性歌舞,是由漢族花燈以土家族其他歌舞藝術(shù)組合并演變而來。土家族花燈最初是人們?yōu)榱蓑?qū)鬼祛病,祈福納吉的演出,后來逐漸向世俗化發(fā)展、娛人、自?shī)食煞旨訌?qiáng),至明清土司統(tǒng)治時(shí)期,花燈歌舞極盛一時(shí)。”{24}
(三)侗戲
如果說地戲、花燈戲是湖廣江南民間戲劇文化隨著漢民族在云貴高原軍屯、商屯、民屯而“流播”的話,那么侗戲就是作為非漢族群的侗民族對(duì)內(nèi)地戲劇文化的“借入”,這種文化借入與當(dāng)時(shí)侗族族群社會(huì)文化精英對(duì)內(nèi)地文化的認(rèn)同不無關(guān)系。
據(jù)侗族學(xué)者吳定國(guó)研究,侗族民間社會(huì)普遍認(rèn)為侗戲形成于1830年,由黎平縣茅貢鄉(xiāng)臘洞村吳文彩(1799—1845)所創(chuàng):“相傳,當(dāng)時(shí)漢族戲曲傳入侗族地區(qū),由于侗族人民看不懂劇情內(nèi)容,因而激發(fā)了吳文彩創(chuàng)建侗戲的念頭。他想:要是侗家能有自己的戲劇,說的是侗語,唱的是侗語,那該多好。為了實(shí)現(xiàn)這個(gè)理想,他用三年時(shí)間,嘔心瀝血地創(chuàng)作出最早的兩出侗戲,一出是根據(jù)漢族說唱本《二度梅》改編的《梅良玉》,另一出是根據(jù)漢族傳書《薛剛反唐》改編的《鳳蛟李旦》。”{25}這里所透漏的信息包括兩點(diǎn):1.侗民族族群愿意接受外來的漢族戲劇,并想通過唱詞語言的“侗化”理解其思想內(nèi)涵;2.侗戲最初在侗民族中間的“借入”,是本源性的漢族戲劇劇目的借用。馬軍在其研究中把這一時(shí)期稱之為侗戲的萌芽期。{26}
在田野調(diào)查中我們了解到,侗戲的萌芽與明末清初中原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隨著侗族地區(qū)交通的開發(fā)和城鎮(zhèn)的增加,逐漸向侗族地區(qū)滲透有關(guān)。明末清初,“漢族人口流入的增多,官府在侗族地區(qū)興辦了‘府學(xué)‘縣學(xué)‘義學(xué)‘書院等文化機(jī)構(gòu),使得在漢族地區(qū)流行的湘戲、彩調(diào)、漢劇等劇種傳入侗族地區(qū),從而使這時(shí)的‘錦(侗族民間敘事歌),終于有了向侗戲過渡的外部條件。”{27}
借用漢戲的侗戲在侗民族中萌芽之后,隨即出現(xiàn)了一個(gè)發(fā)展傳播期,正是這樣一個(gè)發(fā)展傳播的階段,不僅在侗族地區(qū)傳播了漢族歷史文化和社會(huì)文明,同時(shí)也讓侗戲逐漸民族化,使之成為名副其實(shí)的侗戲。“吳文彩先生在侗戲萌芽階段開辟了侗戲創(chuàng)作根據(jù)漢族傳奇性故事改編的先例,各地許多接受過漢文化教育的歌師戲師們,都去學(xué)習(xí)借鑒吳文彩先生的創(chuàng)作方法,創(chuàng)作改編了相當(dāng)數(shù)量的以漢族傳奇性故事為主要內(nèi)容的侗戲。如:《毛宏玉英》《劉世第》《劉高》《山伯英臺(tái)》《陳勝吳廣》《陳世美》等。”正是這些漢族劇目在侗戲中移植演出,一方面強(qiáng)化了侗民族對(duì)于漢族戲劇文化的認(rèn)同,同時(shí)又使得侗戲的藝術(shù)表演和創(chuàng)作手法逐漸成熟起來,最終使得以侗民族民間故事為內(nèi)容的侗戲劇目漸次創(chuàng)作出來。endprint
然而,就其音樂形態(tài)特征來看,其主要的技術(shù)手法仍然是以漢民族民間音樂作為主要形態(tài)行為方式,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1.盡管侗戲的唱腔可分為戲腔、哭腔、歌腔、新腔四種,但原發(fā)于漢民族戲劇的戲腔卻是侗戲的基本唱腔,是決定侗戲特色的重要因素;2.侗戲音樂的戲腔落音和結(jié)構(gòu)與湘劇、漢劇的落音原則和結(jié)構(gòu)原則同出一撤。其傳統(tǒng)唱腔由上下兩句構(gòu)成,上句落音為“商”,下句落音為“宮”,上下句的落音不是五度支架關(guān)系,而是大二度關(guān)系;3.侗戲音樂采用上下句對(duì)應(yīng)性的結(jié)構(gòu),這種對(duì)應(yīng)性結(jié)構(gòu)整體具有基礎(chǔ)意義,其它結(jié)構(gòu)性質(zhì),諸如“起承轉(zhuǎn)合”“分合”“起平落”等形式都是在此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4.盡管在現(xiàn)今的侗戲里,侗家人喜愛的特有樂器,如牛腿琴,琵琶、侗笛以及蘆笙等已經(jīng)廣泛地作為伴奏樂器。但是在戲腔里仍以二胡為主奏樂器,就其根源,這其實(shí)是侗民族的“內(nèi)地化”認(rèn)同心理所使然。
結(jié) 語
上述有關(guān)云貴禮樂文化及其用樂、趕馬調(diào)的流布及其特點(diǎn)和民間戲劇的文化敘事,實(shí)際上是對(duì)當(dāng)?shù)貪h傳音樂文化的一種總體鳥瞰。盡管論述比較簡(jiǎn)略,邏輯比較松散,但是,上述民間音樂文化的事項(xiàng)已經(jīng)較為清晰地呈現(xiàn)了西南各族群“國(guó)家化”文化認(rèn)同、“內(nèi)地化”文化認(rèn)同的心理訴求,同時(shí)亦清晰地呈現(xiàn)了“古苗疆走廊”對(duì)于西南地區(qū)非漢群體和漢民族群體的民間藝術(shù)文化整合的參照效用和粘合效應(yīng):首先,云貴高原少數(shù)民族族群中的禮樂用樂盛行于明末清初時(shí)期的土司治理時(shí)期,表明少數(shù)民族土司一方面欲以此表明“同族群內(nèi)部的君臣關(guān)系”,另一方面也要以此表明對(duì)朝廷的歸附;其次,作為馬道上流動(dòng)的山歌,盡管在“古苗疆走廊”開通之前有可能在民間自發(fā)開辟的“商道”上傳唱,但是當(dāng)它隨著“馬幫哥”定居屯田而轉(zhuǎn)變?yōu)椤稗恫莞琛薄翱巢窀琛币约啊熬聘琛薄扒楦琛辈⒈环菨h族群“借入”,卻是在“古苗疆走廊”開通之后,實(shí)行軍屯、民屯、商屯之后的事情;再次,“古苗疆走廊”的開通促進(jìn)了漢民族民間戲劇文化在西南高原的“流播”和“借用”,就其實(shí)質(zhì)而言,一方面是西南漢民文化記憶的呈現(xiàn),一方面是非漢族群國(guó)家意識(shí)的自覺,歸根結(jié)底是西南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結(jié)果。
{1} 如《廣西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刊發(fā)專欄討論“古苗疆走廊”的概念、內(nèi)涵以及當(dāng)代意義,《中國(guó)邊疆史地研究》《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也連續(xù)刊發(fā)相關(guān)文論對(duì)“古苗疆走廊”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予以推介。
{2} 龍曄生《“古苗疆走廊”研究及其現(xiàn)實(shí)啟示》,《民族論壇》2012年第5期。
{3} 曹端波《國(guó)家、市場(chǎng)與西南:明清時(shí)期的西南政策與“古苗疆走廊”市場(chǎng)體系》,《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第1期。
{4} 楊志強(qiáng)《“國(guó)家化”視野下的中國(guó)西南地域與民族社會(huì)》,《廣西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年第3期。
{5} 田書清《古苗疆走廊與貴州教育的關(guān)系》,《貴州社會(huì)科學(xué)》2013年第1期。
{6} 吳正彪、郭俊《論“古苗疆走廊”中的族群語言構(gòu)成特點(diǎn)》,《長(zhǎng)江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6年第6期。
{7} 徐杰舜、楊志強(qiáng)《“古苗疆走廊”的提出及意義》,《廣西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4年第3期。
{8} 項(xiàng)陽、張?jiān)伌骸稄摹俺熳印惫芨Q禮樂傳統(tǒng)的一致性存在》,《中國(guó)音樂》2008年第1期。
{9} 吳榮臻總編《苗族通史》(五),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410頁。
{10} 張應(yīng)華《石阡民間木偶戲常用唱腔音樂探析》,《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藝術(shù)版》2006年第3期。
{11} 馮光鈺《戲曲聲腔傳播》,華齡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頁。又見宋阿娜、熊曉輝《辰河高腔曲牌的形成、分類及表現(xiàn)形式》,《中國(guó)音樂》2014年第1期。
{12} 楊詠《江西弋陽腔曲牌分類思考》,《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年第3期。
{13} 鄭祖襄《“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詞調(diào)來源辨析》,《中國(guó)音樂》1995年第1期。
{14} 楊嘉興《武定祿勸彝族土司府禮儀樂探微》,《民族藝術(shù)研究》1995年第6期。
{15} 楊嘉興《武定祿勸彝族土司府禮儀樂探微》,《民族藝術(shù)研究》1995年第6期。
{16} 項(xiàng)陽、張?jiān)伌骸稄摹俺熳印惫芨Q禮樂傳統(tǒng)的一致性存在》,《中國(guó)音樂》2008年第1期。
{17} 王立志《貴州山歌“趕馬調(diào)”》,《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9年第4期。
{18} 許甜甜《論貴州漢族母體民歌“趕馬調(diào)”及其同宗民歌》,貴州師范大學(xué)碩士論文2014年。
{19} 庹修明《中國(guó)軍儺——貴州地戲》,《民族藝術(shù)研究》2001年第4期。
{20} 劉懷堂《貴州地戲不是“軍儺”》,《四川戲劇》2012年第1期。
{21} 傅利民《弋陽腔之活化石——貴州安順“地戲”音樂考察》,《音樂探索》2005年第3期。
{22} 肖可《從布依族地戲的分布看布依—漢的文化接觸》,《貴州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1年第4期。
{23} 方園《環(huán)滇池流域花燈音樂的文化學(xué)研究》,云南藝術(shù)學(xué)院碩士論文2014年。
{24} 熊曉輝《明清時(shí)期土家族土司花燈歌舞的表現(xiàn)形式》,《四川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第1期。
{25} 吳定國(guó)《侗戲的源流及特點(diǎn)》,《貴州文史叢刊》1992年第2期。
{26}{27} 馬軍《侗戲幾個(gè)歷史時(shí)期的劃分之我見》,《責(zé)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
張應(yīng)華 博士,湖南第一師范學(xué)院教授
(責(zé)任編輯 劉曉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