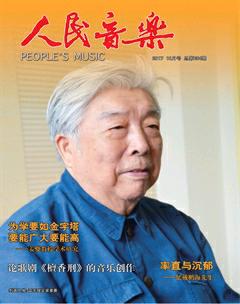2000—2015:觀念與描述
孫絲絲++柯雅杰
緣 起
“西方音樂史”是以我國音樂學研究為基本語境命名的一門研究西方音樂的學科,除與西方“歷史音樂學”有相同的學科宗旨和研究內容外,其研究方法也受到了學界的長期關注,同屬“西方音樂史”學科的研究范疇。為了厘清經上世紀幾十年的發展后,21世紀我國學者們在該領域的學術研究中做出了哪些有意嘗試、體現出怎樣的發展趨勢、學科意識和觀念等問題,筆者對2000年至2015年間《音樂研究》《中央音樂學院學報》《音樂藝術》《中國音樂學》《黃鐘》《中國音樂》《人民音樂》《天籟》《交響》《音樂探索》《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樂府新聲》《星海音樂學院學報》《音樂創作》14種音樂期刊中發表的322篇有關西方音樂研究的論文進行分析,并將其內容分為六大類別之后發現:在橫向共時性研究方面,作曲家(作品)研究和西方音樂史史學研究(包含史學方法、斷代史研究和專題史三個方面)占據了全部研究成果的75%(圖1);在縱向歷時性的斷代史研究中,“20世紀”的關注度最高(圖2)。因此,筆者將作曲家(作品)研究、史學研究、20世紀作為21世紀初期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重點論域,并以歷史性描述、宏/微觀描述、開放性描述為視角進行討論和審視。
圖1
圖2
一、歷史性描述:作曲家(作品)研究
西方歷史音樂學研究發展到今天早已形成以作曲家與作品研究為主要導向的學術審視和音樂史言說{1},但隨著上世紀90年代“新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興起和影響,音樂學家在作曲家及作品解讀方面也開拓了諸多維度:如約瑟夫·科爾曼的“批評性(criticism)傾向”、利歐·特萊特勒 “歷史評論”、蓋瑞·湯姆林森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理論{2}……在這些思想的引領下,我國學者逐漸將研究視角放入到空間更廣闊的歷史性層面中,尋求作曲家(作品)背后的隱性人文內涵。
楊燕迪教授的《音樂作品的詮釋學分析與文化性解讀——肖邦〈第一即興曲〉作品29的個案研究》{3}是這類研究的代表。他旨在討論個案分析時所應有的思維格局:“在不降低應有的‘專業性和‘技術性的基礎上,強化和凸顯其內在的‘人文性與‘文化性。”{4}作者既高屋建瓴地指出音樂意義的生成通道,又腳踏實地地詳細分析樂譜,并進行了作品立意、社會-歷史意義和精神啟示三個方面的文化性解讀,這一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個案寫作探討為作品的深入闡釋提供了絕佳思路。姚亞平教授的《修辭:音樂突圍的謀略——歐洲音樂的藝術化傾向如何從教堂禮拜中產生的觀察與分析》{5}雖在題目中不涉及任何作曲家或作品,但卻以具體樂譜為例,分析、論述了從格里高利圣詠到附加段、繼續詠、奧爾加農再到經文歌這一系列轉變背后的原因和歷程,揭示在宗教體制籠罩下創作者 “另辟蹊徑”的靈感顯現,從而使音樂創作逐漸走出宗教藩籬最終獲得廣闊空間的歷史歷程。
將目光轉向歷史人物的日記、回憶錄、書信、生前故事、傳說,在“歷史的垃圾箱拾撿珍寶”的做法,也是歷史性描述的研究方式{6}。如郭小蘋的《勃拉姆斯的性格特點及其音樂創作》{7}便參考了《勃拉姆斯的生活與信件》和《勃拉姆斯的生活》等重要資料,依據勃拉姆斯童年到青年時期各種實例從心理學的角度對其性格進行了總結,分析“戀母情結”“偶像情節”在其作品中的展現;劉瑾的《埃里克·薩蒂的早期生活經歷與音樂創作》{8}充分分析了哥特式建筑、繼母、作曲家依格涅·巴娜舒赫和叔叔埃德里·薩蒂以及作家安徒生對薩蒂的種種影響,探討早年生活經歷對他一生音樂風格所起到的不可磨滅的作用。
借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對作曲家(作品)進行歷史性解讀,是自2000年來較為“時髦”的視角。如李小兵等所著的《從宮廷音樂家到自由音樂家——17至19 世紀活躍在奧地利的音樂家之社會經濟地位變遷闡析》{9},以社會經濟地位變遷的角度,分析古典主義三杰的生存狀態、經濟狀況,如海頓在宮廷任職同時出售自己作品的“腳踩兩只船”現象、莫扎特較高的收入水平(作者以此來更正音樂史中他“向來”窮困潦倒的傳聞)、貝多芬與出版商之間精明的利益合作等,詳細闡明音樂家在社會環境影響下身份轉變的過程。宋方方以女性主義視角審視了作曲家范尼·門德爾松和克拉拉·舒曼的艱難處境{10},她在社會文化的角度中尋找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了兩位天才級女性創作者沒有達到類似男性作曲家的社會地位和聲望。上述文章中沒有出現任何的樂譜分析,但卻通過對作曲家本人各角度的考證和描述,達到了分析、研究作曲家的目的。這充分說明 “音樂的構成遠不止于譜面上的音符或錄音中聽到的音響,音樂是時代和情景的產物,音樂的形成也離不開構建它的人和社會建制”{11}。
二、宏/微觀描述:史學研究
史學研究是歷史音樂學的學術重陣,在我國21世紀以來的西方音樂史學研究中也占具重要地位,它可分為宏觀和微觀研究兩種層面。
宏觀研究即對西方音樂史學研究方法與范式的探討,當今中國西方音樂史學界幾位領軍人物都對此進行了深入研討。楊燕迪教授的《音樂與文化的關系解讀:方法論范式再議》{12}討論了包括西方音樂史學在內的有關音樂研究的方法,并將音樂置于在文化中(in culture)、作為文化(as culture)和即是文化(is culture)三種范式的研究思路中;他的《再議中國的西方音樂研究:當前處境與學科愿景》{13}以國內社會音樂生活狀況為背景,鼓勵寫作高質量綜論性著譯來提升西方音樂研究的整體品格。兩篇文章在思維方式、學科路向方面為中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指出了方向。姚亞平教授的《西方音樂歷史編撰學的傳統與創新》{14}和孫國忠兩位教授《當代西方音樂學的學術走向》{15}均以實證主義開篇,探討“新音樂學”這一研究方法。前者以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二元對立現象入手,闡釋它們的核心思想及相互靠攏時所出現的新風貌,引出對“新音樂學”的討論與思考;后者則在開篇指出“將研究對象置于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進行探究乃是當代音樂學在西方的基本學術走向”,引出對“新音樂學”中女權主義批評的詳細闡發。孫國忠教授還以《西方音樂史學:觀念與實踐》{16}《西方音樂史研究:學術傳統與當代視野》{17}兩文探討了歷史音樂學從通史到專題史、從實證主義到新音樂學、從自律性分析到批評性詮釋的發展過程,并論及在新學術語境中學者應有的學術品格。他的《尊重學術傳統 再思研究路徑——就“中國視野的西方音樂研究”之相關問題答葉松榮教授》{18}是針對葉松榮教授之觀點的商討。葉教授在2010、2013年于《音樂研究》中撰文兩篇深入探討西方音樂史研究“中國視野”的核心要義{19}闡釋在這一觀念下進行研究的學術觀點、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西方音樂史學科的理論構想以及擁有屬于自身話語體系的學術地位的思考。在這些學者各抒己見之時,以班麗霞{20}、劉小龍{21}為代表的青年學者也對該議題頻頻發聲,探索中國人研究西方音樂的路徑,體現出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endprint
微觀研究是對某一具體問題的研究與考察,有橫向和縱向兩種研究路向之分。橫向研究是對某歷史時期或其中某一問題的探討(作曲家與作品研究除外)。于潤洋先生的《浪漫主義音樂——為〈音樂百科全書〉詞條釋文而作》{22}一文是橫向研究的典范。他從社會文化背景入手,闡釋了浪漫主義音樂在情感、民族、體裁等方面的特點及發展情況,以極具個人色彩的學術思路對該時期作曲家進行點評式的梳理,解讀他們獨有的浪漫主義風格。文中有一處表述或許當時并未關注,現在看來十分“惹眼”,即“一些音樂史學家們不甚準確地用這個概念(指浪漫主義)來概括歐洲19世紀的音樂,聲稱整個19世紀是浪漫主義音樂的世紀”,可看出先生對這一觀點是不贊同的。無獨有偶,在該文發表12年后,孫國忠教授的《十九世紀音樂:古典傳統與浪漫主義》{23}在論述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無法割裂的連續性的基礎上,對浪漫主義給予了更準確的表述——“19世紀音樂中的一種具有鮮明時代印記的‘音樂風尚”{24},這與于先生的看法有不謀而合之意。《古典音樂:時代·風格·經典》{25}上文同是孫國忠教授為“諾頓音樂斷代史叢書”中譯本所著的導讀性文章,他以“時代”框架古典音樂的空間維度、以“風格”審視古典音樂的基本“構件”、以“經典”解析古典音樂的藝術沉淀,完成了對古典音樂、樂派以及該時期的界定與闡發。比上述文章更為微觀的研究,有伍維曦的《“新藝術”時期的音樂觀念、音樂受眾和音樂家生存方式》{26}、姚青的《威尼斯作為16世紀末17世紀初歐洲音樂發展中心的歷史機緣分析》{27}等,這類細致審思性文章的作者以年輕學者居多,顯示了這一群體特定問題的深入挖掘和嚴謹思考。縱向研究是對某一問題的歷時性討論,探討其在不間斷的歷史發展中呈現的狀態和規律,姚亞平教授的《語言與命名——話語變動中的西方音樂體裁史掃描》{28}是這類研究的典范。該文具有著明顯的“新音樂學”意味,他以現代語言學中的“所指”“能指”及福柯的“知識型”理論作為基礎,考察音樂體裁命名的種種問題,用福柯的“相似”“表征”和“現代”三個概念及體裁命名的視角將音樂史進行了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巴洛克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的三個歷史分期,同時指明了如此分類的內涵依據。這種研究方式及視角都彰顯著作者在專題史考察時的獨特思維。
三、開放性描述:20世紀
“20世紀”是西方音樂史六個斷代中距離我們最近的時期,因為各種歷史原因,直到上世紀80年代我國音樂界才陸續開始對20世紀音樂的關注,在2000年之后呈現出突飛猛進的趨勢。陳鴻鐸教授以《20世紀音樂:反叛·標新·多元》{29}一文對該時期進行了整體梳理和研辯式概括。標題中的“反叛”指創作20世紀作曲家的思維范式,“標新”指在“反叛”思維范式下的創作實踐,“多元”指在創作實踐后展現的眾聲喧嘩局面,三者層層遞進、無法割裂。可以說,由這三個詞語所概括出的思維范式、創作實踐和呈示風貌均展現出20世紀音樂的開放性氣質。文中,作者以扎實的音樂分析功底細致地描述了從調性到節奏、織體、音響等音樂要素的革命以及從勛伯格到斯托克豪森、布列茲、里蓋蒂、阿沃·帕特等人不同風格的音樂創作。作者在論述“多元”這一內容時認為:“自20 世紀80 年代后,一批中國作曲家如譚盾、陳其鋼、葉小鋼、瞿小松、陳曉勇、蘇聰等也走出國門參與到西方20 世紀音樂發展的進程中,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顯示了我國作曲家在現代音樂創作中的活力與成就以及中國音樂學家強烈的民族自豪感。
姚亞平教授認為,20世紀并未出現新的體裁,卻賦予了這些體裁新的內涵{30}。正因為這些新內涵,使20世紀音樂的研究出現了繽紛豐富的視角。如王旭青以《理查·施特勞斯交響詩的音樂敘事理路》{31}、《艾夫斯〈未被回答的問題〉的結構思維與敘事策略》{32}、《喬治·克拉姆〈四個月亮的夜晚〉中的引用與象征》{33}等多篇論文,從敘事學、修辭學角度來對20世紀音樂作品進行解析。在對《四個月亮的夜晚》的分析中,筆者著重討論作曲家的“象征主義觀念”這類超音樂(extra-music)文本的使用,以說明20世紀音樂家的開放性思路。姜蕾以《現代主義文學結構與二戰后音樂形式革命——以布列茲〈第三鋼琴奏鳴曲〉為例》{34}《現代視覺藝術視角下的“開放”結構——艾爾·布朗〈可變結構II〉結構研究》{35}《“瞬間結構”與斯托克豪森的〈瞬間〉》{36}等文,將現代文學、視覺等作為著力點,結合音樂技術分析闡釋音樂。班麗霞則以《“整體藝術品”〈幸運之手〉中的視聽藝術交融》{37}《〈幸運之手〉與〈黃色聲響〉比較分析——兼談藝術互動研究的重要性》{38}勛伯格的表現主義音樂形式與視覺藝術的并行互動》{39}等文章,從藝術互動的角度在對作品進行闡釋并解讀該視角的積極意義和作用。此外,邵曉勇{40}、劉奇{41}等青年學者以宗教、物理數學及文化起源等為切入點對該時期音樂進行探討。這些“超音樂”的開放性研究方式的出現,既是20世紀音樂研究的新趨勢,又是作曲觀念變革帶來的必然結果。
與上述個案研究不同,姚亞平教授的《歐洲早期音樂傳統與20世紀現代作曲觀念》{42}是具有歷史性宏觀視角的研究。他將20世紀音樂研究的維度進行了充分擴展——把時間拉回到了遙遠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作者雖然以序列、對位、微分音、分割、拼貼等純技法的層面進行依次論述,但滲透的卻是“關聯性”這一重要的史學思維:20世紀的新技法是具有“前景”性質的表現性問題,其背后是作為“背景”的、任何人無法改變的歷史邏輯。這種關聯性辯證思維也是20世紀音樂研究開放路徑的又一例證。
結 語
隨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英美音樂學界向“批評”學科范式的轉型,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方式、角度也發生著變化,這一點從西方音樂學會年會的議題中同樣得到體現。具體到作曲家(作品)的研究層面,西方學界的兩種研究方式——注重譜例分析的實證主義研究和注重音樂作品審美意義和藝術價值的、帶有強烈“批評”傾向的研究,在我國2000年后的發展情形是:自2006年起,具有批評意味的研究方式呈現出“一路高歌”的姿態(圖3),說明中國學者們對西方研究發展動向的敏銳感知和自我認知的更新與不斷探索,而“闡釋”也早已成為這一論域背后的關鍵詞。endprint
圖3
在西方音樂史研究方法論層面,泰斗級學者錢仁康先生雖未對此進行明確說明,但早已做出了杰出表率:《句句雙 天下同》{43}《與古典詩歌格律脈脈相通的西方傳統音樂》{44}等文雖只是先生治學生涯成果的冰山一角,卻在找尋中西音樂“各自獨立的價值、目標和作用”的同時堅持“平等對話、互動互融”的原則進行學術探索{45},其研究過程中思維的縝密、措辭的嚴謹均令后輩嘆服。楊燕迪教授也曾堅信:“如果在熟讀西方經典著作和精準的分析樂譜的情況下,在具體作品的審美感受、評論和解讀方面,我們和西方同行實際上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并有可能因為我們的中國文化背景和熏陶而具有自己的獨特眼光和視角。”{46}
在筆者現有資料中,“20世紀”目前雖在西方音樂史六個斷代的研究中所占比重最大,但與西方同階段的研究狀況仍有所差異。據我國學者姜蕾的考察,美國學者在2003—2013年間對20世紀音樂的研究從9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44%下降到26%,而對于前調性時期、調性時期的關注卻明顯增加。{47}這樣對比情形的出現,可能依然與我國學者對于西方20世紀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相對滯后有關。
楊燕迪教授曾用“危機四伏”來形容中國西方音樂史學科的研究,而經過最近十幾年的發展,研究成果在廣度的不斷擴展和深度的逐漸豐厚方面是有目共睹的,而“學習-接受-運用-反思-挑戰”或許能夠說明該學科一路來的發展情形。在面對當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之時,筆者愿用姚亞平教授在討論“音樂學分析”時的話來同樣形容:“應該關注當代國際學術思潮的最新動向,但并不盲從,而是吸收一些有用的東西,并結合自身的文化環境和學術傳統,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48}路漫漫其修遠,愿吾等年輕一輩始終能夠做到:“只因實力不濟而有愧,卻為不曾懈怠而無悔。”{49}
{1}{11}{23} 孫國忠《十九世紀音樂:古典傳統與浪漫主義》,《黃鐘》2016年第1期,第5頁。
{2} 賈抒冰《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美“新音樂學”發展綜論》,《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第115—123頁。
{3}{46} 《音樂藝術》2009年第1期。
{4} 同{3},第76頁。
{5} 《黃鐘》2009年第1、2期。
{6} 齊琨《表述:從音樂到音聲再到聲音》,《音樂研究》2016年第2期,第85頁。
{7} 《音樂研究》2007年第3期。
{8} 《中國音樂學》2002年第4期。
{9} 《樂府新聲》2010年第1期。
{10} 宋方方《歐洲19世紀女性作曲家的艱難處境——以范妮·門德爾松和克拉拉·舒曼為例》,《交響》2007年第3期。
{12} 《音樂藝術》2011年第1期。
{13} 《音樂研究》2013年3期。
{14} 《天籟》2007年第3期。
{15} 《音樂藝術》2003年第3期。
{16} 《音樂藝術》2010年第2期。
{17} 《音樂研究》2013年第4期。
{18} 《音樂研究》2914年第3期。
{19} 葉松榮《西方音樂史研究的“中國視野”可行性探討——與其他學科相互參照中獲得的啟示》,《音樂研究》2010年第5期;《西方人的音樂 中國人的學術——對以中國人的視野研究西方音樂觀念與實踐問題的理解》,《音樂研究》2013年第6期。
{20} 班麗霞《對西方音樂(史)研究“中國視野”——說的思考》,《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
{21} 劉小龍《西方音樂話題史:探索新方向》,《音樂研究》2013年第4期。
{22} 《音樂研究》2004年第1期。
{24} 同{1},第16頁。
{25} 《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
{26} 《音樂藝術》2005年第2期。
{27} 《音樂研究》2009年第1期。
{28} 《中國音樂學》2003年第3期。
{29} 《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
{30} 《中國音樂學》2003年第3期,第101頁。
{31} 《中國音樂學》2010年第1期。
{32} 《音樂研究》2011年第2期。
{33} 《中國音樂學》2014年第2期。
{34} 《音樂研究》2012年第5期。
{35} 《中國音樂學》2013年第1期。
{36} 《音樂藝術》2013年第2期。
{37}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38} 《音樂研究》2007年第4期。
{39} 《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40} 邵曉勇《道德與精神的深度描述者——20世紀下半葉俄羅斯作曲家施尼特凱》,《人民音樂》2010年第5期。
{41} 劉奇《“神性”的跨文化碰撞——析莫里斯·奧阿納混聲合唱〈阿沃哈〉的創作技法》,《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
{42}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
{43} 《音樂藝術》1997年第4期。
{44} 《音樂藝術》2001年第1期。
{45} 周楷模《中國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樂歷史——研究者的再定位及其方法拓展》,《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
{47} 姜蕾《21世紀以來美國音樂(分析)理論學科新趨勢研究》,《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第35頁。
{48} 姚亞平《性別焦慮與沖突——男性表達與呈現的音樂闡釋》,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5年版。
{49} 居其宏《新音樂史家與現代思潮研究——明言新著〈20世紀中國音樂批評導論〉讀后》,《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孫絲絲 博士,江南大學人文學院音樂系副教授
柯雅杰 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音樂教師
(責任編輯 金兆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