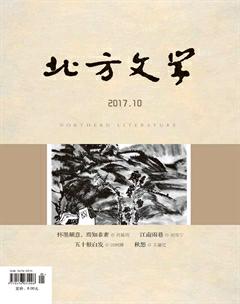狄更斯《雙城記》中的人物解讀
姜婉婷
摘要:《雙城記》是狄更斯創作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這部作品全景式的描繪了19世紀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全貌,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人們的精神生活。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當時社會三個不同階層的代表,每個主人公都被刻畫得形神兼備、惟妙惟肖,為讀者描繪了一種愛與恨的對決,最終是愛勝恨,完美告終。
關鍵詞:狄更斯;《雙城記》;人物形象
一、博愛寬容的仁愛者
(一)公義正直的梅尼特醫生
梅尼特是法國巴黎的一名外科醫生,在侯爵兄弟的威逼利誘下被迫跟隨他們去出診。在侯爵的家中親眼看到了一個發狂的年輕美貌的農婦,一個受了傷的少年。少婦是少年的姐姐,侯爵兄弟染指了少婦,少年將小妹妹安排在了漁民家中,拿著劍去找侯爵兄弟報仇,終因寡不敵眾被殺。少婦和少年都含恨而去。醫生對侯爵兄弟的暴行義憤填膺,對慘遭蹂躪的農民少女及其一家所受的迫害深表同情,他不愿與世俗同流合污,上書朝廷,控訴著侯爵兄弟的罪行。但他天真的以為,侯爵兄弟的惡行會得到懲罰,正義會得到伸張。然而侯爵兄弟只手遮天,將醫生投入監獄,蒙受18年不白之冤。或許是體內的那顆良心的支撐,內心的正義之后未滅,在女兒細致入微的照料下,梅內特醫生的身體恢復了健康。然而多年之后,一場法國大革命的驚雷打破了生活的平靜,封建勢力倒臺,侯爵家族也相繼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另一面,醫生的愛女露西與侯爵的后代達爾內相識相知,達爾內向醫生坦白了自己的身份,用人品向醫生證明自己對露西的愛,醫生同意了他們的交往。顯然在這里,作者是不認同德法石太太復仇的,相比較而言,狄更斯更加贊賞梅尼特醫生的做法,他所倡導的人道主義是寬容而且講道理的,雖然他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但不主張用暴力手段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更不贊同假借革命來完成家族復仇。
(二)仁愛善良的露西小姐
在狄更斯的筆下,紅色是最冷酷的顏色。他用這種鮮明的光彩,烘托著小說復雜的主題。而與鮮明紅色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狄更斯筆下的金黃色,金黃色象征著仁愛、救贖和忠誠,這是狄更斯在文章中布下的暖色調,比如:女主人公被作者描寫為一個滿頭金發的漂亮姑娘,狄更斯就用“金色絲線”來比喻露西的愛,他說:“她是一根金色絲線,而她的語聲,她的容光,她的撫愛,幾乎是對他產生有益的強大的影響......”[1]作者用“金色絲線”表達了最終的寓意:它使人們的心連結在一起,構成仁愛、善良、救贖的偉大力量,用仁愛和忠誠重建人間的幸福。露西繼承了父親的正直與善良,是一位接近完美的女性形象。在全家最艱難的時候,她守護父親,照顧女兒,支撐著家庭重擔,把家里的內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生活中,她和善待人,從不輕視弱者,即使是面對一個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位子的厭世主義者,她也會流露出一種同情愛憐之心。這并不是露西在眾人面前的一種表演,而是她內心真實的流露。她對每一個來到她身邊的人,都報以溫柔和平的心。露西以博愛給人帶來安慰與力量,用仁愛與忠誠重建著人間的幸福,這正是人道主義所達到的境界。
(三)舍己救人的卡爾頓先生
“我真是一個可憐的家伙,擋了自己的路,但不知怎么的,這是一條不斷繼續下去的路。每條道路上都立著相同的指路牌,不論是在路的最前端還是每一個轉彎處。”[2]狄更斯在創作的《雙城記》中也彌漫著這種情感基調,而且書中的一個角色的身上也出現了這種情緒。
近幾年來,許多研究者都在探究卡爾頓選擇成全的原因是什么,這種成全的本質又是什么,目前有三種的見解。第一種是基督教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也是較為普遍的一種解讀,受圣經文化的影響。第二種是源于他對露西的特殊感情。這之中,既包含著愛情,也包含著親情。眾多研究表明,他對露西的感情不僅僅是愛情,可能是露西及醫生一家人的家庭氛圍對于他的一種吸引,也可能是露西和醫生身上的善良,正義,責任感對卡爾頓的一種指引。或許這正是他自身缺失和迷失的一部分。第三種是源于卡爾頓對達爾內特殊的感情。這里所指的特殊感情,并不是某種錯位的病態感情。作品中的達爾內過于理想,人物的發展遵循著作者的理想主義,而卡爾頓更具有真實感,是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的人。他們雖然有著酷似的相貌,在不同領域中都有著值得肯定的才華,但是由于某種原因使本該相似或相同的兩個人產生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走向。在某種程度上看,卡爾頓是現實,而達爾內是理想,他們在精神上是一個人。或許在卡爾頓心中,達爾內是“自己”本應該存在的理想面貌。所以卡爾頓對達爾內的感情,有嫉妒,有羨慕,以至于最后的成全。最后他替達爾內走上斷頭臺,或許是因為對露西的愛屋及烏,但也可能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成全。他把達爾內看作了另一個自己即理想中的自己,他想守護“另一個自己”。
二、冷酷殘忍的壓迫者
文中最為代表的是以侯爵兄弟為代表的的封建貴族。封建是一種基于封建地主階級占領土地剝削農民或剩余勞動力的社會制度。封建在封建主義中的本義,是 “印章”或“建國”;古代文學中的 “封建”是“分封”的意思。[3]故事的第七章“城里的爵爺”描寫了宮廷的大臣吃巧克力需要四個仆人伺候。“要是閣下在吃巧克力是少了一個人伺候,又要在令人羨慕的上天之下保持崇高地位,是不可能的。要是只有三個人寒磣地伺候他吃巧克力,他的家徽就會蒙受奇恥大辱;只有兩個人伺候,他非死不可了。”以侯爵為代表的法國的封建統治者,上自宮廷的達官貴人,下至地方貴族,都是剝削、壓迫人民大眾的喪心病狂的惡魔,他們自認為身份尊貴,玩弄權利,支配他人的生死,這實質上是一種赤裸裸的掠奪,他們只關心自己和所屬階層的利益,從不關心公眾利益,對他們來說,階層的利益高于一切。狄更斯堅信,這種封建特權制度最終會被自由共和制度所取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三、以怨報怨的復仇者
《雙城記》中的德法石太太是復仇者的代表。她就是十幾年前遭到侯爵迫害的那個農婦的妹妹,她被送到海濱,由漁民撫養成人。她牢記自己家族的血海深仇,在內心深處銘刻下了統治者的一樁樁罪行,等待著有朝一日和統治者來一個對決,算一次總賬。革命者的力量源泉是:饑餓與復仇,他們受怨憤的情緒支配,要向統治者討回公道。[4]因此他們的革命很容易走向非理性,甚至變得瘋狂。在作者對法國大革命的描寫中,看不出德法石夫婦為代表的革命者的遠見、膽識和謀略,他們倒像是為饑餓和復仇的欲望所驅使的一群烏合之眾。
就革命的實質而言,狄更斯認為它不是悲劇,而是悲劇的避免。他用生動的事實表明,法國大革命是必然的,是正義的。但是,由于在革命中,群眾的革命熱情沒有被理性地引導,因此是非理性的、瘋狂的復仇情緒占了上風,人類身上潛藏著的野心被激發出來,善良的本質被淹沒了,伸張正義的革命者蛻變為嗜血的殺人狂,濫殺無辜的現象層出不窮,于是本為避免悲劇而進行的革命反而制造了一場又一場的悲劇。雖然狄更斯用辛辣的筆調揭露了那些貴族階級的橫暴與冷酷,但他并不贊成通過暴力革命的手段來改變當時的社會現狀。他一直試圖用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來教育引導社會“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5]雖死永生,卡頓永生,仁愛永生。這就是狄更斯的道德意象,也是人道主義向崇高舍己救贖思想發展的展示。
參考文獻:
[1]劉炳善.英國文學簡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1:10.
[2]狄更斯.雙城記[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80.
[3]聶珍釗.狄更斯小說研究[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34.
[4]叢娟.<雙城記>的人物形象塑造及其價值意蘊分析[J].韶天學院報(社會科學),2004,04(10).
[5]臧嫦艷,郭月琴.<雙城記>的人物形象和文化氣質[A].名作欣賞-外國小說,2012,12(2).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