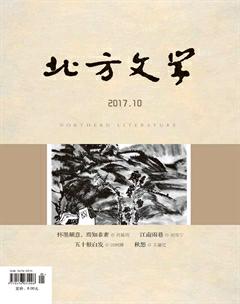“程蝶衣”人格分析
劉詩詩
摘要:《霸王別姬》是上個世紀末最具典型性的一部電影,其中張國榮飾演的程蝶衣在觀眾心中印象深刻。其性格的復雜和特殊性成為這部影片的一大亮點。而早在20世紀20-30年代,中國的一些文學家開始向中國介紹弗洛伊德理論,風靡一時。而在后期,這一理論也深深影響了電影界。本文將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解讀程蝶衣的復雜人格,看其本我、自我、超我對這一形象的作用。
關鍵詞:霸王別姬;程蝶衣;人格;分析
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改編自李碧華同名小說,在華語影壇中已成為經典之作。影片講述了名伶程蝶衣作為戲子一生的悲歡離合,他經歷了“小豆子”的童年、“程蝶衣”的中年到最后“虞姬式”的升華。他也是導演陳凱歌費盡心力塑造出的一個飽滿的成功的悲劇人物形象,陳凱歌在對程蝶衣這個角色進行概括時說:“他是一個在現實生活中做夢的人,在他個人世界里,理想與現實、舞臺與人生、男與女、真與幻、生與死的界限,統統被融合了,這個人物形象告訴我們什么叫迷戀。”導演通過電影區別于文本的視覺、聽覺表達使程蝶衣這一人物形象——復雜迷幻的性格、難以捉摸的心理狀態的言語行為深入人心。這也讓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有了可能。
在十九世紀末,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心理學在二十世紀迅速運用于西方文學研究,精神分析批判成為一類著名的文學批評手段。電影作為一類特殊的文學載體離不開這一文學批判。美國加州大學電影教授尼克·布朗先生就曾指出電影人物形象的解讀與精神分析有直接性關系。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他的人格理論是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主要包括人格結構、人格動力、人格適應及人格發展四個部分。
早期,他認為人格分為無意識和意識兩種結構,人的心理分為意識、前意識和潛意識三個層次。“意識”是人心理狀態的最高形式,是人的心理因素世界中的“首腦”,是人在清醒知覺狀態下的思想和情緒,是隨時可以觀察到的心理現象。它統治著整個精神世界,使之動作協調、穩定合理。“前意識”是從潛意識中而來。潛意識這個概念是從壓抑理論中獲得,壓抑為我們提供了兩種潛意識的原型:一種是潛伏的但能成為有意識的;另一種是被壓抑的不能成為有意識的。前者稱為“前意識”,后者稱為“潛意識”。
晚期,弗洛伊德對他的理論做了修正,提出了新的“三部分人格結構”說,即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個部分構成的。“本我”,是遺傳下來的動物性本能,是一種原始動力機制,其目標是毫不掩飾地滿足生物欲望,內部充滿了非理性、反社會和破壞性的沖動,是潛意識結構部分,是所有本能的承載體,遵循快樂原則;“自我”是每個人都包含的心理內涵,是意識的主體結構部分,它控制著能動性的入口,及時將興奮釋放到外部世界中去,根據外部世界的需要來活動,遵循現實原則;“超我”是充滿清規戒律和類似于良心的人格層面,是道德化了的“自我”,是內在的道德檢察官,它包括良心和自我理想,遵循至善原則。本我、自我和超我處于協調和平衡狀態,人格才能正常發展。
程蝶衣的心理發展在一定意義上是上述三者處于失衡狀態的反映,也正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影響才使得此人物形象獨具特色。本文將依據弗洛伊德的相關人格分析理論對程蝶衣這一人物形象進行簡要分析。
一、性別錯亂——“俄狄浦斯情結”、“創傷性情境”
自幼,程蝶衣跟隨母親在煙花巷里生活,耳濡目染的全是女人家的生活,對母親的依戀就如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描述的男孩留戀母親一般,程蝶衣一生都貫穿著母親的記憶,從斷指時的“娘,手都凍冰了”到戒大煙時的反復囈語足以說明其母親在他意識形成中起著多么重要的作用。而他的母親恰是一位青樓女子,言語行為自是嬌媚非凡,程蝶衣在這樣的環境下亦變得柔美娟秀,較之平常男兒便多了幾分女孩子氣,到戲班子后對于像“父親”一樣保護他的小石頭也產生了依戀和崇拜。再者,程蝶衣性別錯亂起源于童年的“創傷性情境”,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兒童在幼年期間對環境中人、事或物的體驗多半影響成長后的生活方式”。駢指的切除也意味著程蝶衣情欲的斬斷,這是推進程蝶衣女性化的第一步;小石頭用煙斗攪破小豆子的嘴時,嘴角流出的鮮血是精神強奸的表現,這是程蝶衣作為戲子的內心女性化轉折;被張公公凌辱,身心受到折磨,這是程蝶衣作為現實人的徹底的女性化轉變。弗洛伊德在《自我與本我》中提到,不快樂的感覺具有任何形式的內在推動性。它促進變化,促進釋放。如果自我不加強制,它就會施加內驅力。直到對該強制產生抵抗,釋放行動被阻止,這個“未被確定的成分”才能迅速成為不快樂的意識。同樣,身體需要而產生的緊張可保持為潛意識,身體的痛苦介于內部與外部知覺之間的一種東西,尤其當根源是在外部世界時,它行動起來也像一種內在知覺。程蝶衣童年時受到的傷害產生的感覺在到達知覺系統后形成了一種女性身份的潛意識。
二、從一而終——“超我”
“超我”在影片里一方面體現在程蝶衣身上,一方面體現在戲曲里理想化的“虞姬”身上。程蝶衣剛進入戲班子時對所有的人都抱有敵意,對于同齡人的嘲笑眼神里透露著仇恨,而在小石頭一系列的偏袒舉措下,當小石頭寒冬深夜受罰后,他沒有說一句話用被子牢牢地抱住小石頭,這說明在他的心還是善的。在離開張府,偶遇一棄嬰時,不由分說地抱起,潛意識中的母性和“同病相憐”的前意識使得程蝶衣不顧那坤的勸說收留了這個往后忘恩負義、逼迫他至死的“小四”。童年的程蝶衣人格中的“超我”還是占主導的。而影片中從未現身的“虞姬”是另一個“超我”形象,程蝶衣在逃離戲班子又返回后,關師傅給他們說了《霸王別姬》的故事:楚霸王行至垓下,遭受劉邦十面埋伏,深夜四面楚歌,霸王也落下淚來,讓那烏騅馬逃命,烏騅馬不去;讓那虞姬走人,虞姬不肯,給項王斟酒舞劍后隨即拔劍自刎,從一而終啊!“從一而終”這一虞姬身上的精神是傳統道德規范的最高境界,影響了程蝶衣一生。他對戲,對段曉樓更是遵循著從一而終的原則。當發現現實與戲中截然相反時,他寧肯拔劍自刎,做真正的虞姬從一而終而不僅僅是臺上演戲的戲子。
三、不瘋魔不成活——“本我” “自我”
本我是一個原始的、與生俱來的非組織性的結構,自我是從本我中分化發展起來的,成為本我與外部世界的中介。就像維也納的喬治·格勞代克認為,在我們所謂的自我的生活中表現出來的行為基本上是被動的。我們在知道的,無法控制的力量下“生活”著。段曉樓與菊仙的婚姻是造成程蝶衣人格失衡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激醒他內心“本我”的重要來源。得知師兄不再一門心思唱戲時,他歇斯底里,“不是一輩子,缺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小時……都不是一輩子”。“從一而終”的原則遭到了最在乎的人的觸犯,這讓潛伏在程蝶衣內心深處的“本我”爆發出來。而菊仙“窯姐”的身份更是激起了前意識中對“妓女”本能的厭惡,使得程蝶衣每次與菊仙的會面都是不歡而散。“臟淫婦”、“臭婊子”、“臟貨”……冷淡的表情,尖酸的話語,淡漠的舉動都明顯揭露了程蝶衣“本我”中潛藏的女性嫉妒和占有欲,這是平日里儒雅君子式的“自我”所無法控制的。抽大煙時的程蝶衣精神恍惚,瘋癲混亂更是其“本我”中頹靡、放縱、享受的直接表征。同時,程蝶衣身上也存在著遵循現實原則的“自我”,由前可知,自我是本我的一部分,是通過潛意識知覺即意識媒介已被外部世界的直接影響所改變的那一部分。自我在功能上的重要性就是把能動性的正常控制轉移給自我。程蝶衣知曉要想在京劇里“從一而終”就必須要有袁四爺的栽培,雖然是為了熱愛的京劇藝術可現實里的原則也讓程蝶衣有著與常人無異的攀附心理,自我的能動性在這里起到了作用。對師傅的尊重也是“自我”的表現,盡管他是在關師傅的鞭子下長大,但傳統的尊師之道以及“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觀念都讓程蝶衣在對待關師傅的態度和對小四傳授唱京戲之道里有了體現。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自我本應在本我和超我中調節,但當師傅去世后,師兄不再唱戲時,最后還是親手撫養長大的孩子將自己打成反動派,自我已經束縛不了本我。程蝶衣也認清了人的本性,才會在11年后自刎于戲臺,自刎于“霸王”的懷中。
回頭看程蝶衣一生,他作為現實中存在的“人”是一個悲劇。他的悲劇在于其人格體系的失衡。正如弗洛伊德所說:“人的個體人格各個部分并不是彼此獨立的,而是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程蝶衣從“小豆子”到“程蝶衣”再到“虞姬”的心路歷程是這個人物形象本身人格中“意識”與“無意識”,“本我”、“自我”和“超我”共同作用的結果。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