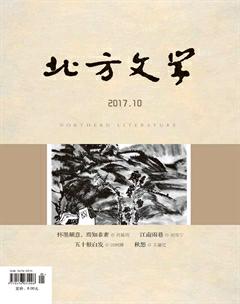微型小說(shuō)與短篇小說(shuō)及敘事散文之關(guān)系
鄭榕玉
在寫作課上講“微型小說(shuō)”時(shí),學(xué)生表示很難區(qū)分清楚微型小說(shuō)與短篇小說(shuō),微型小說(shuō)與敘事散文的關(guān)系。 微型小說(shuō)與短篇小說(shuō)都具備人物、情節(jié)、環(huán)境等小說(shuō)要素,在篇幅上與短篇小說(shuō)也難以截然分開,學(xué)生有困惑也屬正常。同時(shí),微型小說(shuō)散文化和敘事散文小說(shuō)化的趨勢(shì)也常常困擾學(xué)生的判斷。為此,有必要對(duì)微型小說(shuō)與短篇小說(shuō)的內(nèi)質(zhì)與邊界問(wèn)題,微型小說(shuō)散文化與敘事散文小說(shuō)化的問(wèn)題進(jìn)行深入的探討。
一、微型小說(shuō)與短篇小說(shuō)的內(nèi)質(zhì)與邊界問(wèn)題
微型小說(shuō)與短篇小說(shuō)都具備人物、情節(jié)、環(huán)境等小說(shuō)要素,而且篇幅與字?jǐn)?shù)的邊界模糊(注:一說(shuō)不超過(guò)2000字,也有說(shuō)1500字以內(nèi)),單從字?jǐn)?shù)篇幅上區(qū)分微型小說(shuō)與短篇小說(shuō),顯然是行不通的。若要清楚地區(qū)分兩者,應(yīng)該從小說(shuō)的三要素上入手,從它們所塑造的不同人物,情節(jié)與環(huán)境來(lái)進(jìn)行區(qū)分。
(一)塑造的人物不同
微型小說(shuō)人物塑造有一種單純性的要求,一般只突出某一人物的某一性格側(cè)面,往往只捉住某一人物性格特征最為主要、最有代表性的某一個(gè)側(cè)面來(lái)加以藝術(shù)的展現(xiàn)。而短篇小說(shuō)即使其篇幅極短,其人物塑造并不要求單一性,筆墨可能并不聚焦于某一人物身上,即使筆墨聚焦于某一人物,刻畫的也是這一人物復(fù)雜的性格特征。這是微型小說(shuō)與短篇小說(shuō)在人物塑造上的區(qū)別。
(二)情節(jié)設(shè)置不同
短篇小說(shuō)和微型小說(shuō)情節(jié)里的事件在內(nèi)容質(zhì)量上沒(méi)有什么太大的區(qū)別。它們的區(qū)別主要體現(xiàn)在事件的形式數(shù)量上。一般短篇小說(shuō)的情節(jié)必須具有兩個(gè)以上的具體事件,因而你可以把它稱作復(fù)雜事件,微型小說(shuō)的情節(jié)只能是由一個(gè)具體事件構(gòu)成。微型小說(shuō)在情節(jié)提煉上要求通過(guò)敘述一個(gè)具體事件來(lái)構(gòu)成單一性情節(jié)。
(三)環(huán)境設(shè)置不同
微型小說(shuō)被學(xué)者稱為“瞬間藝術(shù)”,作者往往選取 “頃刻”間的單一空間里的事件來(lái)突出某一人物的某一性格側(cè)面。而短篇小說(shuō)則一般通過(guò)不同的時(shí)空?qǐng)鼍皝?lái)展示人物不同的性格側(cè)面,以塑造復(fù)雜園型的人物形象。
區(qū)分微型小說(shuō)與短篇小說(shuō)的根本點(diǎn)在于其人物塑造的側(cè)重點(diǎn),情節(jié)運(yùn)行規(guī)律及場(chǎng)景設(shè)置數(shù)量上,若只從小說(shuō)的篇幅與數(shù)字來(lái)區(qū)別微型小說(shuō)和短篇小說(shuō),勢(shì)必會(huì)陷入混亂。
二、微型小說(shuō)散文化與敘事散文小說(shuō)化的問(wèn)題
(一)真實(shí)與虛構(gòu)的邊界逐漸模糊
敘事散文和散文化微型小說(shuō)有時(shí)很難截然分開,它們之間存在許多共同特征:第一人稱敘述,語(yǔ)言優(yōu)美,情節(jié)感人,以敘事為主。傳統(tǒng)的文學(xué)理論將“真實(shí)與虛構(gòu)”作為標(biāo)準(zhǔn)來(lái)區(qū)分這兩種文體。這實(shí)際上是有“瞎子摸象”之嫌疑,敘事散文的“真實(shí)”事件本質(zhì)上也只是擬真敘事,作者的創(chuàng)作情感與意愿有時(shí)會(huì)過(guò)濾與扭曲本真的事件,使散文的本真事件變形,更何況有時(shí)可能作家自己也記不清遠(yuǎn)久的事實(shí),只能靠想象來(lái)補(bǔ)充。總之,任何創(chuàng)作不可避免都帶有修辭化的虛構(gòu)成分,不可能還原本真生活,真假只能是相對(duì)而言。
(二)小說(shuō)味與散文味逐漸分不清
散文和微型小說(shuō)都是在經(jīng)歷著巨變的文體樣式,外延都越來(lái)越廣。微型小說(shuō)講求細(xì)節(jié),講求情節(jié),但大小說(shuō)家的散文往往是構(gòu)成細(xì)節(jié)的散文,小說(shuō)味濃。散文講究意境,但大小說(shuō)家的小說(shuō)往往具有散文的詩(shī)化意境。
當(dāng)代文壇許多著名微型小說(shuō)家(汪曾祺、林斤瀾、曹乃謙、劉國(guó)芳、鄧開善、于德北、邵寶健等)通過(guò)選擇高品位富有審美刺激的題材和對(duì)題材獨(dú)具匠心的藝術(shù)處理,在短小的篇幅里將情節(jié)提煉得很雅致、很精美,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散文化的審美意境。比如沈從文和汪曾祺師生的小說(shuō)散文味特別濃,如《邊城》《受戒》完全可以當(dāng)散來(lái)品味,而遲子建、莫言、韓少功三位作家的散文《與周瑜相遇》《奇遇》《青龍偃月刀》)小說(shuō)味特別濃,完全可以當(dāng)作小說(shuō)來(lái)讀。
“文體的打亂沖擊再造組合才能產(chǎn)生新的東西。用散文的語(yǔ)言寫小說(shuō),這是一種文體的再組合,讓人產(chǎn)生猛然一新的感覺(jué)。”微型小說(shuō)、散文應(yīng)該可以而且鼓勵(lì)跨界,它們?cè)谖捏w的碰撞之中,使文體再組合,形成更具有藝術(shù)效果新散文、新微型小說(shuō)。
總之,單以真實(shí)與虛構(gòu)、小說(shuō)味濃淡來(lái)判斷微型小說(shuō)與敘事散文,不具備科學(xué)性與可行性。我們?cè)谂袛嗌⑽幕奈⑿托≌f(shuō)與小說(shuō)化的敘事散時(shí),應(yīng)該以其人物塑造的側(cè)面,情節(jié)事件與環(huán)境時(shí)空的數(shù)量來(lái)考察衡量,若三者均符合微型小說(shuō)的單一性原則(人物性格側(cè)面單一、情節(jié)事件單一、時(shí)空環(huán)境單一),則應(yīng)該歸屬微型小說(shuō)。
綜上,我們認(rèn)為,字?jǐn)?shù)在2000字以內(nèi),在單一時(shí)空中通過(guò)單一一具體事件突出人物單一性格特征的敘事文本,即為微型小說(shuō)。
(作者單位:閩江學(xué)院人文與傳播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