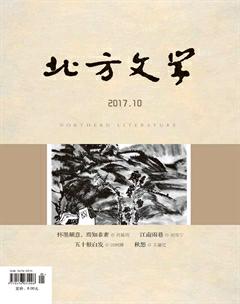早期文化研究的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
郭本華
摘要:文化研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西方興起的學術研究思潮,其復雜的理論構成和前沿性的學術思想突破了傳統(tǒng)的文藝批評和文學研究的范式,將關注點從文學文本拓展至一切文化現(xiàn)象:種族、階級、性別、政治、藝術等多學科的領域,歷經(jīng)多年來的發(fā)展,文化研究最終確定了自身的學科地位,其影響力也從歐洲波及到了美國乃至全世界。本文將從早期文化研究的學科發(fā)展的角度來論述其“現(xiàn)代性”的重要轉(zhuǎn)向。
關鍵詞:文化研究;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性
一、早期文化研究的發(fā)端
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究竟緣起于何時?目前學術界皆無統(tǒng)一的觀點,正如斯圖亞特·霍爾所說,文化研究并無一個“絕對的開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歐洲社會乃至全世界除了面臨著重建家園的困難以外,還面臨著思想和政治上的危機。此時文化研究的興起,便不可避免地帶上了其鮮明的政治色彩,從其發(fā)展的節(jié)點來看,一方面,它和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歐洲活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早期又脫胎于英國英語文學研究,這使得其本身又在思想上帶有某種英國文化主義或精英主義的特質(zhì),下面便從這兩方面來看文化研究的發(fā)展歷程,并且從中我們可以找到其現(xiàn)代性的轉(zhuǎn)向和特質(zhì)。
首先,結(jié)合20世紀50年代的世界政治史來看,文化研究在政治上和英國新左派的形成聯(lián)系緊密,特別是50年代末在歐洲發(fā)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更是加快了新左派批評理論的形成和左翼文化的產(chǎn)生,并最終將這兩股力量結(jié)合到一起。從其思想來源上來看,英國新左派和左翼文化借鑒了前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決定論的批判,認為這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同時認為,前蘇聯(lián)斯大林主義的失敗是由于“經(jīng)濟化約論”,即“把社會、政治、道德和藝術維度簡單約化為經(jīng)濟和階級結(jié)構”[1]。因此,他們質(zhì)疑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要用一種新的思維范式來重置文化與政治、經(jīng)濟之間的聯(lián)系。最終,兩派于1959年共同創(chuàng)立《新左派評論》,此刊物為文化研究的興起建立了穩(wěn)定的理論陣營,著名的文化研究學派的代表人物,如: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圖亞特·霍爾等,都是《新左派評論》的核心成員,也是后來建立享譽盛名的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主要成員。《新左派評論》的成立標志著文化研究從政治確立了自己的理論導向,主要針對的是對文化、政治和經(jīng)濟之間的聯(lián)系,這就使得這個時期的文化研究本身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此時期的一些重要觀點,如“第一,對經(jīng)濟化約論的批判;第二,把文化看作社會過程本身,而把政治、經(jīng)濟僅僅看作這一過程的構成要素”[2],即使這些理論尚未完全形成穩(wěn)定的知識體系,但仍然對后來文化研究批判理論的發(fā)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此外,對政治的關注,是此時期《新左派評論》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文化研究與生俱來的特質(zhì)之一。
其次便是從其思想傳統(tǒng)上看,早期文化研究最早是脫胎于英國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在這一點上,尤其以英國文學批評家李維斯為代表人物。20世紀以來人類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特別是電影、廣播技術的產(chǎn)生,改變了人類的“觀看”事物的方式和生活方式,以電影、電視、攝影、廣告、通俗小說等為代表的新興藝術形式,逐漸成為以大眾為基礎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現(xiàn)代化(Modern)”也成為一個時髦的詞匯。這樣的巨大變革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因此,以李維斯、湯普生為代表的文學批評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便對大眾文化開始研究。然而在對待大眾文化的態(tài)度上,李維斯的觀點和前期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流派之一的法蘭克福學派如出一轍、相互呼應,他們都對大眾文化持一種消極、否定的態(tài)度。李維斯批判大眾文化缺乏“道德的嚴肅性”和“審美價值”[3]。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由于李維斯出身于英國精英階層,因此他的觀點上(李維斯主義)不可避免地帶有保守主義和精英主義的特點。對大眾文化的關注,不僅是早期文化研究學派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也是后來文化研究的一個重點關注對象。李維斯或李維斯主義的基本觀點,對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的研究方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兩人的重要著作,包括: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漫長的革命》等都可以看到這種文化主義傳統(tǒng)、精英主義的影響痕跡,而在對待大眾文化的態(tài)度上,兩位大師卻略有不同。總之,在早期文化研究產(chǎn)生的這一思想層面上來看,早期文化研究的關注點,突破了傳統(tǒng)英國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對于文學文本的分析,而將“文本”的范圍從文學作品擴展至社會、大眾文化等更廣泛的層面上,這是其“現(xiàn)代性”轉(zhuǎn)向的另一個體現(xiàn)。但又不免受到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思維定式的影響。
二、早期文化研究的“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
“現(xiàn)代性”,是一個復雜且含混的概念,從時間的維度上講,“現(xiàn)代”是和“古典”相對立的,而在現(xiàn)代,“現(xiàn)代”又與“后現(xiàn)代”相聯(lián)系。哈貝馬斯在《現(xiàn)代性——未完成的工程》將其定義為:“現(xiàn)代性意識是一種對古典、傳統(tǒng)的對立,是時代精神的現(xiàn)時性”;汪民安在《現(xiàn)代性》一書中,將其概括16世紀至今歐美文明國家的社會存在狀態(tài)……諸多學術界的觀點,都早已超越了歷史學角度的定義,因此,我們認為,與其說“現(xiàn)代性”是描述一個歷史發(fā)展階段的時間術語,不如將其放入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視野中來考察,這樣更具有其現(xiàn)實意義。
從以上對早期文化研究的學科發(fā)展的簡要概括,我們可以看出早期文化研究的理論關注點逐漸以一種“先鋒者”的姿態(tài),介入到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政治經(jīng)濟、大眾文化等諸多領域,這種“介入”實際上是其“現(xiàn)代性”的本質(zhì)和手段體現(xiàn):一方面“現(xiàn)代性”推動了傳統(tǒng)文藝批評催生出文化研究,并賦予文化研究更多的時代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又將這種“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于其諸多的研究對象中:種族、階級、性別、大眾文化、差異政治等方面,以文化研究介入現(xiàn)實、政治。正是在早期的文學研究中,“現(xiàn)代性”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和內(nèi)涵。這些意義和內(nèi)涵又反過來滋養(yǎng)了早期文化研究的獨特的精神品格。早期文化研究的這種“現(xiàn)代性”精神特質(zhì)便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早期文化研究是介入性和反思性的學術思潮。如之前所述,文化研究學術思潮的產(chǎn)生,和20世紀的歐洲社會有著密切聯(lián)系,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的歐洲社會。一方面是科學技術的巨大變革,導致了人類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大眾文化的流行,時間空間的壓縮,傳媒與信息的結(jié)合等;另一方面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動蕩不穩(wěn),加劇了現(xiàn)實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剝離,社會主義的興起和資本主義弊端的凸顯,個體主體性的喪失等。正是在這樣一種大環(huán)境之下,西方學術界的關注點發(fā)生了轉(zhuǎn)移,一些文學批評家開始反思自身,并關注大眾的精神生活和物質(zhì)生活。介入與反思,是早期文化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之一,當傳統(tǒng)的只關注文藝作品的文本研究越來越窮途末路時,文化研究將關注點從作品文本轉(zhuǎn)入現(xiàn)實社會,并介入其中,反思社會政治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并著力于解釋種種矛盾的產(chǎn)生。例如早期的以李維斯和湯普生為代表的“細繹集團”,李維斯與湯普生的代表作《文化與環(huán)境》便是研究廣告的早期著作。這樣的“介入與反思”,是其“現(xiàn)代性”的一個體現(xiàn),也是早期文化研究獨特的現(xiàn)實意義和時代意義的體現(xiàn)。
第二,早期文化研究是跨學科和反學科的學術思潮。文化研究最早是脫胎于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理論。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主要注重的是文學作品本身的文本內(nèi)涵,包括其審美價值、美學傾向、文本與讀者、文本與作者的關系等等,某種程度上來看,文學研究是狹隘的,因為自身只局限于文學作品的文本。但是文本(Text)本身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我們的大眾文化、社會現(xiàn)象、日常生活等等都可以是一個“文本”,即文化研究的文本是一個廣義的文本,換句話說,文化研究的對象是關于社會文本,其范圍早已超越了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同時,文化研究不止是關注當代文化和大眾文化,同時也更注重和社會主流文化相對立的“邊緣文化”和“亞文化”。例如薩義德的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詹姆遜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研究,霍爾的文化身份研究等等,這些也是當時伯明翰學派的關注點之一。其次是在研究方法上,更是體現(xiàn)了其跨學科和反學科的特點。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包括文學、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在具體的研究中更是要借鑒多種研究范式,它沒有固定的研究方法。因此,文化研究的跨學科和反學科的特點,以及多學科的交互融合的表現(xiàn),也是其“現(xiàn)代性”的體現(xiàn)之一,從學科發(fā)展的角度上看,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總的來說,早期文化研究的“現(xiàn)代性”是和獨特的社會時代緊密聯(lián)系的,“現(xiàn)代性”讓文化研究有了自身的時代特點和精神品格。“現(xiàn)代性”不只是一種時間維度的描述,也是社會的一種生存狀態(tài),更是文化研究對待世界的一種態(tài)度。
注釋:
①羅鋼、劉象愚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頁。
②同上,第3頁
③羅鋼、劉象愚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4頁
參考文獻:
[1]羅鋼,劉象愚編.文化研究讀本[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2]汪民安.現(xiàn)代性[M].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3]蕭俊明.文化研究的發(fā)展軌跡[J].國外社會科學,2002(1).
[4]張平功.論文化研究的興起與發(fā)展[J].東南學術,2000(6).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