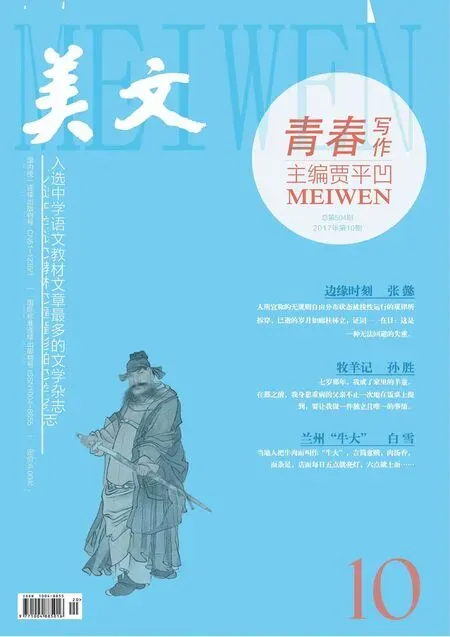第十位繆斯
黃子瑞
第十位繆斯
黃子瑞
我不要蜂蜜,亦不要蜂蟄。
—— 薩福
在海上,最惑人的是塞壬,在人間,最動人的是繆斯。
小亞細亞海岸的萊斯博斯島上曾出現過真正的海妖塞壬——薩福。她用自己的豎琴在古希臘囚住了所有人,讓諸如柏拉圖那樣的挑剔者都認為她是第十位繆斯,而這位阿芙洛狄忒最忠實的信徒,卻最終選擇了在盧卡特的懸崖跳海。“跳崖”在西方文學史上是一個經典的文學符號,早在古希臘時期,盧卡特的人們為了祭祀太陽神阿波羅,會把判處死刑的囚犯挑出來一個人來,讓他背上羽毛做成的翅膀,將其從懸崖上推到海里。在今天看來,這近乎殘忍的舉動卻是當時的一大狂歡,人們從岸邊劃著小船興奮地歡呼著,凝神等待那些翅膀墜落在海中的人浮出海面。那時,不論他曾做過多么十惡不赦的事,離他最近的小船都會載他上岸,并賜予他新的名字——這意味著他獲得了新生。想來,這便是對太陽的一種信仰和崇拜——從海中升起又落下。人們相信,每天的太陽都是由阿波羅駕著金色馬車,擲下最嶄新的一顆,一個個黎明黃昏,就是無數個太陽的沉沒,大海就是太陽的墓地,不計其數的太陽在海底被埋藏起來。渺小的人從海面浮起,人們相信這是海神波賽東對他的寬恕,如太陽一般在海面升起,獲得新生。
也許,薩福站在崖頂時也作如此想。當落入海中的那一刻,所有的愛與恨,恩與怨,都歸于洶涌的波濤,正如她所寫的幾句殘詩,“我不要蜜蜂,亦不要蜂蟄”。她愿意將這一切交由大海決定。
法國有一位畫家曾畫過薩福。畫面是一大片黑白,薩福披著頭發,袒露上身,眼睛看向不知名的遠方,眸中透露出她對愛和自由的向往。她左手自然地搭在巖石上,右手蒼白無力地垂在身旁,手中還握著她靈魂和生命之所在——一架豎琴。它將陪她一起見證死亡或是新生。她的背后是一片海,可能是因為她的襯托,才顯得海面格外平靜。海的盡頭隱約能看到曙光初綻,也許是象征著她最后的希望。這樣的她讓我想起了希臘法庭上人們對她的控訴——不潔,行為放浪,給未成年人樹立了頹靡的范本。這一切只是因為她寫了向往愛情、自由和美好未來的詩。申訴時,她無奈地選擇了解開自己的衣服。她那美麗的身體照亮了一干長老們的眼睛,那一瞬間,男人們熊熊燃燒的敵意如春日的冰凌緩緩融化。他們突然不明白,為什么要判這個阿芙洛狄忒最虔誠的祭司的罪?在美的面前,他們不過如塵埃,蒼白無力地掩蓋自己齷齪的內心。是的,有誰能判“美”的罪,又有誰能判“愛”的罪!
如果不能判愛與美的罪,那么同樣也不能判詩的罪。她的詩是那樣脆弱、柔美,經不起一點打擊,需要用盡全力來維系那純粹的天真。薩福被宣布當庭無罪釋放。在這場荒誕的官司面前,薩福贏了,可是她所熱愛的詩和愛卻判了她的罪,逼著她在盧卡特的懸崖上投海而亡。
她應該是被羨慕的,是被那些不懂詩,卻用詩來裝點門戶的少女們所羨慕的。她們羨慕她裝點了詩,而不是被詩裝點,仿佛這一切是理所當然的,就應該和她融為一體。薩福也許不是詩人,她并沒有創作詩,而是在這冗雜的世間發現了詩。她說,它們僅僅是一絲氣息,聽我支配的話語是不朽的。這是她對情感和詩的敏感,也是她的驕傲。她說,我拿起七弦琴,說——現在來吧,我的神圣的龜甲,變成會說話的武器吧!如她所愿,龜甲變成了豎琴。但凡了解她的人必然知道,豎琴是薩福傳播世間所有美和愛的媒介,也是她生命和詩的延續。那么柔軟的詩出自她的筆下,不帶一絲做作,全然是自己對于愛和美的感悟,以至于因為她,我熱愛上了那片哺育了她的古希臘土地,以及流淌著她炙熱的愛的卡盧特懸崖下充滿悲情的海洋。
她孤單的靈魂沉寂在一段時光里,黑暗的抑或壓抑的暗黑。如果說,詩是戴著腳鐐的人眼前的一扇窗戶,那么薩福一定是窗外最干凈的芙蕖。該用什么去形容這樣的女子呢?柏拉圖曾贊揚道:“人都說九個繆斯——你再數一數,請看第十位:萊斯博斯島上的薩福。你看她的才華是公認的。”古希臘詩人阿爾凱烏斯也說過:“堇色頭發,純凈的,笑容好似蜂蜜的薩福啊。”她一個人在那座島上創立了自己的女子學堂,教授詩歌,以一己之力對詩歌進行改革,從而誕生了“薩福體”,可最后她卻輸給了詩歌和她向往的愛。
她沒有錯啊
從來錯了的都是生不逢時
晚星帶回了
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帶回了綿羊
帶回了山羊
帶回了牧童回到母親身邊
薩福的詩,就是柏拉圖口中的理想國,是大多數人夢中的烏托邦,那些優美婉轉的詩句讓我相信,有一天我們將不必做一個追風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