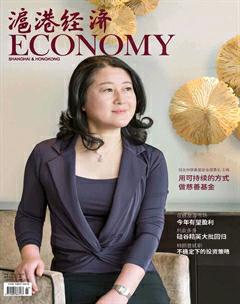機會多多硅谷精英大批回歸
邵玫
1月17日,百度宣布任命陸奇為百度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去年9月,陸奇從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職位上離開,這個被稱為“硅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離職引發業界廣泛猜想。他的去向確定之后,輿論頗為復雜,“華人敗走硅谷”、“硅谷的魅力正在下降,中國的吸引力正在上升”等各種議論不絕于耳。
近些年,中國互聯網快速發展。在硅谷精英中占比很大的華人,的確出現大規模回流現象。中國這個發展快速而潛力巨大的市場,正吸引著越來越多游子歸來。
中國科技企業的高管薪酬正與硅谷接近
早在2015年8月,美國科技博客TechCrunch網站就以“中國正在吸引來自硅谷的高管”為題刊文稱,對硅谷人才來說,為中國公司工作是既可行又極具競爭力的選項,因為中國科技企業的高管薪酬正與硅谷接近。該網站提供的數據顯示,在雇員超過1000人的企業中,擁有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員工級別越高,中美公司提供的薪酬越接近,例如初級工程師的稅前年薪分別為5萬和9.5萬美元左右,而總監及以上級別的年薪都在20萬美元左右。
禾賽科技創始人李一帆發現,自己回國的決定很容易做出,也很容易就得到了周圍人的理解。2014年,他辭掉了硅谷一家有名的公司的首席工程師職位,回國創業。
從硅谷回到國內,即意味著打破之前按部就班的生活節奏,開始適應“太快、太忙、太累”的國內互聯網行業節奏,但對這些人才來說,收入各方面也很有保證。中國互聯網行業為核心員工提供的薪資體系,早已和硅谷接軌,“現金+股票/期權”這樣的待遇,越來越具有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中國出臺了一系列引進國際人才的政策,大力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和急需緊缺人才。2012年,中國又實行“萬人計劃”,同年9月,中央25個部門聯合印發了《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享有相關待遇的辦法》,試點改革綠卡、居留、簽證以及出入境制度,進一步降低海外人才獲得中國“綠卡”的門檻,提升綠卡待遇,為“人才回流”提供了各種便利。
在組織部的高度重視和推動下,各地紛紛建立人才辦,結合自身實際,出臺各種人才政策,如北京的“海聚工程”、湖南的“313計劃”、蘇州“姑蘇人才計劃”、無錫“530”人才計劃、杭州“5050計劃”等。隨著各項人才計劃的開展,人才的開發和培養工作、專業人才的管理、人才吸引平臺的搭建等各項工作陸續展開;留學創業園、海創園等吸引各類人才發展的新載體紛紛出現;創業平臺、資金、信貸、稅收等人才發展所需的推動政策也逐步完善。
提高薪酬正是中國公司努力吸引硅谷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科技行業資深觀察人士孫永杰表示,以阿里、百度、小米等為代表的中國高科技企業都面臨國際化問題。從企業發展戰略上來講,他們需要從國外,尤其是美國高科技企業引進高管人才。高速發展的中國科技企業不僅為硅谷華人高管提供廣闊的職業發展前景,而且還提供豐厚的股權回報等現實利益。相形之下,一些外企近年發展并不如意,如戴爾、惠普等發展不如以前,導致很多中高層管理人員紛紛跳槽中國企業。
除了企業的積極招攬,中國的發展大環境也成為吸引硅谷人才的重要因素。TechCrunch網站說,盡管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嘀咕聲”不斷,但其發展引擎仍在連續高速運轉,6年來穩定在6.5%以上。與此同時,高素質員工的供給難以滿足市場需求和增長。
“美國政治環境的變化,也有可能導致華人高管回歸。”孫永杰提出另外一種可能,“特朗普近日簽署的有關難民、移民的禁令已體現出其保守傾向,不排除以后還有其他政策會限制華人流動。與其在外受排擠,為何不考慮回來呢?”
回國窗口期不容錯過
與當初中國互聯網近乎“一窮二白”的場景不同,今天中國已經既有BAT這樣的互聯網巨頭,也有遍地開花的創業公司。精英們在硅谷獲得的技術創新領先優勢,回到國內有著很大的用武之地。
僅從幾家巨頭招攬的人才質量就可見一斑。百度已經將一大批頂尖硅谷技術專家招至麾下,如斯坦福大學副教授、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權威專家吳恩達,Facebook前資深科學家徐偉,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統計學教授張潼,異構計算專家、AMD異構系統前首席軟件架構師吳韌等。螞蟻金服同樣如此,首席數據科學家漆遠是麻省理工博士、前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人工智能部總監盛子夏是卡內基美隆大學博士、曾就職于Discovered Card,研究員俞本權此前是谷歌高級主管工程師。而在騰訊、華為、360等企業,來自硅谷的人才同樣比比皆是。
多個國際獵頭認為,對于硅谷精英來說,最近這幾年的回國窗口期不容錯過。中國互聯網產業發展速度極快,很可能會“時間不等人”。
人才服務公司GCP(Global Career Path)合伙人Timothy Li認為,硅谷技術海歸的優勢最多只有未來3至5年。在他看來,雖然中國之前一直在學習硅谷模式,然后進行微創新,但很快會迎來質變,在很多方面超越硅谷。
中國未來或可以有多個硅谷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認為,中國已崛起為世界最大電商市場和移動互聯網服務創新的領軍者。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顯示,在2015年全世界290萬件專利申請中,中國約占100萬件,而美國僅為52.6萬件。在這樣的創業環境中,深圳被廣泛視為“中國的硅谷”。在麥肯錫董事華強森看來,高科技人才發揮才能的地方已絕不止深圳一個城市。他認為,從經濟層面而言,中國并不是一個“同質體”,每個大城市都可以“獨立運轉”。鑒于各個城市的龐大規模和差異,“我看不到中國未來為何不能有15至20個硅谷的理由”。
去年5月,美國互聯網精英羅丁(Cyriac Roeding)來中國考察創業環境,三周后,他的結論是:未來幾年,北京是美國硅谷唯一真正的對手……北京的企業家精神看上去就像是新生的、有時甚至是更純粹的硅谷。endprint

羅丁認為,北京不止會成為一個有趣的創業樂園、一個巨大的創業聯盟,而且把企業家精神和創業者對擴張規模的渴望結合起來了。“北京是主要的創業中心,中國頂級高校北大、清華的工程天才們與風投在此相會。看到這里的規模、速度、抱負、資本和人才,我認為,未來十年,這里將是硅谷的真正對手。”
他還說,在中國,3~5年就能建立大創業公司,在美國需要5~8年。創業者們都希望能借助成功的理念,努力、盡快地超越對方。
也不光是北上廣這樣的特大城市,杭州、成都、南京甚至一些二三線城市,都成為硅谷精英們的“淘金”之地。以杭州為例,這個去年剛舉辦過G20峰會的城市,已經有了阿里巴巴及其旗下的螞蟻金服等一眾世界領先的企業,人工智能產業也已走在全國前列,成為中國科技創新的重鎮。烏鎮智庫發布的《FINTECH2016:世界與中國》、《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6)》顯示,杭州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企業均已超過廣州,形成“北上深杭”新格局。
不少城市已然意識到這股潮流,并想盡辦法吸引來自硅谷的人才到那里安家落戶。例如,此前南京組織過專門的硅谷創業人才懇談會,成都則專門設立了對接硅谷高端創新項目的高新孵化器。
從硅谷帶著51支創業團隊回到中國的硅谷高科技創新創業高峰會創始人、執行主席雷虹感慨地說,即使到了成都,她也“感覺整個城市都動起來了,遠遠超出想象”。這樣的現象,在當下的中國絕非孤例。
做國外“想做而沒做到的事”
薪酬之外,更應看到海歸潮背后的事業空間“誘因”。以金融科技為例,事實上,中國作為傳統金融產業后發國家,監管部門明智地對行業采取了包容態度。這導致以金融科技+金融場景生態為核心的新金融產業在中國迅速崛起。無所不在的便捷移動支付,結合電商、O2O、消費金融創造出來的廣闊新金融產業空間,都給這個行業帶來了超越全球的想象力。
業內人士分析,這波以互聯網精英為主的歸國潮,開啟于中國移動互聯網及創業井噴初中期,也就是2013年、2014年左右,國內的互聯網平臺、服務、產品,以及構建的生態、用戶數量、商業機會等,迅速趕上甚至超過國際先進水平。中國互聯網巨頭的業務場景和用戶不僅開始布局全球,而且創下一個又一個世界第一。
在技術能力上,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中國自主研發的操作系統,開始打破IT核心技術長期被歐美壟斷的局面,中國最前沿、最具創新的技術能力,集中出現在互聯網公司。這為硅谷人才回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盛子夏分析說,以前我們總有一個慣性思維,要做什么事就先看看歐美、日韓是怎么做的,之后“Copy to China(復制到中國)”,如今我們已然成為被復制的對象。他舉例說,支付寶實名用戶4.5億,全球第一;滴滴打車用戶3億,全球第一;騰訊社交平臺總用戶數,全球第一……
“以螞蟻金服為例,我們做成了全球金融機構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把金融變得像可樂一樣,無論貧富、國籍、城鄉,都能享受同樣的服務。”說起這些,盛子夏不無驕傲。
而關于中國互聯網的未來可能性,還有諸多更為樂觀的預計。近兩年,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發現,在跟哈佛、斯坦福等名校留學人員交流時,他們表達的回國創業意愿越來越強烈。“中國創業的黃金10年已強勁啟動,經濟在持續增長,留學人員回國創業面臨廣闊的市場,機會無限,未來可期。”
互聯網科技企業最需要的市場、技術、人才要素,中國現在已經完全具備且難以被媲美。
硅谷仍具吸引力
不過,在中國工作是個不錯的選項,并不意味著硅谷的吸引力在顯著下降。“選擇回國的中國工程師,通常在硅谷有10年以上的工作經驗,他們的職業發展遇到了瓶頸,因此希望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在方亮看來,“硅谷的多樣性強,具有技術創新土壤,仍然是業內人士的朝圣之都,處于事業上升期的人都渴望過去”。方亮2006年獲得美國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后,曾先后就職于硅谷多家知名高科技公司。2015年秋天,他看到國內互聯網金融市場的空白,并考慮到個人職業發展,選擇回國。
對于中國國內的技術創新領域“生態圈”,方亮也有他個人的看法。他認為,很多國內公司如今在技術創新上建樹不多,喜歡跟風,這一點跟硅谷不同。另外,國內喜歡過多強調某個公司想做什么,硅谷則是一群公司共同做某件事,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不同角色。“在競爭方式上,硅谷比較常見的是良性互補,但國內更多的是同質惡性競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