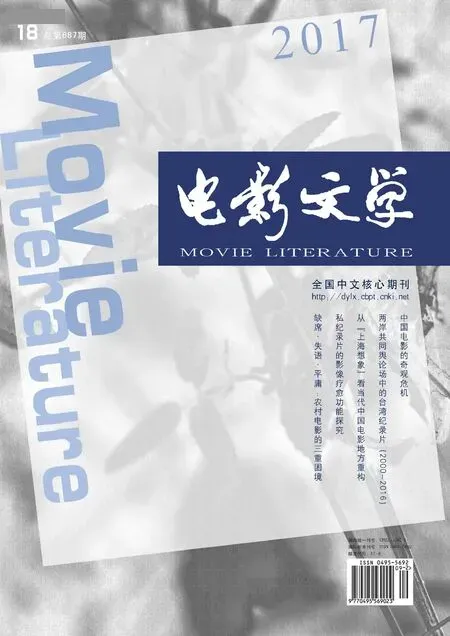私紀錄片的影像療愈功能探究
李 姝
(成都大學美術與影視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6)
一、IDOCS為私紀錄片站臺
2016年的IDOCS(國際紀錄片論壇)是由北京零頻道發(fā)起創(chuàng)辦,北京電影學院承辦,中國第一個獲得官方合法許可的獨立紀錄片國際電影節(jié)。IDOCS自2009年首次舉辦,至今已成功舉辦5屆。它以智利導演顧茲曼的話“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作為信條,以“眼界改變世界”作為口號,將全世界頂級電影節(jié)和紀錄片頻道中收獲贊譽的最新、最優(yōu)質的作品帶入中國。最近這一屆IDOCS2016展映的作品,無一例外地紛紛把目光投向了個人與家庭,關注隱秘的自我、罕為人知的關系和難以言說的創(chuàng)傷,在為期6天的展映活動中,數(shù)十部來自世界各地的“私紀錄片”給人帶來了如同宗教洗禮般的情感震顫。
近年來,“私紀錄片”作為舶來品,越來越多地進入大眾及學術的視野。
例如,在[日]那田尚史《日本私紀錄片的起源與現(xiàn)狀》(2007,李瑞華譯)、韓鴻《民間的書寫:中國大眾影像生產(chǎn)研究》(2007)、樊啟鵬《中國私紀錄片帶來的變化與挑戰(zhàn)》(2007)、徐亞萍《通往真實的自我——中國私紀錄片研究》、于潔與關大我《中國私紀錄影像的風格探析》等國內(nèi)外一些學者和研究者的專著及文章中,我們窺見了私紀錄片的緣起和基本發(fā)展脈絡。以揭露記憶創(chuàng)傷、暴露個人隱私、展現(xiàn)隱秘關系、宣泄內(nèi)心情感為特征的私紀錄片(亦稱第一人稱紀錄片)為我們勾勒了一幅獨具魅力的人類精神世界畫像。日本電影導演今村昌平在他的代表作《鰻魚》(1997)中曾提出這樣的觀點:現(xiàn)代社會,人人都有心理暗疾。人們在飛速發(fā)展的工業(yè)化時代,面對龐然大物般的樓宇和機械,身處大興土木沸騰不休的土地,在舟車勞頓、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被短平快的節(jié)奏捆綁,被喬裝打扮后的快餐文化吞噬,被各種人類自身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異化。虛擬的世界和現(xiàn)實的世界戾氣橫行,越來越多的孤獨靈魂成為行尸走肉。然而,在優(yōu)秀的私紀錄片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個體經(jīng)歷,也看到了社會整體。這些家庭故事背后私密的情感和人際關系,幫助我們整合了各自的生命沖突與體驗,同時獲得了一種更高級的對人類群像的認知與人性反思,從而達到一種類似心理治療效果的自我救贖。
二、私紀錄片與影像療愈
最早把電影藝術與心理治療結合在一起進行探討和研究的是法國著名符號學家麥茨(Christian Matz)。他成功地把20世紀西方人文科學的成果和思想結晶運用于電影理論研究中,并做出許多極其重要的理論建樹。麥茨認為,電影就是與人的“力比多”①打交道,即表達人的欲望和訴求。電影通過聲畫手段,刺激大腦的神經(jīng)元,調度眼耳舌身意等感官統(tǒng)覺的整體反應,從而勾連起人們的潛意識和記憶,最終通過壓抑的釋放、宣泄、投射、移情、替換、同一化等方式對觀看者的心理活動機制產(chǎn)生影響。
目前,從19世紀的古典精神分析學開始,隨著弗洛伊德的理論在世界范圍內(nèi)得到廣泛接受,心理治療在一百多年的歷程中逐漸拓展出以繪畫、音樂、戲劇等非語言表達的方式,即藝術治療。藝術治療作為心理治療的分支及重要的治療方法,因其與患者達成更廣泛、深入、靈活的溝通,從而更好地實現(xiàn)潤澤心靈、凈化情緒的效果。藝術治療在當今西方社會已得到承認并在一些高校及研究機構成立了專門的藝術治療專業(yè),建立了藝術治療師的資格培訓體系。
也許是世紀之交的普遍性生存焦慮和對人類未來的恐慌,步入21世紀前后,突然興起了一股主觀敘事的非虛構影像創(chuàng)作熱潮。無論是自傳體紀錄片《我的建筑師—— 一個兒子尋父之旅》(MyArchitect:ASon’sJourney,2004)、引起巨大爭議的動畫紀錄片《與巴什爾跳華爾茲》(WaltzwithBashir,2008),還是中國的獨立紀錄片《不快樂的不止一個》(2000)、 《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2001)、 《家庭錄影帶》(2001)等,都引起了國內(nèi)外學術界的關注。美國紀錄片學者保羅·亞瑟稱這種“以公認的、隱含的、心理治療手段的方式來建構”的影片為“治療紀錄片”。在這些往往以非商業(yè)化和國際化作品為主的“治療紀錄片”中,導演大都在講述心理創(chuàng)傷事件、家庭秘密或尚未愈合的感情傷痕。這種近20年來逐漸興起的紀錄片亞類型和本文所講的私紀錄片在創(chuàng)作理念上高度重合,以私紀錄片開啟的第一人稱紀錄片敘事“為這個難以抑制的自我書寫時代建構了一個新的范式”②,對紀錄片至高無上的“真實觀”也起到了顛覆性的闡釋和重構作用,為影像文本的創(chuàng)作開啟了嶄新的“抵達心理真實之境”的路徑。
三、從IDOCS看影像的藝術療愈:從被動觀看到主動攝制
在跨學科的視野下,當今的心理咨詢過程經(jīng)常會使用影像資料來對來訪展開討論,“幫助其修通無意識情節(jié),并產(chǎn)生新的領悟”③。但國內(nèi)的相關研究尚不系統(tǒng),目前還缺乏對電影療法的理論體系建構。然而,本屆IDOCS 2016論壇的所有紀錄片作品均鎖定“家庭:愛與療愈”這一靶心,影片的制作者們通過參與攝制,變被動等待為主動干預,為我們展現(xiàn)了暗淡、苦悶、焦灼的常態(tài)人生中一絲明媚新生活的可能。
參展影片《暮年之光》(TwilightofaLife,2015比利時Docville國際紀錄片節(jié)最佳影片),以兒子(導演)的口吻描摹年邁的母親,以兒子的視點觀察母親晚年的形象,以極簡主義的畫風(兩個人、一間房、一張床和一把椅子)構建了一部以“死亡”為題卻充滿歡歌笑語、幽默詼諧、睿智如詩般的生命故事。經(jīng)歷過大屠殺歷史的母親多年來一直保持緘默,與兒子之間缺乏溝通使得彼此的誤解與傷害成為生活的主角。攝影機的出現(xiàn),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嘗試打破二人的沉默,攝影機作為觸媒促成了自由的對談,另一種語言——愛撫代替了分別之時的哀傷,使得影片閃爍著迷人的光芒。
參展影片《公寓》(TheFlat,2013波蘭猶太主題電影節(jié)金鳳凰獎)以“我”(導演)的視角探尋即將搬遷的廢舊家庭公寓中隱藏的家族秘史,在調查歷史遺物和外祖母復雜的人物關系中逐漸揭露出大歷史的悲慘和戰(zhàn)爭對人性的壓抑。影片最激動人心和引人入勝的地方在于抽絲剝繭的過程中浮現(xiàn)的隱秘情感和跨越敵我界限的人性之光。
參展影片《全家福》(AFamilyFair,2015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節(jié)荷蘭紀錄片單元評審團特別獎)同樣以“我”(導演)的角度闡釋了親祖母謎一般的人生圖譜。風華絕代卻被外界評議為蛇蝎美人的祖母意外地對自己表白,突如其來的情感背后隱藏的是祖母童年時的家庭創(chuàng)傷與伴隨終生的厄勒克特拉情結。④祖母父親對她的苛責使其一輩子活在自卑的陰影下,穿梭于無數(shù)男人之間以尋求愛的補給。孫子與祖母的這場對話最終解開了影響四代人生活的謎團——愛的缺位與自我的迷失。
參展影片《曾經(jīng)的母親》(OnceMyMother,2013澳大利亞電影協(xié)會最佳紀錄片獎)通過“我”(導演)對曾經(jīng)眼中“背叛”自己的母親的“審問”,通過拍攝之旅檢索她與母親陷入困境的根源。面對日漸蒼老、陷入癡呆的母親,導演蘇菲最終發(fā)現(xiàn)心魔的癥結是戰(zhàn)爭的殘酷以及人對自我的寬恕。
參展影片《當我們靠得更近》(TheCloserWeGet,2015Docs國際紀錄片競賽單元最佳紀錄片)以“我”(導演)的勇氣、坦誠、溫暖,講述了一個關于忠貞、夢碎和心靈救贖的故事。身患中風臥病在床的母親為全家人的團聚帶來契機,也讓導演時隔多年之后拿起攝像機首次探尋父母不為人知的婚姻秘密。父親的雙重丈夫身份背后隱藏著人性的欲望,而影片也讓我們看到了更廣泛的兩性情感維度以及家庭如何重獲新生的非凡故事。
上述幾部是IDOCS 2016論壇眾多參展私紀錄片中的優(yōu)秀代表。從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對母子、父女、祖孫、父親關系的探討,都是從“私人的”、第一人稱角度進行審視。攝影機變成了“我的世界”解碼器:從“我看”到“我說”,從傳統(tǒng)紀錄片的“聽你講故事”變成了“我來講述我的故事”。這種自主的表達和鏡頭前毫不避諱與被攝人物的互動對談促進了自我反省,也幫助被攝者揭下人格面具;滿足了觀眾窺探隱私的快感,也幫助當事人宣泄釋放內(nèi)心的苦痛、從而滿足心靈的慰藉。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Alain de Botton)在新書《藝術的慰藉》(ArtasTherapy)中提到現(xiàn)代社會人類的各種心理缺陷以及藝術的治療功能,他把藝術比喻為新宗教,指出了藝術對人生困境具有很好的解釋和療愈效果。
美國紀錄片學者比爾·尼科爾斯(Bill Nichols)在對當代紀錄片進行劃分時提出了基本的6種紀錄片形態(tài),即詩意型(Poetic)、闡釋型(Expository)、觀察型(Observational)、參與型(Participatory)、自我反射型(Reflexive)以及表述行為型(Performative)。上述的私紀錄片作品很好地融合這6種方式,常規(guī)紀錄片先知和全能的旁白替換成導演“我”的自述或獨白、從主觀視角展開搜尋、自由出入畫面與被攝對象自由探討、將隱秘的內(nèi)心世界及不可言說的欲望進行詩意再現(xiàn)。“我”既是觀影者、窺視者、受害者抑或自戀者,同時也是創(chuàng)作者、催眠者、講演者和被治療者。私紀錄片的“私”既是主觀的“我”的闡釋內(nèi)心,又是私密親密關系中創(chuàng)傷與苦痛得以釋放的關鍵。通過影片的攝制,每一個“我”重新發(fā)現(xiàn)了自我,重塑了正念人生。
在網(wǎng)絡直播泛濫和手機游戲成癮的當今社會,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高校青年學子,常常面對迷茫卻難以自拔。高校的影視賞析和美育教育如果能結合私紀錄片力量,通過紀錄片拍攝來走進家庭關系,對自我和關系親密的人進行重新認知,也許能增進對生命的感悟和對人性的體察。正如龍應臺在《大學里沒教的兩件事》中寫道:第一,大學教你如何與別人相處,沒有教你如何與自己相處。第二,大學教育了你如何認識“實”,但沒有教你如何認識“空”。作為人生高級階段的學習之旅,大學教給了我們各種實用的技術和知識,卻囿于各種限制沒能培養(yǎng)學生認識自我的能力和獨立思辨的智慧。希望更多的專業(yè)認識能夠借助藝術心理學等跨學科研究的推進,讓私影像之光照亮無數(shù)身處困境的靈魂,讓愛溶解疾苦,用溝通潤澤心靈。
注釋:
① 力比多,拉丁文libido的音譯。精神分析學認為,力比多包含一切身體器官的快感,指人的本能欲望,心理現(xiàn)象發(fā)生的原始驅動力。
② [美]保羅·亞瑟:《影像的救贖:自我治療紀錄片》,孫紅云、汪亦紅譯,《世界電影》,2013年第5期。
③ 張愛寧:《觀影療心——電影在心理咨詢與治療中的應用》,華東師范大學,2008年。
④ 厄勒克特拉情結(Electra Complex),即戀父情結,精神分析學中解釋為女兒親父反母的復合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