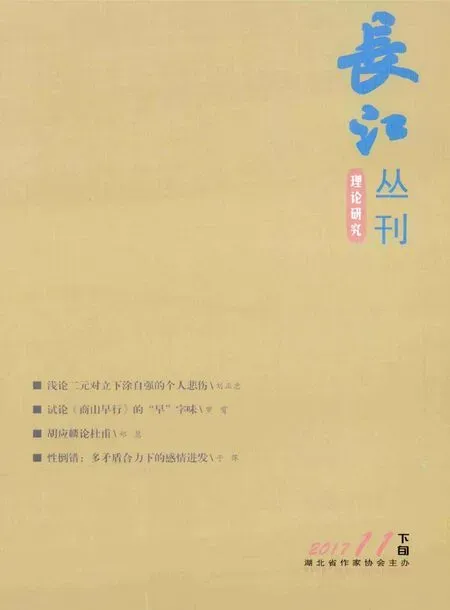“比較”以致“貫通”
——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比較研究
高一品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談及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首先,要搜集、審定、整理史料,進而將各家學說梳理為有條理、有系統的哲學,至此,即為“述學”,在此基礎上,依時代順序研究各家之間傳授的淵源、交互的影響、變遷的次序,此為“明變”,進而探究此種傳授、交互、變遷的原因,即“求因”。最終以各家學說的影響效果判別其價值,即“評判”。
而本文論述主要圍繞胡適在整理史料過程中“貫通”功夫所需要的以西方哲學思想作為材料對中國哲學史進行理解的方法。胡適認為,在哲學史研究中如果不注重對史料的校勘與考據而只注重義理的闡發和思想整體脈絡的貫通則會流于空疏,流于主觀臆測的臆說。而如果只注重訓詁考據等,例如清代乾嘉學派,而不注重貫通的功夫,則會流于支離,缺乏對思想體系的完整性認識。可見,貫通功夫的重要作用。而此種貫通的實現則要通過超越研究內容及其體系本身而選取、借鑒其他材料及方法進行比較才能獲得關于其研究內容本身的整體性、全面性的認識。我們只有通過比較研究內容與西方哲學的參考資料,使二者之間相互印證、相互發明才能理清研究內容的條理系統。
一、《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研究方法論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多使用西方哲學概念類比中國哲學的范疇。例如,在對老子的分析中,其以西方哲學的自然法(Law of Nature)類比老子的“天道”,以斯賓塞的政治學說說明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政治理念;在對孔子的分析中,以蘇格拉底的“概念說”類比孔子的“正名”思想以說明此正名主義是中國名學的始祖,以康德“感覺無思想是瞎的,思想無感覺是空的”一句類比孔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證孔子理論中學與思相互依存的關系,并補充說明,二者比較之下也存在差異,不同于康德作為直接經驗的感覺,孔子的“學”是指讀書,通過傳授而獲得的間接經驗。此外,胡適在論述《論語》中關于道德的問題時,將道德分為內容與外表,而注重內容的道德又分為康德的“道德律令”與宋儒所主張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天理”。在對墨子的分析中,胡適將墨家的“巨子”類比為歐洲中古的“教王”,以說明天志尚同的宗旨是在政治組織之上設立一個統一的“天”。在墨家的“辯”中,胡適以西方邏輯學中的“主詞”說明“實”,以“表詞”說明“名”,而名與實的結合即為“命題”。在說明以上基本概念后,胡適又以維恩圖表示種屬關系說明作為歸納推理與演繹推理基礎的“類”的概念。在演繹法中以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作為比較對象,“凡‘人’皆有死,孔子是一個‘人’,故孔子必有死。”[1]在《經上》中,“物之所以然”是“故”,凡正確的故都可以作為法,若不能發生同類的效果則只說明不是正確的“故”。可見,名學的演繹法是根據“同法的必定同類”的原則進行,將已知之故作為前提。因而,《墨辯》中的演繹法不同于亞里斯多德三段式的演繹法,其以“人”為孔子的類名,是介于“名”與“實”之間的,等同于西方邏輯學中的“中詞”,其認為大前提中的意思已經包含在小前提之中,大前提的作用只是說明小前提的“人”,是介于“孔子”與“有死的”兩詞之間的“中詞”,所以已經小前提已經可以滿足要求,無需三段論的架構。通過與其他文明中的傳統邏輯學的對比,胡適認為,相較于墨家名學,印度因明學改古代的五分法為三支,只剩余演繹的方法而喪失了歸納的精神,而歐洲中古的哲學缺乏創造性,只是擴充古希臘邏輯的形式,使其逐漸脫離亞里士多德的本意。因此,胡適認為,中國古代的墨家名學兼重演繹與推理,有其自身的重要特性。
可見,胡適多以西方哲學的概念類比中國哲學思想,既使得中國哲學思想更易于理解,使得中國哲學史更具體系性,更為貫通,也使得中國哲學自身的思想特色得以彰顯。
實際上,此種借鑒吸收西方哲學思想作為材料與中國哲學思想進行比較以彰顯中國哲學思想特色的方法可歸結為“以西釋中”,而胡適此種開新紀元、開新風氣的方法被后世所傳承。
二、《新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論
勞思光同樣贊同以西方哲學的方法詮釋中國哲學思想史。勞思光認為,胡適在對中國哲學史的書寫中主要注重史料的考證辨別,“大部分工作都是用于考訂史實”,“卻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闡釋”。[2]實際上,胡適多以西方哲學作為內容、材料以述說中國哲學史,而相較于胡適,勞思光多以西方哲學的方法論述中國哲學的材料,將西方哲學的方法作為工具處理中國哲學的問題。其以歐洲近代發明的顯微鏡可觀察非洲古代已產生的細菌并以此解釋疾病發生的真相說明西方哲學的解析方法與邏輯論證可打破時空的界限應用于中國哲學史的論述。在論證運用西方哲學解析中國哲學史的正當性的基礎上,勞思光強調,不能認為在邏輯解析方法下所發掘的思想只能出現在邏輯解析方法產生之后,顯微鏡發明以前細菌已存在,“思想上的顯微鏡”出現以前,思維規律一樣存在。
因此,勞思光在《新編中國哲學史》中以西方哲學中的形式邏輯等解析中國哲學史,發掘其中已存的義理,使其體系內部相貫通。例如,在論證仁、義、理三者的關系時,勞思光以邏輯數學說明在理論程序上,禮以義為其實質,義以仁為其基礎,在實踐程序上,理與義相連,不能分別實踐。在理論程序上,“求嚴格之意志”、“思考之嚴格性”,“演算中之嚴格論果”是三個不同層次的觀念,即仁、義、禮三個概念相區分。而實踐程序上,思考必依據符號而進行,“思考之嚴格性”需要通過“演算中之嚴格論果”得以顯現,因而二者不可相分離,即義與禮不可分離。
此外,勞思光以形式邏輯論證孔子的“君君臣臣”并不能說明其擁護封建制度。其認為,君君臣臣只具有形式的意義,未論及“君”與“臣”各自權利與義務的具體內容,只是表示“權分”的理念,如同邏輯學家說明“A是A”、“B是B”時,只表明A與B自身的同一性,而未涉及A與B的具體內容。因而,君君臣臣只是說明“權分”本身必須遵守,并未劃分具體內容,不能說明其中是否存在專治,也不能說明其體現了不同階級的存在。孔子以“君”、“臣”等詞只是為構成其陳述形式,只是指不同的職分,說明不同職分應各盡其職,認為其擁護封建專治社會實為對孔子的誤解。
可見,勞思光以西方哲學的邏輯解析方法分析中國古代思想,理清其中的義理的涵義,使其體系內部相貫通。但其認識到,思維規律的運行與人們能自覺其存在是不同的,因而以西方哲學的方法分析中國哲學的內容或以西方哲學的概念類比中國哲學的范疇都應存在一定的界限,不能對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進行過度解讀,將古人“現代化”。
三、“以西釋中”方法論的界限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研究中國哲學,解讀中國哲學史成為一種主流。1957年1月北京大學哲學系召開了“中國哲學史問題座談會”,該會議討論的核心是研究哲學史的方法論。參加會議的成員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學科上橫貫中、西、馬,其中包括馮友蘭、金岳霖、賀麟、洪謙、鄭昕、周輔成、張岱年、任繼愈、汪子嵩、艾思奇、侯外廬、關鋒等。實際上,此次會議展現了一種“哲學史方法論上的修正主義”[3]。此種哲學史研究方法會使人產生一種誤解:哲學史研究只是闡述唯物主義如何戰勝唯心主義的過程。其忽略了唯心主義哲學流派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忽視了歷史上唯心主義存在的歷史必然性和其認識論的根基,忽略了社會歷史觀的維度。并且當時此種風氣導致了一些學者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對中國哲學史進行過度解讀。例如,《周易》的作者已自覺或不自覺的意識到“對立統一”、“矛盾轉化”等辯證法的規律以及“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而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概念,指人的社會實踐,這種社會實踐活動包括人類為從自然中獲得物質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生產斗爭,也包括階級社會中各階級為奪取經濟利益而進行的階級斗爭,同時還包括社會實踐。而早在《周易》時期人們的認識能力和思維水平是無法達到這一高度的。可見,盲目運用西方哲學的方法解讀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并將許多現代的思想安排在古人名下,是一種荒謬的行為。因此,“以西釋中”的方法論需要一定的界限,才能保證古代思想內容的客觀性而不流于解讀者的主觀臆想。
因此,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我們既要學習胡適、勞思光等引進西方思想與方法解讀中國傳統思想,發掘其中義理,使得中國哲學史自身相貫通,也要為此種解讀方法劃界,將思想置于其自身所產生的時代進行理解,遵循哲學史進程中嚴格的歷史性,最終建立一套理論的設準,統攝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特顯中國哲學自身的思想理論特色,表明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中的地位與意義,使得“哲學在中國”發展為“中國的哲學”。
[1]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79.
[2]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2.
[3]關鋒.反對哲學史方法論上的修正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