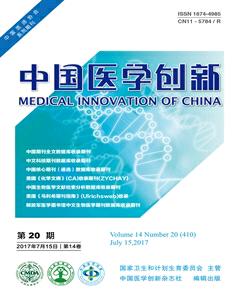動力導向團體心理治療對大學生抑郁情緒干預效果的研究
熊梨花+李玉美+高镕+嚴薔薇
【摘要】 目的:探討動力導向團體心理治療對大學生抑郁情緒的干預效果。方法:選擇120例在校大學生,分為動力導向心理治療組和問題導向心理治療組,每組60例,每組再分為5小組,每小組12例。兩組分別采用動力導向和問題導向團體心理治療方案,針對抑郁情緒進行干預。于干預前、干預結束時及干預結束3個月末,采用Beck抑郁自評量表(BDI)和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進行效果評定。結果:動力導向團體心理治療組BDI的各項得分均顯著低于問題導向團體心理治療性組,而RSES得分顯著高于問題導向團體心理治療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結論:動力導向團體心理治療可有效改善大學生的抑郁情緒、提高大學生的自尊水平,從而提升大學生的生命品質。
【關鍵詞】 動力導向; 團體心理治療; 抑郁情緒; 大學生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power-oriented group psychotherapy on university students depression.Method:A total of 120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power-oriented group and problem-oriented group,60 cases in each therapeutic group,each group was divided into 5 groups again,12 cases in each group.Two groups were respectively treated with power-oriented and problem-oriented therapeutic group counseling programs,interventions for depression.Before the intervention,in the end of the intervention and three month end of the intervention,Beck depression self rating scale(BDI) and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RS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effect.Result:The scores of BDI in all factors of power-oriented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problem-oriented groups,and the scores of RSES of power-oriented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roblem-oriented groups,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Conclusion:Power-oriented group psycho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university students depression and their self-esteem level,so a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Key words】 Power oriented; Group psychotherapy; Depression; University students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Yichun,Yichun 336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7.20.035
抑郁是造成大學生自殺的主要原因之一,29%的大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狀況,其中20%為輕度抑郁,7%為中度抑郁,2%的大學生存在重度抑郁[1-7]。
針對大學生的抑郁情緒,絕大多數心理工作者以問題導向為理論依據,開展情緒管理團體心理輔導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學生的情緒,但容易復發。為促使大學生更好地習得情緒管理能力,提升大學生的生命品質,本研究以動力導向為理論依據,針對大學生抑郁情緒開展團體心理治療,并進行對照研究,取得了一定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5年3-12月宜春市某高校符合納入標準的在校大學生120例。納入標準:(1)Beck抑郁自評量表評分≥8分;(2)自愿參加、有自我改變的強烈愿望、愿意與他人交流;(3)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語言溝通障礙、嚴重精神障礙疾病以及嚴重軀體疾病者。其中男56例,女64例,年齡17~22歲,平均(19.7±1.2)歲。所有患者分別按訪談順序編號,編號為奇數者納入動力導向心理治療組,編號為偶數者納入問題導向心理治療組,每組60例,兩組性別、年齡結構及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小組設置 兩組均按12例組成一小組,各5小組;每小組每周一次團體心理治療活動,120 min/次,共10次。
1.2.2 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目標 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旨在通過團體活動,引導小組成員多視覺探索早期創傷體驗對負性自動模式形成的影響,陪伴小組成員重新體驗過去的創傷體驗,鼓勵其帶著覺知去宣泄早年創傷體驗帶來的壓抑情緒,以全新的角度處理過去和現在的關系模式,構建積極認知模式,激發學員學會從過去的經驗中發掘心靈成長的動力和源泉,從而有效改善抑郁情緒,促進心靈成長。endprint
1.2.3 問題導向治療性團體目標 問題導向治療性團體旨在通過團體活動,促使組員自由表達自我、探索自我,增強組員對自己、對他人負性自動思維模式的覺察與認知,逐步建立積極的應對模式、激發組員對生命的熱愛之情。
1.2.4 團體治療的實施
1.2.4.1 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的工作實施 共10次活動,分為3階段:關系建立階段(由1次團體活動時間完成)、主題實施階段(由8次團體活動時間完成)、結束階段(由1次團體活動時間完成)。(1)關系建立階段(第1次活動):運用“群體動力學”理論[8-13],通過心理游戲讓組員彼此相識、彼此認同,消除溝通的障礙,營造真誠、溫暖、關心、理解、支持、陪伴的團體氛圍,讓組員之間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使個體克服恐懼、焦慮心理,建立安全感,引發其參加團體的興趣和需要。(2)主題實施階段(由第2~9共八次活動完成):①第2~4次活動形式為意象對話團體輔導方式:第2次活動目標為引導成員覺察自己的情緒和心理沖突,積極應對現實困境與壓力。第3次活動目標為引導成員了解自己內化的原生家庭模式,促進自我探索與心靈和諧。第4次活動目標為引導組員了解當前的心理總體狀況和情緒特征,并在潛意識層面修復心理創傷。②第5~7次活動形式均采用系統排列方式,每次活動的目標如下:a、引導組員呈現心理沖突與案主和父母關系的模式,尊重與承認家族中事實的原貌;b、引導組員認識情緒與行為背后的深層動機;c、引導組員理解、尊重、接納父母,接受現實,活出真我;e、喚醒愛的智慧,從中學習生命給我們的功課,不再無意識地受傷悲痛;f、引導組員透過承認與感謝,并讓過去的經驗化為內在的力量,把自己從傷害中釋放出來,擺脫限制,更好地面對和處理困境,在困境中獲得成長的力量。③第8~9次活動形式為格式塔團體治療,活動目標依次為:引導組員從自身去發掘心靈成長的源泉,學會揭開生活的面紗,去發現其中潛隱的智慧,無論是痛苦還是歡樂,都是豐盛生命的資源。(3)結束階段(第10次活動):讓成員共同分享在團體過程中關于自我成長的收獲,并鼓勵成員把它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并在實踐中互相鼓勵、互相幫助。
1.2.4.2 問題導向治療性團體的工作實施 問題導向治療性團體活動過程:(1)團體開始階段:用兩次活動時間來完成,第一次團體目標為相識、簽訂團體契約,建立組員之間的信任感;第二次團體目標為相知、自我探索,為組員在團體情境中打開心扉做鋪墊。(2)團體工作階段:用七次活動時間來完成,團體活動主題依次為:我是誰、我的社會支持系統、感恩生命、生命的終止、價值探索(2次)和我的人生我做主。團體目標為在團體情境中借助心靈游戲引導組員進行理解自我、珍愛自我、探索和尋找生命的價值,制定人生規劃。促使組員積極面對挫折,激發組員對生活的激情,引導組員珍惜親情,珍愛生命、接納自我。(3)團體結束階段:鞏固團體治療效果,處理離別情緒。
1.3 觀察指標與評定標準 于入組前、干預結束時,干預結束3個月末各用Beck抑郁自評量表(BDI)和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進行一次效果評定。(1)Beck抑郁自評量表(Beck depressionrating scale,BDI)由美國著名心理學家Beck AT編制[14],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由13個項目組成,各項均為0~3分四級評分,無癥狀=0分;輕度=1分;中度=2分;嚴重=3分。分數越高,抑郁程度越高。(2)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由10個條目組成[14],采用李科特四點計分,得分越高,自尊水平越高。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5.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BDI和RSES評分比較 干預前,兩組BDI各項目分、總分及RSES總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結束時,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組BDI各項目分和總分以及RSES總分均顯著低于問題導向治療性團體組(P<0.01);干預結束3個月末,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組BDI各項目、總分以及RSES總分均顯著低于問題導向治療性團體組(P<0.01),見表1。
2.2 問題導向治療性團體組組內不同時間段BDI、RSES評分比較 問題導向治療性團體組干預結束3個月末與干預結束時BDI各項目分、總分以及RSE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結束時、干預結束3個月末BDI各項目分、總分以及RSES評分均顯著小于干預前,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1。
2.3 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組組內不同時間段BDI、 RSES評分比較 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組干預前、干預結束時、干預結束3個月末BDI各項目分、總分以及RSES評分兩兩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1。
3 討論
動力導向團體心理治療對大學生抑郁情緒的改善和自尊水平的提高具有快速而持久的效果,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與社會適應能力發展有不可多得的積極意義 本研究可知:(1)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對大學生抑郁情緒干預的效果明顯優于問題導向性團體,對改善大學生抑郁情緒具有積極意義。(2)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對改善大學生抑郁情緒、提升大學生自尊水平具有快速而持久的積極意義。動力導向團體心理治療是一種非常高效的心理治療手段,在實質性療效上與個體心理治療可以相提并論[15-20]。本研究結果證明,團體心理治療結束時,兩組BDI和RSES各項評分都在正常范圍值,而動力導向組成員抑郁情緒改善程度顯著優于問題導向組成員,自尊水平顯著高于問題導向組。在現實中發現通過動力導向團體心理治療的大學生更具有自信,在承受壓力的時刻更能付諸行動克服困難,在人際關系中更顯親和力,更有共情能力。
動力導向團體心理治療在改善大學生抑郁情緒的同時,還能激發大學生對生命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促使他們勇于擔當,積極面對挫折和困境 研究發現,在問題導向治療性團體情境中,小組成員可以依據自己與他人所形成的特殊群體為參照框架,更為真實地觀察、分析和描述自己的問題,認識到自身存在的負性自動認知模式,并嘗試在實踐中構建積極認知模式,針對性地做出生活的適應和改進;而在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情境中,小組成員在“覺察-宣泄-面對-轉換”等情緒處理過程的同時,透過現象場看見情緒后面深層次的動力因素,并且清楚地感知到,每個人必須承擔自己的命運,每個人在自己人生里面都有一個責任義務去肩負或是為自己的行動負起責任,當他能夠去做的時候,作為回報,他會有力量和尊嚴,同時可以肩負行動的后果。endprint
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可持久地改善大學生的抑郁情緒,提升自尊水平,促進人格整合,修通自我 動力導向治療性團體安全的設置和穩定的關系為團體成員提供了安全的退行環境,使團體成員清晰地看見了早年客體關系對個人信念價值和自尊水平形成的影響;原生家庭關系模擬的特征性體驗,使得團體成員郁結多年的情緒情感及愿望得以釋放和表達,內心的沖突得以解決和關系得以修通、獲得矯正性積極情感體驗[21-24]。這一系統的運作使團體成員的人格發展更加持續地穩定在積極健康的一端。
參考文獻
[1]崔慶霞,王在翔.大學生抑郁現狀調查及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14,31(8):629-630.
[2]劉琰,譚曦,李揚,等.大學生抑郁情緒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J].中華全科醫學,2015,15(1):91-93.
[3]劉華,欒奕.醫學類獨立學院大學生抑郁情緒研究現狀與思考[J].中國煤炭工業醫學雜志,2014,33(7):1198-1202.
[4]楊艷芳,吳滌,關明杰,等.331名在校醫學生抑郁現狀分析[J].包頭醫學院學報,2012,28(5):29-30.
[5]馬健.團體心理輔導對大學生情緒管理的作用[J].中外企業家,2016,23(36):155.
[6]王麗麗,魯雅靜.大學生抑郁的影響因素與治療[J].教育教學論壇,2016,46(2):52-53.
[7]王健,劉書梅,張沛超,等.積極心理干預對抑郁癥狀大學生情緒及主觀幸福感的影響[J].中國特殊教育,2016,30(11):44-50.
[8]強健.團體心理輔導在高校學生工作中的應用[J].黑龍江教育(高教研究與評估),2015,22(4):89-90.
[9]戴曉陽.常用心理評估量表手冊[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11.
[10]葉仙紅.團體輔導對抑郁情緒的應用分析[J].高教學刊,2016,29(5):246-247.
[11]陳娟,張興瑜,趙秀娟,等.朋輩團體心理輔導對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干預效果評價[J].中國學校衛生,2014,35(12):1819-1821,1825.
[12]賴青,李贏,黃秋平.結合團體輔導的《護理心理學》教學對提高護生職業心理素質的作用[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4,22(12):1871-1873.
[13]賈夢楠,肖溪,王曉麗,等.團體心理輔導對武警新兵適應性的影響[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5,23(2):365-368.
[14]王麗.大學生消極情緒心理咨詢視野下的思考[J].經濟研究導刊,2014,10(32):115-116.
[15]葛慈,張聰穎,武雪嬌,等.團體心理輔導對醫學專業新生情緒與壓力管理的影響[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3,21(2):199-201.
[16]馬金萍,盧國華,于麗榮.等.初中生情緒彈性對學校適應的干預效果[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6,24(8):1219-1224.
[17]高镕,熊梨花,曾清萍,等.治療性團體對青少年心理行為問題干預的對照研究[J].宜春學院學報,2014,36(12):74-76.
[18] Irvin Yalom.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M].李敏,譯.5版.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0.
[19]朱宏博,張淑麗.心理動力團體治療的臨床應用[J].中國醫藥科學,2012,2(24):197-199.
[20]王林,陳愛民.希望理論與認知行為治療在抑郁癥患者中的整合應用[J].護理學報,2014,24(4):72-74.
[21]龔定宏,肖明升.社區戒毒運用團體心理咨詢的成效研究[J].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2013,8(3):189-192,237.
[22] Bertold·Ulsamer.家庭系統排列入門:如何釋放家庭愛的力量[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9:10-17.
[23]徐楊.大學生無聊感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抑郁與學業倦怠的中介作用[D].哈爾濱:哈爾濱師范大學,2015.
[24]趙振軍.大學生心理危機音樂治療干預策略的相關性研究[A].中國音樂治療學會.中國音樂治療學會第十一屆學術交流會論文集[C].中國音樂治療學會,2013: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