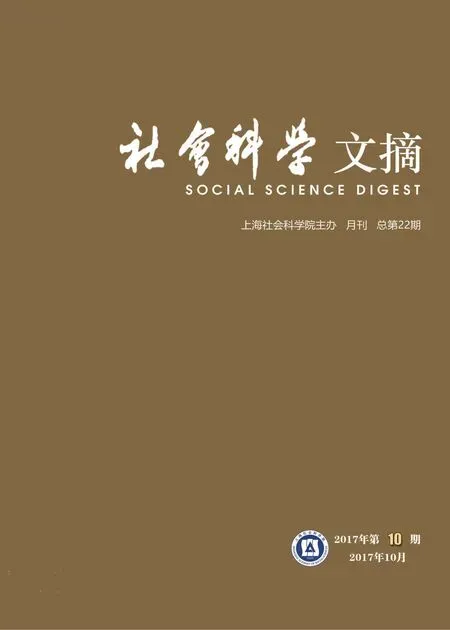對當代哲學起點的五大追問
文/劉潼福
對當代哲學起點的五大追問
文/劉潼福
一問:什么是哲學在當代中國的共同起點?
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必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雖然作為學科意義上的中、西、馬三種哲學各有自己不同的領域,但作為指導實踐的時代精神,必須找到共同的起點,建立互通的基礎。否則,指導思想的分庭抗禮,必然導致實踐世界的離析亂象。
初入哲學之門可清晰見到:西方哲學從水、火、原子等具體元素尋找世界的本質,而中國哲學從太極陰陽滋生萬物追溯天人合一的境界,故學界向有“西哲重物,中哲重人”之說。但深入研究發現:尋找具體元素的西方哲學只在古希臘早期曇花一現,因為科技手段尚未出現,人類無法依靠有限經驗去猜測無限世界,所以當柏拉圖發明了超越經驗世界的“理念”,建立了具有普遍性效用的抽象概念本體,加上亞里士多德創造的形式邏輯可以被運用于抽象概念間作無限的推理和演繹,整個西方哲學就在概念邏輯的基礎上建構起了一個完全不依賴真實世界而存在的“理念世界”。雖然純粹的“理念世界”本就是人的思維形式,但當思維用以尋找世界、研究對象時,自身并不在被研究的范圍中。正是這種與科學實證世界日益脫離的理念世界,構成了西方哲學長期唯物與唯心的本體論哲學之爭。直到康德提出了“物自體”和“理念世界”不可逾越的兩岸理論,才如雷鳴地震般從根本上喚醒了西方哲學沉迷理念世界之夢,近代西方哲學才開始尋找理念世界如何通向真實世界的橋梁。
要建立兩岸溝通的哲學橋梁,首先要尋找支撐哲學橋梁的基點。然而,哲學的思維之河是如此變幻莫測,要確立一個足以承受貫通兩個世界之大橋的穩定基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海德格爾幾乎花費了畢生心血去做這項工作,學界普遍感到理解海氏哲學的艱澀,其實,海氏的語言艱澀只是假象,真正的艱澀在于對人本的把握。海德格爾對哲學本體的思考,頗有中國道家關于“道”的意蘊,這也是他相當欣賞中國道家理論的緣故。這種共鳴,顯示了西方哲學的今天與中國哲學的起始遙相呼應。但這并不表示中國哲學比西方哲學有先見之明,因為中國哲學的起點有先見卻并不明,在對人本的認識上,充滿神秘和模糊。
按照認識的規律,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開端是一樣的,也是從探尋有無開始追溯世界的本原,只不過采取的視角不同。起源于中原大地的中國早期思維受農耕特點影響,更關注天地陰陽、四時變化的總體。因而,中國哲學雖提倡天人合一,卻并不凸顯人本,而以順應天命為本。唐宋時期儒、道、佛三家融合,中國哲學開始出現各種涉及人本的概念探討,到宋明理學達到頂峰。馮友蘭認為,即使朱熹“謂性即理,理和心仍然相隔在兩個世界”,直到王陽明的心學,才令“良知”通過“知行合一”的實踐功夫達到心物不分的境界。但王陽明的本體還只是道德實踐中以“良知”為前提的領悟功夫,并非普遍性的人本。
因為大一統的封建政體和克己復禮的儒學體系從根本上束縛了人性,所以近代中國實際上并沒有完成人本哲學的建構。今日人們從陽明心學中發掘著人本覺悟的哲學起點,是在西方科學和哲學百多年的沖擊滲透下,才獲得了人本意識的初步解放,形成了本體意義上人與世界的對等和交流。如張世英先生的“萬有相通”本體哲學,就是吸納西方哲學后的產物,因為能夠充當“萬有相通”之本體功能的,不可能是別的什么存在,只能是自覺的人。由上簡述可見,中西哲學在當代中國的會通都指向“人本”的起點。
同樣,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也不例外。盡管早年流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唯物主義的物質為本體,以資本生產引起的階級斗爭為主導,但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人們很快發現這些理論并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真正的核心是對人本自覺的重視。嚴格說來,實現人類真正的理想是馬克思一生的追求。這種理想的支撐點是以人為本,以自我完美為目標的哲學。馬克思青年時期的人生哲學,就準確地指向了“人本”和“自我完美”這兩個核心。但在現實中,人和社會怎樣才能達到完美狀態呢?從早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到晚年的《人類學筆記》,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馬克思始終在思考如何實現完美人本。
二問:人本的哲學起點是什么?
如果說中、西、馬哲在當代中國共同指向了“人本”,那么什么是“人本”的哲學起點呢?在中國,雖然有荀子的性惡論,但以儒家孟子主張的性本善為主流。在西方,人是什么?著名諺語稱之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雖然蘇格拉底的哲學曾經將“善”作為基點,但統治西方精神的基督教原罪論和立法基點卻都是建立在“性本惡”的前提上。恩格斯就認為“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可見,關于人的本質,在東方和西方同樣是一個爭論不休、沒有定論的命題。
“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是馬克思的名言。初看,這一內涵無限的“總和”對于追溯本體的哲學思維猶如“老虎吃天,無從下口”。但是馬克思認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這種存在的特點不是區別于動物的思想意識或宗教,而是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在生產中,首先的支配力量不是“人本”而是“資本”,資本是橫亙在通向人本道路上的汪洋大海或高山深壑。正是這種清晰的洞見,導致馬克思用42年去撰寫“資本論”,履行著哲學轉變的現實使命。顯然,變成現實的哲學是很難用語言表述的,更不是一個抽象的本體概念可以把握的。但在傳統西方哲學看來,這還是哲學嗎?以至學界長期難以確認馬克思哲學的本體。
不過西方概念哲學難以理解的馬克思哲學特點,在中國文化中恰恰獲得了“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效果。中國智慧重實踐體悟而輕文字知識的現象,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諸圣皆強調退隱語言概念以冥契事體之意,如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莊子言:“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
綜上所述,在兩岸哲學如何轉折這一令人困惑的問題上,中、西、馬三種哲學出現了戲劇性的纏繞:近代西方哲學意識到要跨越理性的此岸去到現實的彼岸,但執著于普遍概念的傳統思維令這種跨越仿佛拉著自己的頭發難以飛離此岸;馬克思哲學變革了西哲的傳統,真切地飛到了現實的彼岸,卻似乎不見了哲學的身影;本就在現實彼岸,應該成為西哲轉折目標的中國智慧卻面臨“哲學合法性”的質疑。
其實,三種哲學纏繞的不過是一種基本的哲學現象:普遍(或抽象)與特殊(或具體)的關系。哲學追求的是普遍真理,但這種真理就像人的靈魂附著在具體的實踐身上,不見其有獨立的蹤影。人們用哲學去分析外界事物時,猶如一位手術高明的外科醫生給人開刀,清晰有效。但當人們要分析哲學自身的基礎時,如同醫生要解剖自己的腦袋尋找靈魂,這就玄乎了。存在主義開創者克爾凱戈爾就認為:“在普遍本質和每個人的特殊存在之間橫亙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對特殊的問題不能給予永恒的或普遍的回答。……在存在(永恒)與變化(時間)之間存在著誰也無法通過心理活動加以掌握的本質矛盾。”馬克思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但在談到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兩條道路理論(“表象——抽象——具體再現”)時,也承認了其中的差別。馬爾庫塞試圖通過將哲學追求真理的過程等同于人類的存在方式,進而以人類的實存為出發點建立“具體哲學”。但每一門具體學科中的哲學靈魂,都屬于具體的“具體哲學”,于是抽象的“具體哲學”與各學科具體的“具體哲學”之間,重又陷入了普遍(或抽象)與特殊(或具體)的矛盾陷阱,問題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最初看來,作為具體存在的人因為思索著絕對永恒的普遍真理,個體的具體性和真理的普遍性就在思維著的人(此在的存在)這一起點上得到了統一。這也是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命題的基本含義,但深入考察就會發現這是一種粗糙而想當然的統一,因為每個思索著的具體個人都受到特殊環境和先前觀念的限制,很難站到絕對普遍的真理起點上。因此海德格爾要嚴格區別同一存在形態(思維著的個人)中兩種不同的存在,他主張在追問存在的時候,不要受到歷史和其他因素的干擾,既然“此在”就是現實中具體的人,而具體的人都會因為受到歷史和環境的影響而變得不純粹。為此,他要求從概念上清理“此在”,使之立足于最純凈的起點。當然,這個起點不可能是一個沒有內涵的純基點,相反要像一顆“種子”,在微小而純粹的存在形態中包含整個世界的結構。簡而言之,具體的存在(人)通過一生的時間去領悟普遍的存在,是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關于人本的總體表述,而其中注入時間的“存在”,便是人本的哲學起點。但這個起點是清晰的嗎?人同樣度過一生,有的升華,有的沉淪,這是“存在本體”無法回答的問題,還要訴諸“良知”,結果重又要回到具體的道德領域去尋找答案,與中國的陽明心學一樣殊途同歸于概念的循環陷阱。
三問:人本起點的困境何在?
從海德格爾的宏篇大論中可以發現,他是在用一連串深奧而晦澀的概念展開方式來完成對人本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早在古希臘戴爾菲神廟的唯一碑銘上就以如下的名言提了出來:“你要認識你自己。”盧梭稱它“比倫理學家們的一切巨著都更重要、更為深奧”。但如何認識自己卻始終是哲學上的難題,因為不明人本,就無從認識自己,更妄言認識世界;但從海德格爾的存在論中,我們看到了相反的循環:人若不認識世界又何以認識自己,更妄論透視本質!這是一個從循環論開始到循環論結束的繞人命題。
海德格爾哲學最晦澀的地方就在他表述不同層次上的“存在者”與其背后的“存在”(是)的關系,這個絕對存在著的“是”,如同基督教的上帝,創造著一切,卻從不現身;亦如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貫穿在一切存在的物質形態中,本身卻不具有物質的形態;它作為存在者的信念是永恒的存在,它作為存在者的感知是無法捉摸的存在。如俞宣孟先生概括道:“我們一切能夠認識、能夠表達的東西無不是在這個‘是’的過程中是其所是、成為是者的。或者說是者是‘是’的結果。這樣的‘是’在我們領悟一切是者的過程中,它本身卻不是任何是者。”這個關系儼然就是羅素集合論悖論在哲學本體論上的翻版,也是傳統本體論始終無法擺脫的困境,例如:唯物主義把一切存在歸結為“物質”本體,結果,作為本體存在的物質本身變成了非物質的概念;而唯心主義將一切存在歸結為精神,結果作為最高精神存在的上帝只能以人格化的形態保留于每個具體的肉身之中。根據哥德爾“形式系統的不完備性”定理,形式系統的這種天然悖論,使得在具體的存在(存在者)概念和抽象的存在(純存在)概念之間,恰如克爾凱格爾所預言的,橫亙著一條邏輯無法逾越的鴻溝。千年的哲學在語言和邏輯的世界繞了無數大圈,始終在人本問題上找不到起點的歸宿,這就令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道家“天下無指”“得意忘言”“圣人行不言之教”的深意:超越文字概念,直面事物本真,人類能否認識世界?依靠什么認識世界?
四問:文字終極的背后是什么?
現代人已經習慣用文字來記載一種事實,表現思想的智慧;但在文字誕生以前,同樣的事實和智慧通過什么來傳承呢?現代考古發現,史前人類智慧的傳承形式主要是圖像思維。如女神時代(生殖崇拜的母系社會)曾經經歷過3-5萬年美好漫長的和平治理,六千年前克里特島的文明“實際上超過了現代許多發展中社會的成就”,令考古學家驚得目瞪口呆。
以圖像思維為主的歷史,雖然在人類幾十萬年的發展中也只有幾萬年,但遠比三千年文字時代要漫長。在新石器時代數萬年的女性領導社會中,圖像思維占據重要的地位。在人類后來的繪畫、舞蹈、建筑等象形藝術中,圖像思維始終是厚重的基礎。中國的象形文字起源于圖像思維,西方在完成拼音文字之前,同樣經歷過圖像思維的過渡階段。在古希臘羅馬盛行的雄辯術,就以古老的記憶術為基礎。古老的記憶術是世界聞名的神秘學問之一,它的特點就是依靠圖像化進行記憶和思維。現代研究發現,全部大腦的容量是當今美國國立圖書館藏書的50倍。因為圖像與人腦具有結構的對應性,恰當的圖像思維可以激發大腦記憶容量的潛能,其自動索取信息和邏輯組合的功能更為現代圖書館所望塵莫及。象形思維并非簡單的記憶術,它通過圖形的闡述,激發的是對事物本質的理解力和重新表現規律的創造力。
相比抽象的文字,圖像思維更接近現實,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務實的傳統顯然與中國象形文字比西方符號文字更接近真相有關。事實上,文字交流固然有比較精準的特點,但各國各地文字語言的巨大差異,給實際交流造成了巨大的困難。相比語言文字之抽象交流的困難,圖像和音樂的意會溝通要容易得多,哲學智慧難道只能固守抽象文字的唯一領域?
五問:哲學是否應該接納新路?
哲學即使堪稱思維的最高抽象,也不能改變思維固有的形式。思維作為宇宙發展中的存在,當然擁有宇宙發展的基本形式,今日量子世界的科學探索很大程度上并非先有事實后有認識,而是思維推理參與實驗設計,然后才發現新的本質。這種由推理思維與實驗結果共同確認的本體,展示了人和宇宙的共同本質,完全不同于早期哲學對世界本質或起源因模糊猜測而導致了主客對立。這種現象表明:沒有思維規律和宇宙規律的共鳴相通,人類無法對起點進行認識從而也無法認識人本。
傳統哲學之所以在人生觀和世界觀之間出現規則斷裂和主客對立,便是因為以抽象文字的形式系統所進行的純粹思維無法解脫時空的困境,不能真正把握現實的人本。其實,現實的人本就是從受精卵開始發育的胚胎,但抽象的哲學會舍棄它的具體成因而追溯絕對的本質,這樣就會陷入“有-無”之爭。然而,有無之爭真的就能追溯到本質嗎?胚胎是父母性結合的產物,但當父母還未相認甚至他們自己尚未出世時,這一后世的胚胎在哲學上只能表現為“無”,但它作為自然界存在的元素卻始終存在,屬于不被感覺的“有”,它會按照某種命運之神的安排最后通過父母的奇遇變成可感的“有”,因此在“無”中已經蘊含了“有”,這種抽象的表達就給神主宰世界留出了空間,導致二元對立。現代科學發現在連續塌陷的宇宙大爆炸中,生命所需要的各種元素開始由輕到重分層析出,在特定的數碼關系中以遺傳基因的形式通過性的載體重合成生命。宇宙和生命并無主客對立的本原,它們在元素的層面同屬數的結構本體。數的結構本體很難用抽象的概念把握,卻可以相對輕松地用圖像去描繪。如遠古女神時代用倒三角作為生殖崇拜的象形圖案,艾斯勒稱之為“圣杯”崇拜,其內涵的深刻性和豐富性就容納了現代基因理論。因為胚胎發展總是一分為二的細胞分裂形式,將這種形式寫成數學公式就是2n-1,自然數代入其中,結果向上排列成圣杯圖形,向下排列成金字塔圖形。這種結構不僅蘊含了生命誕生的秘密,也蘊含了自然發展的秘密。它作為一種表達宇宙創生并展現生命過程的神秘“存在”,難道不是哲學智慧所追求的簡單“本質”?
何以復雜的人生會從這樣簡單的本質中,并在成千上萬年代和數量中,以基本不變的形式誕生出來?支撐這一生命結構萬變不離其宗的“人本”,究竟是怎樣的“存在”?當我們這樣提出問題時,人類智慧的追問會令我們重新關注古希臘以數為宇宙本體的哲學家畢達哥拉斯。
文字誕生前,人類長期通過圖像壁畫、音樂舞蹈進行思想交流和傳承,其中的智慧(即無文字的哲學)已透入人本,指導實踐。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象數智慧并不專屬西方畢達哥拉斯學派,其他文明亦有豐富的底蘊。中國自古就有陰陽八卦的象數思維,以東方的智慧延續著這一神秘的人本認識形式。自從萊布尼茨發明了二進位制后,人類的計算機技術運用這一算式迅速邁進了神秘的生命領域,畢達哥拉斯關于數的認識路徑得到了迅速的拓展。薛定諤在《什么是生命》一書中已經明確提出“生命不過就是一組編碼數字”,以后整個基因工程不斷在證明著這一判斷:從“阿威塔”數字生物誕生,到機器人駕馭生產技術、戰勝圍棋高手、代替精英管理等,神秘的質數效應通過電腦編程,直接變成人腦智慧,凸顯人之本質。
從象和數進入生命本體的哲學之路,更契合東方中國和古老埃及的智慧源頭,與傳統西方概念哲學之路不同。概念分析的哲學猶如西醫的手術刀,剖析了大量的活體,找到了很多構成生命的本質,解惑了遠古和中哲長期含混難言的神秘人本,但這些本質就像風干的標本,喪失了活性,無法再現生命。鮮活的人本,需要象、數、文三足鼎立的立體哲學路徑去建構完整的認識。今天,哲學是否應該接納其他智慧的途徑,關注人本鮮活的起點?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摘自《哲學分析》2017年第4期;原題為《追問哲學在當代中國的起點——讀張世英先生、俞宣孟先生之本體觀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