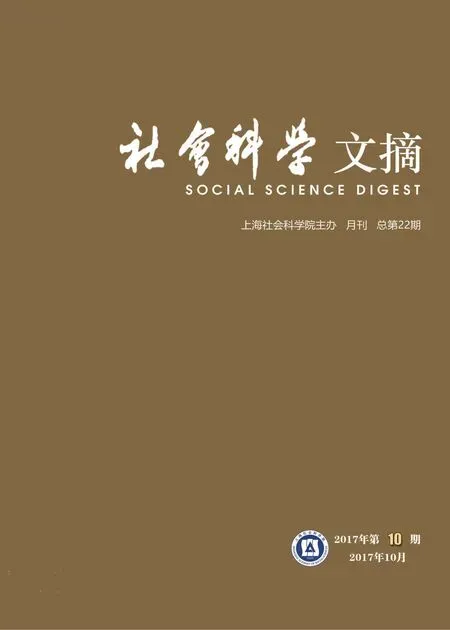中國思想史研究需要繼續深耕
文/龔留柱
中國思想史研究需要繼續深耕
文/龔留柱
一次影響深遠的學術轉向
早在1994年李澤厚就提出一個著名的論斷:“九十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學問家凸顯,思想家淡出。”他還在同年的一次訪談中說,他并不反對“對具體問題作微觀的實證的研究”,但是“重視專門之學,強調細部研究并不就是一切”,那種認為“只有考據、微觀、實證才是真功夫,而所謂思想則既不能稱為學問,對社會也并無用途,而且似乎談思想搞宏觀是非常容易的事”,這是一種大錯特錯的認識。“思想家必須具有廣闊視野和強有力的綜合把握能力,才能從大千世界中抓住某些關鍵或重點,提出問題,或尖銳或深刻,反射出時代心音,從而才能震撼人心而成為思想家。”
2012年,彭衛有一篇名為《近十年中國古代史研究之觀感》的學術評論文章,在充分肯定由于“大量新的資料不斷刊布”導致“中國古代史研究呈現持續進展的態勢”的同時,也尖銳指出了其間的一大短板,即學者“對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論問題著意有限”。作者慨然發問道:“對具體問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能否支撐起構建理論的空間?在對中國古代具體歷史研究厚實的基礎上,能否嘗試提出中國學者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道路自己的解釋?更進一步看,我們能否在自己細碎的研究點之外,尋找到理論上的突破口?”
2013年,王學典發表《治學術史的兩條道路》一文,對學術轉向及其影響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說,一是受特定意識形態的影響,1990年代以降,進入“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新時代。思想觀念的反思、建構和爭鳴遂讓位于對學術傳統的爬梳、整理和重續。于是,學術史研究迅速取代思想史研究成為一個新的焦點和熱門,暢行至今。二是治學術史逐漸形成兩種路數、兩條門徑并存的局面。一種是以事實為中心,以材料考辨、定點清理為主要工作;一種是以問題為導向,以范式探討及線索梳理為基本任務。結果,前一種路數有長足進展,遍地繁盛,成績斐然,為當下大宗。這是基礎性、起步性的工作,意義當然不可低估,以后也不可或缺。但后一種路數的研究是更高層級的工作,是懷抱明確的問題意識,借助某種觀念工具,力圖對學術演變的內在邏輯和基本走向進行整體把握,進而為當前的學術研究尋覓一條恰當的路徑。但這種研究在整體上薄弱,甚至被刻意回避。總之,學術界重學術輕思想風氣的形成,治史者對“事實”熱衷,對“問題”冷漠,沉潛于專深之學而回避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以材料和事實為中心的路數發達,而以問題為導向的路數低迷,這與當下學術界的價值取向密切相關。
學術轉向的兩大原因
那么,這場影響深遠的學術轉向,其發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學典所說的“受特定意識形態的影響”,可能只是原因之一,是學術界面對外部環境的突變而產生的一種應激反應。除此,還應有一種更深層次的因素在發揮著更加持久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正如鄧曉芒所分析的,“思想和學問的分裂”,原因往往在于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嚴酷的政治高壓下,學者不敢表露自己的思想,只能以學術的方式來藏匿思想,或借以自保,如西方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國的乾嘉樸學;另一種是思想的狂躁和學術的淺薄導致的分裂,如胡適的口號‘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90年代的輕思想而重學術也屬于此列”。
我們先看前一個出于“意識形態”的政治原因。對此有更進一步明朗化解釋的是程廣云在一次學術會議上的演講。首先,他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領域,出現了一次影響深遠的學術轉向”。“所謂‘學術’已經獲得了話語霸權,而所謂‘學者’則通過這種話語霸權的獲得,逐步爭取到學術資源,并且掌握了學術權力。”這次學術轉向的影響雖然只及學界,但深刻持久,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80年代“思想解放(啟蒙)的歷史終結”。其次,關于這次學術轉向,它“是由一場關于學術規范問題的爭論引起的”。在爭論中出現了三種基本趨向,一是鄧正來的“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要求通過“確立學術規范”,拒斥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保證“學術自主”。二是朱學勤強調“民間思想”的意義,認為近代知識體制和大學的兩面性“有利于知識傳授而有害于個性成長,有利于學術積累而有害于思想創新”。三是劉小楓強調“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利之間的個體學術的價值”,認為個體學術才是最基本的問題。結果,第一種強調“學術規范”的意見成為大陸學界的主流,“同時將民間思想、個體學術拒斥于體制外”。最后是轉向的影響和得失。一是學術規范好比一種準入制度的“圍城”,在這個學術特區里,雙方達成一種隱性的“契約”。學者回到書齋,放棄了思想的權利,不做第一流的思想家,只做第二流的學問家,從而獲得了學術的權力,形成體制內學術。官方則保證了思想的權威,讓渡了學術的資源,使“純粹學術研究獲得了與意識形態學術研究大致相當的位置”。二是學術自主性的實現,符合韋伯所提出的“世界的祛魅化”(去意識形態化)的現代性的表征,其表現就是價值中立和意義懸置。“在這種純粹學術中,原本為問題而創造的學理,反而獲得了自己獨立的意義和價值。”于是在學術規范旗號下,經驗主義的樸素學術被邊緣化,而教條主義的繁瑣學術被中心化。三是大陸學者身份職業化轉型的實現,從依附于政治的官方知識分子和依賴于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中,分化出一大批學院知識分子。他們為了學術而學術,依靠手中的學術“絕活”,以之作為謀生手段和“生存技藝”。四是出現了一場“學術大躍進”,官方學術資源投入之多,產出之少,史無前例。結果是學術“虛假繁榮,真正腐敗”,但它是一次“和平贖買”,雖然對學術進步的意義有限,但對于“政治穩定”的價值卻無可置疑。
王學典也就此分析說,1949年以后政治長期介入學術的深刻教訓是造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因素,但不可矯枉過正、因噎廢食,不可鑒于以往“以論帶史,造成的流弊而排斥思想理論。研究歷史不僅需要史料也需要理論和概念。離開了理論,人們對現象只能局部的個別的認識而在整體上毫無頭緒。具體材料只是素材,只有思想才能將之變成學術。所謂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對學術研究不僅有傷害也有不可忽視的正面作用”,如基于社會現實“提供問題意識”,這是學術活動自身所無法產生的。
鄧曉芒對這種因意識形態原因而產生的學術轉向進行了尖銳批評。他說,90年代學界面臨的問題,一是信仰危機。其所謂“思想”,“只不過是依附于政治使命或政治前途這張‘皮’上的‘毛’而已,并沒有自己獨立的地位,也從來不是靠學術能夠撐起來的”。二是以“純學術”來掩蓋自己思想的貧乏和信仰的喪失,到書齋生活中去尋求“學術獨立”和“人格自由”,使“思想和學術都呈現出一種向內龜縮的趨勢”。三是真正的學術規范應當是思想規范,通過思想交鋒和辨析,清除思想界的陳腐之見,使得一方面尊重事實,一方面尊重邏輯,不能只是表層次的技術規范。四是中國當代思想和學術的分裂,在于學人的思想本質上還不是一種“學術思想”,而只是傳統型的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并且使之立足于以“誠”“信”為本的情理之上,“不容學理和邏輯有自由施展的余地”,成為道德從而也是政治的附庸。
關于這次學術轉向的第二種原因即社會文化因素,2011年汪丁丁在一篇名為《學術家為什么沒成為思想家》的簡短網文中,有一種獨辟蹊徑的論斷。他說: “本世紀的最初10年,權力的敗壞不可避免地導致生活世界各領域的敗壞,最后一個最高級的領域——它涉及人的本質(自由或創造的能力)——是思想與學術領域的敗壞。”“首先,它的一般特征是思想能力的缺失”;“其次,它的中國特征在于,它是以精英身份維護著思想能力的缺失。”接著作者又說,“根據韋伯的感受,當代社會的知識困境在于:學術而缺乏思想,專家而沒有靈魂。導致這一困境的,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日益嚴格的大學分科制度和理性社會的官僚化”,結果導致“普遍的平庸”。
中國思想史需要繼續深耕
不久前,陳春聲教授曾經大聲疾呼:“世代交替之下的中國史學的發展,可能又到了重新關注理論思考的學術價值的時候了”,他的認識基于兩個理由,一是長期研究課題的碎片化,學界由“小題大做”,變成欠缺問題意識的“自言自語”,這樣使帶有“終極關懷”意義方向感的學術研究已經相當薄弱,難于培養起把握整體的“中國文明”或“人類文明”的意識和雄心。二是“數字人文”時代的來臨,歷史學者的功力,更多表現在眼界和通識方面,更重要的是有深厚學術史背景的思想建構。“出思想”與否,成為新的學術世代衡量史學研究成果優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能否具有更大的理論關懷和超越具體研究課題的問題意識,對于新一代史學家來說,可能已經成為對其學術生命生死攸關的問題。
我的理解,這里強調重新關注“理論思考的學術價值”,要求能夠“出思想”,其實涉及兩個“生死攸關”,一個是與整體的“中國文明”的演進和我們能否將自己的文化傳統融入現代“人類文明”的潮流生死攸關,一個是與作為學科的史學研究的前途生死攸關。
首先,我們來看后一個問題,即史學界如何能夠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甚至歷史學科在新時代變得更有價值。我們都承認,史學是分層次的,它又是以學者的思維認識層次作為基礎來劃分的。比如李開元的史學層次模式理論即認為,作為整體的史學,是由三個層次構成的。
第一是基層史學。它以確立歷史事實之具體存在為目的,往往通過技術手段如考釋和描述的方法來追求史實的復原。傳統史學中的史料學和歷史編纂學都可歸入此范圍。第二是中層史學。它在基層史學已經確立的史實基礎上,以探討各個史實間的關系為目的,用邏輯分析和歸納的方法來追求繁紛史實關系的合理解釋。傳統史學中的史論,往往就是有意識地從因果關系上來解釋史實的,如王夫之的《讀通鑒論》、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以及今天學術期刊上的大量論文,都是在這個層次上有所“發明”。第三是高層史學。在基層史學確立了史實和中層史學對史實關系進行合理解釋的基礎上,史家進一步建立歷史演化的一般法則和理論模式,哲學上的抽象和假設為其工作方法之特點。如顧頡剛在《古史辯·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中提出的“層累造成的”中國傳說的古史系統說,又如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都可視為高層史學的代表。國外如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則被稱為高層史學的典范之作。
盡管處于不同層次但只要是創新性的成果,都應該具有相當的史學價值,可是這種價值也并非完全等同。從對社會和文明發展演進的貢獻以及其學術影響的大小而言,高層史學的價值往往要重于中層史學,中層史學的價值又往往要重于基層史學。因為根據“懷特海三段論”,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達。在任何表達之前,先有對重要性的感受。“思想”和“學術”之間,前者更偏向于“對重要性的感受”,后者更偏向于“表達”。高層史學借助于理論工具,往往從全局出發,具有更鮮明的問題意識,更敢于回應一個時代的重大問題。而基層史學以“純學術”自詡,由于缺乏思想的引領,只能局促于對史實的零碎而平面的“表達”。
鄧曉芒提出,學術和思想的關系可以歸結為“歷史和哲學的關系。只有在哲學的眼光中,歷史才能真正成為歷史。因為按照當代解釋學的說法,所謂歷史并不僅僅是編年史和史料史,而是歷史的意義的歷史;不是外在器物的歷史,而是賦予這些器物以意義的人的發展史”。而這些單憑實證的“死學問”是無法揭示出來的。反過來,“也只有在對歷史發展的思索中,哲學和深刻的思想才有可能形成起來,并對歷史具有超越性”,才能產生真正的“新思想”,而歷史科學根本說來是隸屬于哲學的。這無疑是對高層史學及其價值的充分肯定。
這些,都是從史學建設和發展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思想史研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正像陳春聲所呼吁的,“能否具有更大的理論關懷和超越具體研究課題的問題意識,對于新一代史學家來說,可能已經成為對其學術生命生死攸關的問題”。
其次,關于我們如何通過“帶有理論思考價值”的史學研究,以“培養起把握整體的‘中國文明’或‘人類文明’的意識和雄心”,這是一個涉及面廣而又非常深刻復雜的問題,這里只能從三個角度做個簡單的提示。
第一,我們還處在中國現代化社會轉型的艱難過程之中。按照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前后兩個社會政治形態的轉換,其間必有個作為瓶頸的轉型期,即“三峽”。中國古代從貴族封建體制轉向皇權-官僚體制,大約從戰國中期的商鞅變法啟動,到西漢武、昭之際基本完成,前后約300年。而中國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大約從鴉片戰爭后開始,至少需要200年,估計到本世紀中葉方能基本完成。作為一個14億人口龐大國家的現代轉型,是一件萬分復雜的事情。我們既需要從當代各國的現代轉型過程中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還需要從特殊的國情出發,從歷史的得失進退中提煉出寶貴的思想資源,來支撐我們順利地走出“三峽”困境。當今,人類在信仰、價值觀、行為方式、情感、心理、審美等等方面都面臨著全方位的困擾,中國人也不例外。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繼續進行深入探究,鍛造理論利器,以獲取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使命。而承擔使命的前提,無疑是精神的獨立和學術的自由。
第二,華夏文明需要一次“鳳凰涅槃”。一個民族的思想深度和持久的影響力是靠千百年來為數不多的思想家來奠基的,所以思想家被稱之為“國之重器”。其任務不僅是整理既有的思想成果,使人類在文化上能夠薪火相傳;而更重要的則是對舊文化傳統的顛覆、破壞和解構,從而引領出一個新的思想時代。正如許紀霖所說:“啟蒙運動百年以來,尚未解決的真正問題有兩個:其一,如何將‘好’的文明內化為中國人能夠認同的‘我們的’文化? 其二,如何將‘我們的’文化提升為全人類普世的文明?” “只有當文化與文明的主體重新合二為一,不再撕裂與對抗,中國才能走出百年來的二律背反,重拾民族的自信,再度成為一個對人類有擔當的世界民族。”
第三,未來大學的新樣態,也值得深入思考。現代大學是民族的“靈魂”。但隨著“數字人文”時代的到來,文明的記錄和傳播介質日益借助于互聯網,知識獲得的方式已經技術化。所以未來在大學里“獲得現成知識的功能將變得不重要”,人文知識的獲取多數可以在校園外實現。如果文史哲的教學體制還是以簡單傳授知識為目標,那么它們在大學中還會有合法地位嗎?謝泳認為將來大學的功能將轉變為“聚集青年,思想碰撞,在群體生活中互相激勵,養成相互合作的精神以適應未來的社會生活”。未來學生在大學要養成現代的創新意識和基本素質,學會容忍異端和包容不同政見的現代政治風度。教師必須用思想和人格來感召青年,師生關系將有可能“重新回到傳統的師徒模式,有思想共鳴才產生關系”。
以上三項為犖犖大者,已經充分說明思想資源的深度開掘和思想史的深入研究,不僅不能滯停消退,而且必須奮起直追,將其水準提升到一個嶄新的高級階段,以不辜負時代的期許。
(作者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摘自《史學月刊》2017年第9期;原題為《式微中的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