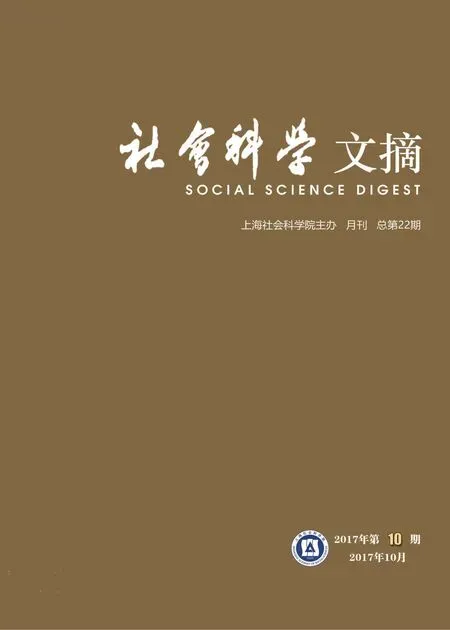春秋思想界的張力:論新思潮與老傳統的關系
文/貢華南
春秋思想界的張力:論新思潮與老傳統的關系
文/貢華南
對春秋思想的看法,20世紀初胡適與馮友蘭定下基調后,至今還在學界流行。胡適把老子、孔子之前的二三百年當作中國哲學的“懷胎時代”。不過,囿于實證古史觀與狹隘哲學觀,胡適并未正視此“龍胎”,而只是將此“龍胎”當作毫不起眼的“胎兒”輕輕地滑轉過去。馮友蘭同樣囿于狹隘的哲學觀,將《詩》《書》《禮》《樂》剔出哲學之外,孔子之前的思想亦全部被剔除出哲學。故馮友蘭以孔子為“萬世師表”,并將其確立為中國哲學史的開端。
其后,有學者接受西方“哲學的突破”理論,認為春秋戰國是中國“哲學的突破”時代。具體說,儒家與墨家最早突破“王官之學”舊傳統,而建立新的思想系統。將諸子視為“突破者”,這個論斷沒有問題。但將突破的對象確定為詩書禮樂等“王官之學”,其論不能無疑。從“王官之學”到私家之學,“學”改變的僅僅是“形式”,“突破”也只是形式的突破。真正的突破指的是實質的突破,就是指突破詩書禮樂精神傳統,而建立新的思想傳統。如果真是諸子推翻了詩書禮樂精神傳統,而建立起新的思想體系,那么,諸子就是詩書禮樂思想的“掘墓人”。問題是:詩書禮樂舊傳統的“命”是諸子革掉的嗎?通常的看法是,老子、孔子生而面對“禮崩樂壞”之頹局。也就是說,在他們思想時,詩書禮樂舊傳統的“命”已經被革掉了。那么,革掉詩書禮樂舊傳統命者并非老、孔,亦非純粹的、破壞性的“虛無”力量。能夠革掉詩書禮樂舊傳統之命者勢必在思想領域有相當的廣度與深度,且擁有強大的現實勢力。這個新的思想勢力才是老、孔及諸子所要直接超越的對象。
春秋思想世界中的老傳統與新勢力
西周以來的《詩》《書》《禮》《樂》等典籍構建出一個深厚而博大的思想傳統,春秋思想世界首先扎根在這個傳統之上。漢人將諸子視作六經之支流,亦立足于此。正因為扎根于六經,諸子的思想才能夠深沉博大。截斷眾流,老、孔失去這個根基,其思想也會隨之淺薄與無法理喻。
從其構成看,春秋思想世界中的《禮》《樂》是一個老的思想傳統,《書》以及《詩》中的《雅》《頌》也為歷史所遺留。偏向抒發個體情志的《風》則大體為春秋時期所創作,是新涌現的精神趨向。不過,《風》吟誦、歌詠、敞開人的性情,以期陶冶、健全情性,這種浪漫的、理想的精神與禮樂精神仍然內在一致。詩書禮樂的世界是一個文質彬彬的世界,也是一個深沉綿長的思想世界。諸子生長于斯,涵思構想,遂破繭而成就各自的思想系統。
周王室衰微,朝廷、宗廟之音成為幽幽往事,而《風》所傾訴與追求的價值理想,如家國安定、人倫有序、人情敦厚等,其如何由理想變為現實,停留在主觀情感的,或“應該”的層面始終得不到解決。尋求可靠、有效地變革現實的客觀手段與力量,這構成了春秋時代賢士的歷史使命。事實上,春秋以來,除了《詩》《書》《禮》《樂》所構成的思想世界,另一股與之相對的思潮也在涌起,那就是以齊桓霸業為標志,以管仲為其思想名片的思潮,其文本為《管子》。這個思潮的特點是推崇形名事功,具體說,提倡效率,追求功利。其表現是,推賢舉能,明令尊法,務實尚形(刑),計功重財。甚至“義”“孝”“敬”“悌”等無甚實用的精神也被齊桓-管仲在治國理政中提及。齊桓-管仲思想博大龐雜,雖不能一以貫之,但卻有清晰的主軸。宰周公以“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國語·晉語》)來概括齊桓-管仲思想,應當說是非常精到的。作為一貫的做事風格與思想原則,“務施與力”顯然是對《詩》《書》《禮》《樂》所構成的思想世界之反動,通常所說的“禮崩樂壞”正是這一思潮崛起、沖擊所帶來的后果。
客觀地看,春秋三百年間并非質而無文之混沌,亦非文化黑夜。其間禮樂猶在,而仁義形名等各種思想勃興。只不過,思想之共主示弱,各種思想力量依次登臺。“禮崩樂壞”乃春秋末期的社會思想狀況,亦是孔家的價值判斷。如果用事實判斷表述則是:禮樂由至尊的意識形態轉變為與形名法術同序列的思想力量。作為新涌現的思想力量之代表,齊桓-管仲思想以效率、功利為其基本旨趣,其現實目標包括取物以歸己與屈人(國)以就己。“取物”“屈人”也就是能將自己的意志、目的、欲望施加于事事物物,簡言之,即“有為”。老子以“無為”扭轉“有為”,孔子以“為政以德”來超越刑政。老、孔皆對齊桓-管仲思想而發,或者說,皆是齊桓-管仲思想的突破者,這似乎更合乎春秋思想的邏輯。
管仲最重要的舉措是讓“士”“農”“工”“商”分工分處,使“士”明確獨立出來。“士”不與“工”“商”“農”雜處,給予他們相對獨立的空間與充裕的時間,讓他們共同從事思想觀念的探討(“言”),以解決精神生命的安頓問題(“心安”) ,“士”無疑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階層”。不同的“士”興趣、關懷不同,其觀點、立場亦自然有異。對于來自齊國之外的“天下之賢士”來說,他們各以其“賢能”而為齊桓-管仲所用,而他們的思想與齊桓-管仲不必一致。這些來自不同文化區域、具有不同思想傾向的賢士居住在一起,專心思考、議論、辯難,探求種種思想的可能性。盡管他們沒有各自獨立創建自己的學派,亦沒有文獻明確記載他們思想間具體的差異、對立,但其中包含諸子之各種思想端緒已經相當明晰。就此說,將齊桓-管仲思想視為《詩》《書》《禮》《樂》老傳統的第一次真正的突破或許更合適。
齊桓-管仲思想以形名事功為核心,大異于詩書禮樂“務德”等浪漫、理想精神,也同時構成了諸子思想的重要源泉。兩股力量相互激蕩,相互撕裂,共同構成了春秋思想世界的完整圖景。禮樂缺乏外在物質力量之保障,詩之思精神穿透力強大,亦缺乏直接變成現實的通道。相較而言,齊桓-管仲的形名事功思想與權力、物質利益牽連,擁有更強的變革現實的力量,由此成為春秋戰國諸侯為之傾心的新的思想勢力。
形名事功思想之發展
齊桓-管仲的思想在其同時代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賢明的諸侯紛紛效法之。晉文公是其中最成功者,其圖霸業之舉措多借鑒齊桓-管仲。子產治鄭國,尚賢使能,依靠刑辟,其主導精神亦是對齊桓-管仲思想的繼承。以“能”任事,以此為原則,不惜違逆主政者,這正是齊桓-管仲的核心思想。“能”以“學”而得,“鄉校”為“學”與“議”之所,子產拒絕“毀鄉校”,其理由同樣基于鄉校之有利于為政。不固步自封,而是向賢能開放,這是子產為政的重要特征。“學而后入政”,就保證了治理的效率。鄉校中議政固然可以疏通民情民怨,但也激發了“民智”。其結果是造成了鄭國思想的短暫勃興,鄧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鄧析與子產都將“刑”客觀化,兩者精神實質一致。故子產殺鄧析,但還是用其竹刑(《左傳》定公九年)。鑄刑書與竹刑以確定性、客觀性為其基本特征,這無疑推進了齊桓-管仲所崇尚的效率原則最大化之展開。
除了形名家、法家之外,直接繼承齊桓-管仲思想的還有兵家。兵圣孫武晚齊桓-管仲百年,在其入吳前一直生活在齊國。孫子入吳所獻的《孫子兵法》無疑與齊桓-管仲的思想有著順承關系。因為,《兵法》中不止是軍事,還包括刑政、名法、經濟,及更廣大的天地人之道。《兵法》之成熟不僅標志著軍事理論之高度自覺,同時也意味著刑政、名法、經濟理論之高度自覺。在春秋諸侯中,只有齊桓-管仲以來的齊國達到符合其現實與理論的要求。此外,在齊桓-管仲的繼承者中,法家一直是重要的一枝。《韓非子》稱管仲為“圣”,表現出法家對齊桓-管仲的自覺繼承。
老子對形名法令的超越
老子活動與思考的時代為齊桓-管仲的形名法令思潮所籠罩。老子反對、超越的對象包含禮樂文化,但其最重要的對象是形名法術,后者即是當時主導諸侯思想的齊桓-管仲思想。或者說,形名法術思潮亦構成了《道德經》展開的思想背景。具體說,《道德經》所批判的不是處于自發狀態中的鄙俗、沖動,而是在當時已經被“理論化”“系統化”的思想潮流。管仲所追求的“倉廩實”“衣食足”指向功利的實現與人的欲望的滿足,這無疑是世俗性的人道價值。在老子看來,這些世俗性人道價值的實現不僅不能帶來社會秩序的安定與道德品格的完成,相反,它卻會使社會陷入爭斗、混亂,人的品格墮落,人心不得安寧。“尚賢”“貴難得之貨”“見可欲”并非儒家的核心主張,而這卻是《道德經》所極力批判的觀念,《道德經》顯然并不是以儒家為其敵手。同時,這些主張乃自上而下的治理措施,其發布與支持者只能是擁有至上權位與社會聲譽的霸主、名相。《道德經》之指向是明確的,那就是齊桓-管仲所掀起的形名事功思潮。
效率、功利、欲望都指向“有為”,而徹底的突破自然是“無為”。《道德經》第80章所展示的世界圖景正是扭轉“有為”的“無為”世界。“舟輿”“甲兵”可以提高人的行動效率、可以更有效地實現人的目的意志。對于“什伯之器”,老子的態度是“不用”,即拒絕效率原則,拒絕以人的目的意志加于他者之精神。不用效率高的籌策,改用無效率的“結繩”,這也是“道”的基本精神。
在“無為”精神主導下,人的生命才能得到保全與守護,才能吃什么都香(“甘其食”),穿什么都好(“美其服”),住什么樣的房子都滿足(“安其居”),什么樣的外在條件都可以樂在其中(“樂其俗”)。同樣,與人共在的其他生命才能免遭損傷。顯然,“小國寡民”狀態下,“萬物”“民”的生命力甚強,而“國”則相應被弱化。二者不可得兼,齊桓-管仲選擇的是“尚賢能”“作內政而寄軍令”而富國強兵,老子選擇的是扭轉此精神路向而讓民、物各全其真。齊桓-管仲追求形名法令,老子則果決地拒斥之而追求“無形(無名)”之道。這條道路后由莊子繼承并發揚光大,由“形”而明確走向“使形者”或“形形者”,從而確立了道家“形而上”思想道路。
孔子對刑政的超越
如果說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為“無道”,那么諸侯只出征伐而不舉禮樂可謂無道至極。孔子欲恢復周禮(包括《詩》《書》《禮》《樂》等)以救世,但當時的思想界卻是齊桓-管仲的形名事功思想當道,老傳統被沖擊而逐漸式微。在理論上堅定地回擊齊桓-管仲的“刑政”思想,此為孔子繞不開、推不掉的難題。在《為政》篇,孔子對比了兩種為政方式,并斷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針對的是孔子同時代的諸國意識形態,此意識形態之祖師無疑是齊桓-管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齊桓-管仲僅僅達到了“倉廩實”“衣食足”這個物質文明的目標,“知禮節”“知榮辱”等精神文明目標顯然沒有實現。百年后的孔子看到了這一點,并且敏銳地指出了問題之所在。為實現精神文明目標,孔子另辟蹊徑,開辟了“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精神道路,喚醒內在精神、由內而外地認同、皈依精神目標,由此形成健全的道德品格(“有恥且格”)。以“德、禮”治國也拒絕以效率為先,拒絕以功利為尊。在孔子,真正重要的是倫常秩序修整,民眾道德意識健全。這亦是指向對齊桓-管仲“賢能”為“上”價值觀念的超越。
管仲相齊桓而霸諸侯,其才能已經得到證明;但他沒能輔助齊桓走上王道,此又為儒者所詬病。這個評價所包含的兩個方面的內容在《論語》中都有展開。以“禮”為價值標尺而做出的價值評判,則管仲“不知禮”。這也可以說明“禮”在管仲思想中并不重要。在管仲觀念中,國之強盛依賴賢明之士與以法令保障的制度系統,于是,大力“制國”“進賢”。圍繞“足甲兵”展開的舉措以提高效率為核心,其實質正是孔子所反對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更與禮樂制度所維護的確定秩序相悖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實施百年,在春秋時代影響巨大,其流弊孔子看得十分清楚。“民免而無恥”不僅是道德的評價,更是鮮明的社會效果之揭示,可謂精當之極。孔子“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理念即是立足于刑政之治的流弊而展開的超越,其深沉正基于刑政之治所帶來的思想力量與社會影響之深刻的反轉。
孔子仁愛、禮治等觀念雖與管仲霸道刑政觀念相左,但霸道刑政對于文明的守護又為前者之實施提供前提與保障,孔子對管仲事功的肯定正基于此。而且,管仲之霸諸侯,不是完全憑借武力。盡管管仲思想與禮樂相悖,但以事功捍衛文明,霸諸侯而不以兵車,此乃孔子退而求其次,有限地接受、肯定管仲的原因。而且,為達到人倫治平的目標,在仁德、禮讓精神前提下,孔子亦不棄絕“刑罰”“名利”。在孔子觀念中,作為外在規范的“禮樂”離不開內在人心的認同,禮樂之興最終要仰仗“仁”的精神。“仁”為禮樂之基石,禮樂則能保障刑罰之效用。不以名利、刑罰為尊,而是在仁德、禮讓精神根基上開啟其用,這是孔子對齊桓-管仲思想的顛覆與扭轉。不同于老子同時拒斥禮樂、形名,孔子拒斥形名法令而使之歸于仁、禮,此道路后由《系辭》繼承并發揚光大,由“形”走向“形而上”,從而確立了儒家“形而上”思想道路。
結語
老、孔面對的不僅有詩書禮樂的老傳統,同時還有一個廣大博厚,且擁有思想與現實雙重勢力的齊桓-管仲新思潮。不妨說,這兩個不同思想道路之爭——可視作當時的“古今之爭”——構成了春秋思想界之張力與境界。據此,我們可以補充《漢書·藝文志》的說法,諸子不僅為六經之支流,同時也是齊桓-管仲之支流。溫情、和諧、理想與強力、秩序、現實,不同的價值追求糾結于兩個思想道路之長期對峙中。對待春秋思想界張力的立場與態度之差異構成了“百家爭鳴”的實質內容:老子對禮樂文化系統與形名事功思潮一并否定;孔子試圖否定、超越形名-事功思潮,而欲恢復、重建禮樂文化系統;老、孔由此開辟并使中國思想走上“形而上”道路。子產等法家、孫武等兵家及鄧析等形名家則自覺批判禮樂文化系統,繼承并系統完善形名事功思潮。簡言之,詩書禮樂老傳統與齊桓-管仲思想新勢力之對立構成了春秋思想展開的必要張力,在此張力展開過程中,超越“形”而走上了“形而上”道路,由此確立了中國哲學的運思方向。正視此兩股思想力量,尤其是齊桓-管仲掀起的形名事功思潮,為準確理解春秋思想世界及諸子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學系教授;摘自《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