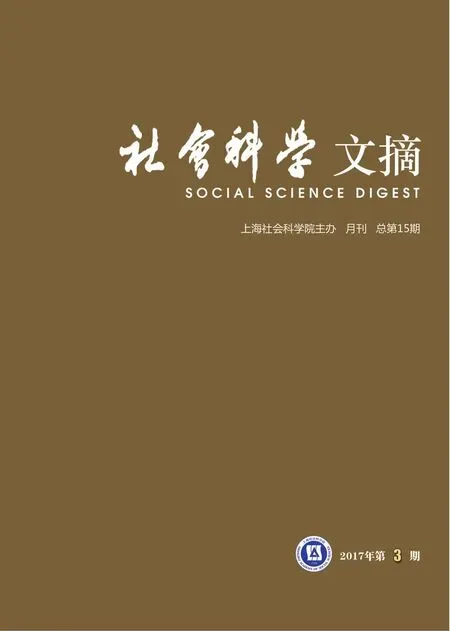現代民主的和平悖論及不平等
文/劉圣中
現代民主的和平悖論及不平等
文/劉圣中
民主觀念和民主制度從古典時代的城邦理想轉變為現代社會發達國家的標志性政治框架,隨著全球化浪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們似乎越來越清晰地發現民主的背后蘊藏著深深的秘密,民主制度之內還夾帶著無法逃避的宿命般的悖論。
古典民主與現代民主的分野:政治與市場
古典民主源自古希臘的城邦和廣場,城邦內的公民都享有基本的參與審判和投票權,有平等而自豪地參與決斷權(亞里士多德),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對城邦事務的意見和看法,并投票決定是否選擇某位公民擔當執政官和其他職位。古代雅典民主的意義在于它能使自由成為可能,“它不只使雅典人在一個相當穩固的基礎上成為自己的統治者,而且使他們按照他們個人或共同選擇的方式生活,毫不吝惜地保護他們的私人機會免受任何強權的威脅——這些威脅或者來自雅典內部,或者來自別處”。(鄧恩)古典民主是一種整體的民主,以統一性、一致性、參與型和非常嚴格的公民資格為標志。(赫爾德)而進入現代社會,民主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民主不再立足于政治共同體,而是立足于個人。通過代議制選舉出來的政治官員從自己所代表的立場出發作出判斷和選擇,政治決斷就在簡單多數中妥協和產生。他們所決斷的事情以及所代表的人民之間被隔離開來,這種代表制度讓民主過程變成一個二次行為。政治已經無法還原為古典時代的政治中介性,而是成為眾口難調的、討價還價的、利益糾葛的政治角力場。它消散了古典政治的整體感。正如貢斯當所言:在一個現代商業社會,要重建一種同樣專注的、不知疲倦的、全體公民共同分擔城邦中心的政治機構的責任和義務的民主制已不可能,并且,這種徒勞的重建要求必定會侵害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使其為之付出可怕的代價。與古典民主相比,現代民主與市場經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它是一種為現代市場經濟提供保護的民主體制。商業帶來自由,也賦予了民主權利。反過來,民主制度則強力保護市場機制,民主的決策也因此遵照市場原則,常常為市場辯護。那么,這種分野將民主帶向了何處?其背后有著什么樣的秘密法則呢?
現代民主的秘密:資源的占有制度
現代民主與古典民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立足于個體的民主,它從市場和商品交換中獲得力量,乃至價值。現代民主的價值和自由觀念來自市場的斗爭和切身的體驗,成長于市場的第三等級和商人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爭奪與貴族階級相等的政治經濟地位,他們起而抗爭,從而獲得了寶貴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權利。“新興的鄉紳和資產階級找到了團結全國的力量參與最高政權,掌握一部分政權直至奪取政權的最好組織形式。”(郭方)在這場現代政治的抗爭過程中,正是市場和經濟為他們提供了動力和支持,所以市場就成為了民主的基礎。而現代民主的秘密也恰恰藏在這里。維護市場是現代民主的天然本性,而維護市場的延伸就是維護資本。現代民主的秘密也恰在此處。
按照索托的研究,資本的秘密即資源的所有權。正是這種對自然物或者說資源的所有權,給資本主義體系提供了聯結、合作、競爭與進步的原動力。資源和財產所有權讓資本主義世界獲得了長足的飛躍式發展,并成為發達世界“自由的基因”之一。(漢南)所以說,對所有權的維護和擴展是資本主義的命根子。洛克在他的《政府論》中也明確地指出著名的洛克式限制條件:“勞動在萬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業上面加上的東西,這樣它們就成為他的私有的權利了。”當然,占有應該以物的恰當使用為限度,然而貨幣的發明卻讓人們可以擴增其無限占有的機會。這就是資本占有正當化的理論辯護。同時洛克也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著名論點:“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財產”,這一點很清晰地指出了現代民主與資本之間的關系。
民主制度所保護的資本主義從一產生開始就不僅僅局限于一個主權國家之內,而是在全球范圍內拼命地爭奪和占有各類資源,以實現利潤和資本的最大化。縱觀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可以說,沒有海外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的資源與市場,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發展和延續到今天的。從資本主義拓展世界市場的開端到大發展,乃至后資本主義時期,無不如此。當時間推移到21世紀,當今資本主義世界正日益遇到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的困境,這恰恰是當代資本主義掠奪式占有資源在全球主權國家遇到層層阻力之后而呈現出來的困境。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海外市場瓜分完畢,海外市場的競爭與利潤鏈條的中斷是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漸衰弱的根本原因。這種衰敗及其產生的沖突和危機最先在發達國家最薄弱的鏈條上產生,如南歐的小國希臘、西班牙等。
帶給發達國家“緊箍咒”的并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另外一個根本性的要素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真正的詛咒。這就是地球有限資源與環境發出的資源詛咒。有人預計,地球上所有的礦產資源將在未來的30年耗盡,地球上主要的資源如石油將在未來的18年內耗盡。(斯蒂芬·李柏)如果這個預計成為現實,我們無法想象未來的資本主義將走向何處?資本主義的幽靈將在其帶給世界瘟疫一般的資源耗盡式的瘋癲之后,逐漸煙消云散。
在資本主義世界里,民主與市場是相伴相生的。民主為市場保駕護航,市場為民主提供物質基礎。然而市場卻有著固有的缺陷,這種缺陷將給民主機制帶來挑戰和壓力。有學者總結了市場的三大缺陷:(1)限制了人們在福利事業進步中明確的推動力的信仰;(2)市場效率與分配公平之間缺乏聯系,自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的失敗及對環境保護的失敗;(3)看不見的手無法確保個體在追逐財產、地位優勢等個人利益時能同時導致社會福利事業總體的進步。(理查德·布隆克)市場機制不能解決的問題,終究要交給民主制度來落實,然而民主制度在落實這些問題的時候并不能確保一定按照更加符合人類理想的方向來開展,而是極容易被民主的政治競爭性裹挾,帶入到無休止的爭斗甚至暴力威脅當中。所謂民主和平的自由體制很可能轉變為利益占有者和暴力掠奪者的專斷體制。
現代民主的和平悖論:內外有別
索托認為,“所有權使資本更加友好”。然而,現實告訴我們,目前的資本主義世界正陷入一種所謂的和平悖論當中,即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發生(或者說沒有)戰爭與民主國家成為20世紀最主要的戰爭策源地之間的悖論。
“民主和平論”自康德開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假設。其后許多學者也都延續著這一觀點,并提供了理論和實證方面的論證。但是,無論這一公理存在多大的可能性,但它卻與另一個殘酷的現實是相悖的,這一現實反過來也證明民主和平論的有限性。這一現實即二十世紀主要的民主國家是世界上主要局部戰爭的策源地(特別是美國以及其盟友國家北約成員國)。那這一悖論的形成究竟是什么根源呢?其背后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總的來說,這兩者并不是一種互不相關的關系,不是偶然產生的,而是有著特殊的互為因果的關系。前者恰恰是后者的結果,沒有后者就沒有前者。民主國家之間不發生戰爭雖然從目前來看有一定現實性,但是這并不必然意味著他們失去了戰爭的激情和動力。那么,為何他們在沒有失去戰爭動力的情況下卻還可以避免國家間爆發戰爭呢?究其根源在于,這些國家之間暗存著一種自動化解戰爭的機制。在許多人看來,這是因為民主國家內含的民主決策機制,決策的民主化保證了暴力手段的謹慎控制。當他們遇到同樣類型的民主國家時,通過民主程序來反映多數民意的制度,可以有效緩沖各種激進的暴力傾向,因為人民反對戰爭,人民的反對可以防患戰爭的發生。(斯蒂芬·平克)然而,同樣是民主決策卻也是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戰爭的制造者,正是民主機構中的議員們通過法定的投票機制決定了每一場針對非民主國家的戰爭。從這一點看來,民主決策機制并非是民主和平的根源,那么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實際上,結合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們不難發現,市場和資本因素在這里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市場和貿易有一種和平的綏靖功能,也可以稱之為市場的綏靖機制。康德就提出一種和平三角理論,其中重要的一角即商業貿易。市場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有了國際市場,有了可以瓜分的蛋糕,戰爭的可能性就被消減了。20世紀初期,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時候大多數時間是相安無事的,甚至是結成了同盟。但也有擦槍走火的時候。英法在非洲的戰爭、日俄在中國的戰爭、美西在美洲的戰爭等都是例子,而這正好說明了民主國家之間曾經不是和平的,為了爭搶殖民地也發生過真實的戰爭。
市場的綏靖在一定程度上基本上是有效的,但是其前提是市場有效。在市場有效時,市場發揮的綏靖功能讓民主國家劃分市場資源和產品中能夠理性地保持了一定時期的和平。但是,一旦市場出現無效,民主國家間無法理性地分享各種市場成果,甚至會因為國內環境的倒逼,加大民主國家之間的競爭和惡斗,這時候這種綏靖就會自動瓦解。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消除民主國家深藏起來的戰爭的原始動因。曾經的盟友片刻之間就會變成敵人。這方面,波蘭尼的論述非常深刻而且有力,他的著名論點“自由放任是有計劃的,而計劃卻不是”,意指自由市場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在民族國家背后的強力推動下逐步發展的。他揭示了現代政治經濟過程中的三次大轉變,18世紀統一市場的建立,19世紀針對市場的社會保護主義普遍的建立,更重要的轉變是20世紀30年代市場經濟保護運動所衍生出來的巨大災變:法西斯主義與蘇聯式社會主義。自由市場的發展演變成了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包括民主國家體系內部和外部的戰爭。
根據市場的現代性要求,民主國家遵循著這一鐵的規則,努力維持和鞏固著世界性的市場秩序,一旦哪里出現不和諧之處就會產生重大的壓力,導致采取戰爭性暴力手段來達到目的。因此,我們所看到的發達國家同盟對付某個小國的不平衡戰爭經常出現。盡管我們也無法否定戰爭發動者所主張的國際正義理由對戰爭的作用,但是我們同樣也不能否定作為政治之核心要素的國家利益在其間所發揮的重要功能。正如艾森斯塔德的分析:現代性有一種破壞性力量,是這種破壞性力量帶來了世界戰爭和種族屠殺,這可以從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后的種族屠殺得到驗證。“所有這些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與現代性的樂觀主義觀點相反,現代性的發展與擴張事實上并不是進步的、和平的。”艾森斯塔德所言的現代性,恰恰是資本主義現代性,是一種市場無限擴張、利益無限追逐的現代倫理要素。
現代民主的不平等后果
立于資源無止境占有和消耗的全球資本主義陷入和平悖論而難以自拔,其根源不是某個或者某些民主國家具有好戰的秉性,而是現代民主與生俱來的秘密所帶來的自我紊亂。它也會帶來嚴重的不平等后果。
(1)現代民主的第一個不平等后果就是國家體系之間的不平等
和平悖論的本質是圍繞占有資源的斗爭,這種爭奪資源與反爭奪的斗爭必然導致雙方的資源大損耗,會更加速資源枯竭的步伐。戰爭勝利者可以依靠資源剝奪而暫時領先,享有資源的好處,戰爭失敗者則獨自品嘗其苦果。所謂的自由市場體系難以在戰后重建,如果真的建立起來,那也是戰勝方的市場體系。誠如布羅代爾所言:“資本主義仍然建立在剝削國際資源、利用國際機遇的基礎之上的,換言之,它以世界為存活的范圍,至少它是向世界伸展的。它當前的大目標是:重整全球主義的旗鼓。”全球主義是強者的全球化,而不是弱者的全球化。全球化必然帶來難以彌合的不平等。日本學者也曾論述道:“全球化資本主義問題的根源在于,現在商品和貨幣都跨越國境自由翱翔了,而控制他們的主體卻仍然是分散存在的國家。”(中谷巖)
(2)第二個不平等的后果是戰爭動員體系下公民政治和生存權利的剝奪
為了維持在全球體系中的優勢地位,民主國家必須保持著強勢的軍事能力,這樣才能實現經濟市場全球化和維持和平、優雅、奢侈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在蘇聯垮臺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體系一下子找不到敵人,但是又不能削減其戰爭儲備力量,于是陷入了所謂的“過剩的帝國主義的無限戰爭”的狀態。這種帝國主義不僅不會削減去軍備開支,反而要強化、保持永恒的軍事強勢地位,將所有可能的敵人都置于其監控之下。這種模式終究會一定程度地剝奪國內公民政治和生存的權利。高度戰爭動員狀態的民主體制是一種不平衡的體制,也是一種相對缺乏彈性的體制。
(3)第三個不平等的后果是民主代議制過程的不平等
現代民主作為一種代議制民主,“作為一種旨在保護資本主義經濟的政體形式,將難以避免消逝的命運。代議制民主也沒有辦法自己提高其對現在所面對的眾多領域的——國內的和國際的——實際問題的處理能力”。(鄧恩)關鍵的問題是在代議制民主的過程中容易出現兩種結果:代議民主的寡頭化替代和技術化肢解。所謂寡頭化替代是指代議制過程中掌握經濟資源的政客或者資本家能夠利用手中的資源來掌控選舉和決策過程。民主有時候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用一個國家公民們的個體生命去換取另一個國家的政治災難以及延續前者命運的戰略資源。而所謂的技術化肢解是指大空間范圍的民主只能通過電視技術或者網絡技術來推廣其平面形象和模式化語言,而選民們也只能在這種有限的單調的虛擬的形象和認知中進行決斷。這可以說是一種殘缺的選舉政治。
后自由主義民主是否可能?
美國學者提出過一種未來的民主模式:后自由主義民主。這種民主用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來替換自由主義民主模式,即:“追逐利潤的資本市場為民主地負責的投資和資源配置的計劃所取代,工作場所和其他共同體通過代表制和參與制而組織起來,實現經濟不平等的弱化。”(塞繆爾·鮑爾斯)他們希望用一種新的計劃模式來替換純自由的放任的逐利的資本市場體系,并且希望通過民主參與的深入來解決工作過程中的控制、經濟依賴和不平等問題。舒馬赫也提出了一種小的經濟模式,認為回歸到原生的、中層技術的、當地化的經濟狀態更有可持續性。
總而言之,政治的回歸是未來人類社會必須直面的重要問題,如何尋找更好的,能夠超越現代民主的模式,來構建新的共同體和生活道路,是我們需要認真思索的問題。
(作者系江蘇師范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摘自《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