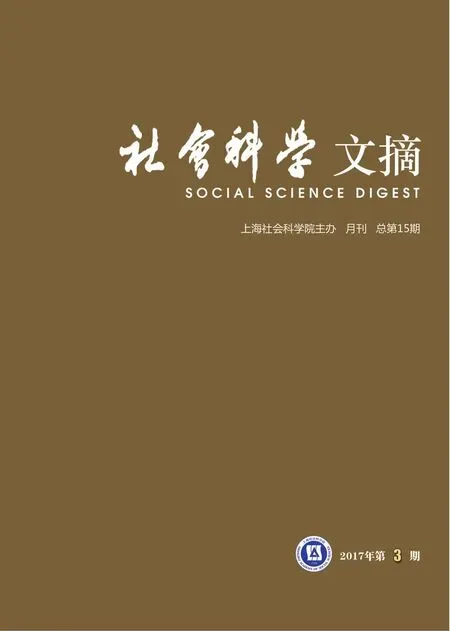想象世界與中國文學空間的早期建構
文/曹勝高
想象世界與中國文學空間的早期建構
文/曹勝高
從文學形成的角度來看,文學空間是指攝取到文學文本之中的想象世界,無論這些想象是基于現實還是超越現實,在作品中都被作為一個獨立而自足的存在,成為中國文學抒寫情志、表達理想與寄托愿望的所在。如果要描述中國文學格局的形成,早期的想象方式如何拓展開中國文學空間,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諸如神話傳說、巫術視角、地理圖式、時間認知是如何匯聚到兩漢學者、作家們的知識體系之中,并成為其塑造文學空間的基本要素,很值得我們系統討論。
周秦文學的空間建構
討論文學空間的建構,需要明確文學空間的存在形態,不是文本描寫中的某些單一構造,而是融匯著作者想象、文本描述和讀者還原三位一體的立體結構。這是因為,從創作過程來說,作者的構思是以其對客觀世界的理解,建構出一個相對真實或者虛幻的世界。在這其中,所謂的真實是作者按照生活的邏輯去描寫,盡管有些生活的邏輯被后世認為是虛幻甚至荒誕的,但由于當時作者是信其實有的,例如神話對天地秩序的理解,屈原作品中上昆侖、求神女等描寫,作者多以實寫的方式出之。而所謂的虛幻,也包括作者信其為虛幻而自覺以此進行文本建構,如《山海經》中的巫術描寫以及《海內十洲記》中的神仙想象等。
如果我們以作者自覺與否來衡量文學空間,就能相對容易地把握作者對文學空間的建構,是以現實空間、歷史空間和想象空間三個維度去實現的。現實空間是作者生活其中而實有的;歷史空間是作者對過往事件的追述,這種追述是基于時間還原而產生部分想象;想象空間則完全是作者超越生活現實環境而虛幻出來的更為寬廣博大的意識流動之所。中國文學的空間在其形成之初,便以此三個基本的空間感存在。
現實空間,即第一空間,作為生活的真實存在,是文學空間建構的基礎。這種建構完全遵從生活的經驗、方式和習慣。先秦文學中的故事敘述,則是依照現實生活重新進行建構。這類建構的目的是為了突出某些人物的德行,或者強化某些生活經驗。文學空間的形成,正是這些取自生活而又精于生活的描述,使得文學表述與生活常態有了本質的區別。這些區別的強化,便是文學特征得以進一步確立。如諸子散文、策士論政中所刻畫出的人物形象,便是通過異化進一步明確其特征,形成了一個個迥然不同于現實的文學表述空間,如孟子口中的“拔苗助長”“齊人有一妻一妾”等,都是通過對現實生活中某些人、事進行異化的處理,夸大其做法的荒誕,強化其不符合生活邏輯的部分,給接受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諸子和策士們在說理時勾畫出的這些不合生活邏輯的形象,不僅沒有得到接受者的質疑,反而有助于說明、論證其觀點的合理性,其原因在于作者、接受者在聽聞這些故事時,進入到了一個“相對虛構”的空間中。這種區別于現實存在的虛構空間,是以通過想象實現的,便區別于歷史的求實性;這種虛構是按照現實的邏輯進行處理的,便區別于神話的幻想性。可以看出,文學空間的形成,最有效的手段是對現實空間的典型處理。
歷史區別于文學在于其更注重真實性,也就是說歷史更在意其敘述的人物、事件、制度等是否更符合客觀存在,而文學在此類敘述之中,更注重其中的典型性和獨特性。因此《詩經》里對周民族某些本立意于客觀存在的史實,卻因為富于想象而更接近于文學。如《大雅·生民》中姜嫄“履大人跡”而生后稷的描述,便使得敘述的歷史附帶了想象的成分,這種帶有夸張性質的描述,從來源上帶有神話的痕跡,從筆法上看則是典型的文學手法。這種基于精神生活而形成的第二空間,是經過藝術化處理過的新的結構,便是文學空間。
對歷史事件來說,歷史性的想象,一種是歷史追述中的想象,是要先有其事,然后對其進行演義,其是以歷史事實為根據的;另一種則是歷史想象,即這類想象雖然是以歷史的手法寫出來,但主要是在對精神世界進行描述,是以虛構為旨歸的。我們由此觀察歷史敘述,就會發現在看似真實的敘述中,常常蘊含著某些虛構的成分,如《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左傳·宣公十五年》“魏夥不聽亂命”之類的鬼神之事,便是基于想象而形成的文學化處理。這種處理有兩個指標:一是歷史敘述者對某些無法解釋的歷史事件、歷史進程或者歷史邏輯試圖進行解釋,只能借助于想象世界中的某些要素,使歷史敘述得以合理;二是這類跳出生活邏輯而進行的敘述,使得歷史不再是一個客觀時間、現實地點和事件真實所融合而形成的二維空間,而是可以通過神異能力、夢境體驗等方式跳出二維空間而形成的三維空間。
如果說二維空間源自于生活實踐,三維空間則更多通過想象、變異、比擬等方式,形成一個超越現實之上的敘述空間。我們可以用想象空間來命名,類似于西方敘事學理論所謂的第三空間。如《戰國策·齊策三》中蘇秦謂孟嘗君所言,土偶與桃梗可以直接對話,全部出于虛構。
這類出于想象而構建的文學空間,完全超越了現實世界而形成一個相對自足、相對完善的藝術空間,在這樣的藝術空間中,人可以不再為現實所束縛,如《莊子》中的“藐姑射山之神人”可以跨越時間,“枕骷髏而臥”“鯤鵬高舉”“任公子為大釣”之類想象可以超越空間,形成一個多維的藝術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敘述者與作品中人物可以自由地與萬物交流,引導讀者進入到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可以滿足人渴望超越現實局限的愿望,使得這個空間具有了合理性而為讀者所接受。可以說,以現實空間、歷史空間、想象空間三維并存的空間結構,是周秦時期對文學空間建構的基本方式。
秦漢文學空間的建構方式
早期人類對空間的理解,是融合著生活經驗、宗教意識與現實渴求而形成的一個多元空間。在這其中,生活經驗作為建構空間的基本尺度,可以依照相似律建構起想象空間的基本要素,使得這類想象按照人類的生活邏輯進行。宗教意識作為形成空間的想象源泉,是通過超越自然的神力的描述,作為解釋自然形成、社會形態和人生困惑的理據。現實渴求則作為組建空間的精神動力,決定了想象空間的基本指向,是要超越現實的困境達到一個更加自由的想象世界。
我國吉林大學的曾平等人基于控制移動機構和支撐面之間摩擦力的方法,研制了一種慣性式壓電驅動器,如圖11所示[20],該驅動器最高速度達到1 mm/s,最大承載力為1 000 g,位移分辨率達到20 nm。
生活空間是人們在生活中逐漸形成的四方概念,常被作為最基本的空間架構。生活空間是現實的客觀存在,但在現實空間之外的未知空間進行描述,則需要借助于想象,形成一個陌生化、異己化的想象世界。例如《山海經》在構思上,是以當時人的生活地點為中心,展開方位描寫,在這些越來越遠的空間中,動物、植物、礦物、醫藥、巫術、宗教、民俗也越來越奇異,這些奇異性源于人們的原始宗教意識,其中所形成的奇異描寫,恰恰是出于人們對于超越現實生活局限的渴望。
想象境界一旦打開,藝術就不再是循規蹈矩的生活場景記錄,而是充滿著瑰麗恍儻的形象,洋溢著被解放出來的精神活力。正因為遙遠的空間不可到達,才可以按照作者現實渴求進行無拘無束的想象,既可以靈異如《山海經》,也可以恐怖如《大招》。在這類自由的想象世界里,與現實生活空間的寫實性描述不同,文學性的想象被強化,從而構筑出一個多彩多姿的藝術世界。
地理區域的拓展,給予了人們更多的想象空間,可以使得人們按照自身生活的經驗,依據原始宗教的邏輯,盡情地暢想那些現實中不可獲得但又充滿渴望的那些超自然的現象,作為現實客觀存在的補充。漢魏時期形成的博物類小說,便是按照這一邏輯展開的,例如《海內十洲記》便是按照《山海經》的地理空間邏輯,對諸多海上島嶼進行了描寫。《漢武帝洞冥記》更是雜記仙境、靈藥、奇木異獸之類,形成一個光怪陸離的靈異世界,辭藻可以豐縟,文華足以熳麗,敘事頗呈玄怪,為中國博物、志怪小說的形成不斷積累經驗。
文學空間拓展的另一個模式,便是不斷深化文學形象的塑造,細化文學敘述的筆觸,使得原本粗線條勾勒的文本,可以形成細膩的肌理。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對原先的故事模型進行重述,形成一個更為具體、更為細致、更為明確的文學空間。例如原憲居魯一事,原見于《莊子·讓王》,后《韓詩外傳》重新敘述,這使得原憲安貧樂道的形象更加鮮明。這類增益的故事敘述,實際是在原本拓展的文學空間中,補充了諸多細節,使得故事仿佛從白描變成了素描,可以更加立體地得以呈現。這種看似簡單的做法,是中國文學空間拓展時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如果說《山海經》到《海內十洲記》《漢武帝洞冥記》的發展是拓寬了文學空間的容量,那么諸子散文到《韓詩外傳》《說苑》的發展,則是提升了文學空間的質量,使之更細密、更具體、更精致。這兩種方式內外結合,保證了文學空間的雙向拓展。
文學空間的這種雙向拓展,很類似于王充所謂的“語增”;而融合著想象對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和作品場景進行增益,則類似于王充所謂的“虛增”,即相對于生活現實,作品中增加諸多神話色彩的想象、靈異的藝術描寫,使得文學敘述呈現出虛實結合的傾向。其中的虛,既包括文學筆法的虛構,更包括作者想象的虛幻。例如《竹書紀年》載:“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在《穆天子傳》中,更注重細節描寫,使得《竹書紀年》中寫實性的歷史敘述,轉化為真實可感的文學描寫。正是其中“多言寡實”“恍惚無征”的想象,使得《穆天子傳》成為歷史小說之祖。
通過想象的增益而開辟文學空間,是秦漢文學性增強的基本手法。這些手法有時來自前文所言的踵事增華,有時則來自神仙、巫術的附會。從周秦文學來看,神靈護佑出行的觀念,作為周秦時人的一種信仰,在文學作品中大量出現。最典型的莫過于《離騷》中屈原對上昆侖的描寫,以風伯、雨師為使。《九辯》《遠游》所言更為詳細,太昊、玄武、文昌、風伯、雷公、雨師皆為其驅馳,不斷增虛,形成了騷體賦出行場面的宏大描寫。至司馬相如《大人賦》中,這種游仙性質的描述便成了經典的文學想象,將前文所言的空間鋪排、文學增益和想象虛構三種模式融合為一,形成令武帝飄飄欲仙的想象空間。
如果說對生活空間的鋪排,在平面上拓展了想象空間,使之更加博遠開闊;那么不斷增益的想象細節和描述筆法,則豐富了想象空間的內在,使之更加具體生動;而借助于宗教、巫術、信仰和神仙觀念而形成的虛幻空間,則使得想象空間更加立體多維,為文學表述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也給作者提供了全新的藝術體驗,為讀者提供了豐富多彩的藝術感受。
文學想象與精神生活
想象力是文學作品產生不可或缺的條件。沒有想象,就沒有文學;想象越豐富,空間感越大,文學塑造的可能性就越多。優秀的文學作品,正是作者馳騁想象于文本之中,建構了一個自如、自足的文學空間,才能讓自我的情緒得以表達、構思得以實現,才能讓讀者如同親炙,感知并進入到栩栩如生的文本空間,去還原、去想象、去認同。陌生化的想象是以異己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目的是滿足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渴求,其想象中的世界常常與現實生活場景截然不同。文本所塑造的陌生空間,是以滿足人的好奇心和想象欲望為特征的,它可以讓作者、讀者暫時忘記現實。熟悉化的想象是用律己的方式,建立與現實生活類似的想象空間,例如《神異經·東荒經》中的東王公與玉女燕飲、投壺游戲等場景,便是按照帝王生活形態設計出來的;而其人形鳥面、白發虎尾的形象則是按照《山海經》塑造神靈的方式想象出來的。
由此觀察,文學空間建構具有兩個基本路徑:一是熟悉化的想象,意在塑造一個接近于現實感受的空間,讓讀者在切己的氛圍中身臨其境地感受現實生活。而陌生化的想象,則意在建構一個完全異己的空間,形成完全不同于現實邏輯的客觀存在,作為對現實的超越。但這只是從理論對舉的角度闡釋,在具體的創作之中,切己和異己是相對存在的,不是絕對分離、截然對立的。由于熟悉和陌生本是相對的概念,某種現實生活樣式,對某些人是熟悉的,對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陌生的。同樣,某一文學空間,對了解其背景者而言是熟悉的,對不甚了解者而言則是陌生的。二是由于生活時代不同,某些想象對當代來講,是想象的虛構的;對于未來而言,可能就會成為真實的存在,比如古人日行千里、行于云上的想象,現在已經成為現實。某些想象,對過去來講可能認為是真實存在,對未來來講便只能是虛構,古代關于天宮、地獄的描寫,古人出于知識的局限便信以為真,今人不視之為實有。所以,想象構成的空間分野是相對存在的,而不是絕對存在的。
熟悉的陌生化、陌生的熟悉化是建構文學空間的基本想象模式,將生活經驗、前代傳說和藝術想象結合起來,形成一個亦虛亦實的文學空間,使之既有合理性,又有超越性,才更能滿足讀者對文學空間的想象渴求。
作者樂于通過想象塑造文學空間,或者讀者更喜歡充滿想象的文學空間的基本動因,在于將文學空間視為精神生活的存在方式。正是由于想象空間的建構,才使得文學作品區別開了現實生活,現實生活中不可獲得的能力、不能實現的愿望以及無法得到平復的情緒,都可以在文學空間里得到滿足。即便是很簡單的詩歌意象,也是作者將物象從現實生活中選取出來進行加工,選取和加工的過程融入了作者的價值判斷,帶有作者的主觀傾向,作者的人生體驗、現實愿望與內在情緒,可以在文本所建構的想象空間中得以實現。
文學想象是緩解作者精神困頓的一種模式,可以通過藝術世界的建構,進入到另外一種精神愉悅中去。由此來觀察中國文學空間的形態,就會發現很多時候作者塑造的目的,在于追求精神上的滿足。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就是亂世之外的理想世界,郭璞游仙詩中的場景也是現實中不可得的暢想,李白作品中的虛幻正是作者渴望超越的精神表述,從而使得文學空間不單純是想象的世界,更是精神生活的一種方式。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摘自《中國文學研究》2016年第4期;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秦漢國家建構與中國文學格局之初成”(12BZW05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