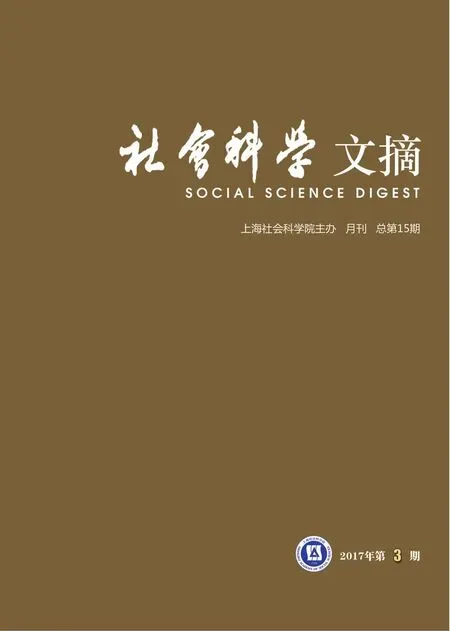文化心理結構、倫理變遷與鄉村政治
——陳忠實筆下20世紀中國鄉村社會的“秘史”
文/張勇
文化心理結構、倫理變遷與鄉村政治
——陳忠實筆下20世紀中國鄉村社會的“秘史”
文/張勇
陳忠實的小說創作,從《白鹿原》所展現的20世紀上半葉的鄉村變遷,到21世紀初期幾篇短篇小說中所揭示的農村現實,幾乎完整記錄了整個20世紀中國鄉村社會的“秘史”。20世紀中國經歷了帝制的崩潰、現代的創生、戰爭、革命以及此起彼伏的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一個世紀。如何透過這些紛繁復雜的事件和關系去把握20世紀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是極具挑戰性的。《白鹿原》這部著作不僅具備了盧卡奇所說的“史詩的本質標志”——對“共同體的命運”而非“個人的命運”的關注,還運用了正確的歷史方法,即在主要社會力量的關系之中考察歷史的走向和共同體的命運,而非在這些關系之外建構另一種歷史圖景。
《白鹿原》展現了某種“民間歷史”,但這種“民間歷史”是被置于政治、社會的變遷之中呈現的,而非孤立甚至對立于政治、社會變遷的。因此,《白鹿原》更像是在“革命現實主義”延長線上所產生的杰作,它非但沒有以“民間歷史”置換“革命史”“政治史”,而且將“革命史”“政治史”當作了重要的表現內容。在陳忠實的其他小說中,鄉村政治也是作家始終重點關注的對象。這在新時期以來濃厚的消解政治、拒斥政治的文學氛圍中,是難能可貴的。布羅代爾曾引用埃德蒙·法拉爾的話說,“正是對大歷史的恐懼扼殺了歷史”。 中國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中大概也存在著類似的“恐懼”,而《白鹿原》和陳忠實其他一些創作的價值正在于將“大歷史”重新帶回到文學的視野之中。
“文化心理結構”及其“剝離”
“文化心理結構”是陳忠實談創作時最常提及的概念。這個概念最初由李澤厚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它的內涵與之前更為常用的“民族性”“國民性”有較大重疊,不過,“文化心理結構”呈現為中性色彩,不像“民族性”尤其是“國民性”那樣,在中國近代以來語境中被賦予了明顯的貶義。以“文化心理結構”取代“國民性”,不僅意味著對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價值評判上的變化,同時也關涉到對中國現代化實踐的重新評價。
“文化心理結構”學說并未讓陳忠實否定中國的現代化實踐,它的啟示性在于為作家提供了一個透視歷史變遷的視角。“文化心理結構”的承載者通常是作為群體的“民族”,它與其說來自對于民族共性的實際觀察,不如說源于某種理論預設,反過來又限制了對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豐富性、復雜性的認知。陳忠實以“文化心理結構”來解釋作為個體的人物及其差異是一種誤用,卻恰恰彌補了該學說可能帶來的武斷。也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陳忠實沒有循著“文化心理結構”走向“尋根文學”,他對個體“差異”的興趣決定了他的落腳點在于“演變”——“民族的精神和心靈演變的秘史”。
首先,陳忠實關注的是人的多樣性和社會、生活的變化。作家甚至在一些短篇小說中,也試圖勾勒人物的轉變,如《失重》《轱轆子客》《兩個朋友》等。其中有的篇目由于未能運用恰當的敘述結構或技巧,仍然按照時間順序平鋪直敘,不免給人以倉促之感,藝術上也算不上成功。陳忠實常常是以長篇小說的思維方式和結構形式來創作中短篇小說的。其次,陳忠實雖然像大多數作家一樣,在批判現實的基礎上構筑起自己的文學,但是未從根本上動搖過對于美好未來的信念。現實的問題不會上升到對于現代化途徑優劣、對錯的思考;對于歷史,陳忠實的興趣在于歷史的具體形態,特別是能夠與自身相聯系的、具體化為先輩生活和心路歷程的歷史形態。在陳忠實看來,歷史的實然便是歷史的必然,歷史上的錯誤不過是通向必然王國道路上的小波折,因此,歷史的應然幾乎不會作為問題進入作家的視野中。當作家系統地審視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道路時,他對歷史必然性的認知更加被強化了。
陳忠實對于中國近現代歷史以及當代現實的認識算不上深刻,反而顯得有些正統甚至于“過時”。這類似于作家所堅持的現實主義、一定程度上還帶有“革命現實主義”印記的創作方法,在新潮更迭、敘事技巧日新月異的80年代文壇所表現出的姿態。陳忠實絕非思想型的作家,也非先鋒實驗型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易被歸入到某個具體的流派或創作類型之中,然而,悖論的是,當文學新潮聲勢浩大時,“保守”或“落伍”反而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
陳忠實自覺地“從文化心理結構的角度去寫人物”,最早可以追溯至中篇小說《藍袍先生》。作家此時對“文化心理結構”的觀察主要是負面的,接近于金觀濤所說的“宗法一體化結構”。作家是從傳統/現代的二元結構來審視“傳統”的,當現代被賦予了正面價值時,“傳統”便不可避免地帶有了負面的品質。稍晚創作的《四妹子》基本上延續了這種思考。
“文化心理結構”常常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決定了農民在思想觀念、情感上與舊事物之間的分離過程是漫長的。陳忠實從自己的經驗中也領悟到這一過程的緩慢與痛苦,他稱之為“剝離”。陳忠實詳細記述了自己“剝離”對農村集體化的信仰的過程:1982年,當陳忠實作為農村干部指導農民落實中央的“分田到戶”政策時,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在進行的工作“正好和30年前柳青在終南山下的長安鄉村所做的事構成一個反動”。直到這一年的秋天,當陳忠實親身享受到“責任制”所帶來的農業大豐收時,他才真正開始了對集體化的“剝離”。在此期間,陳忠實創作了短篇小說《霞光燦爛的早晨》,其中透露了作家對于“包產到戶”政策的隱憂。一方面,作家看到了“單干”所激發出的潛在的生產力;另一方面,作家也洞察到了“包產到戶”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單干”的邏輯已經開始動搖農村的互助倫理。農村中新的現實問題迫使他從另一個維度上思考“文化心理結構”的嬗變,“剝離”因而演變成了“疏離”的問題。
“離鄉”母題與鄉村倫理的衰微
陳忠實幾乎從不在城/鄉二元對照的結構中觀照鄉村,從而也避免了在文明/野蠻或異化/自然的對立視野中將鄉村簡化為某種符號。他筆下的鄉村既非愚昧、落后的代名詞,也非田園牧歌式的烏托邦。長期在鄉村生活和工作的經歷,使得作家很少在類型化的意義上去書寫鄉村。這決定了他筆下的鄉村與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尤其是知青文學中常見的農村形象的差別。如果說陳忠實筆下的鄉村也體現為某種類型的話,那便是“根”或“本”。這里的“根”不同于“尋根文學”中的“根”,它是無需尋找的,是一種自然的存在。在陳忠實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創作中,存在著一個與知青文學、“尋根文學”迥然不同的“離鄉”母題:對精神上離“根”、忘“本”的批判或懺悔。如果把“根”“本”理解為鄉村倫理、生活和做人準則的話,那么陳忠實大部分的作品都可以納入到該母題之中。“離鄉”母題顯現了一種農民式的價值、道德觀念。
“離鄉”母題可以看作是對趙樹理、柳青、王汶石等作家所開創的農村小說敘述模式的一種反題敘述。陳忠實延續了趙樹理、柳青等作家對農村“新”“變”的關注,但是“新”“變”卻不再是“好”的同義詞。《康家小院》的前半部分很像是一個趙樹理式的婦女翻身的故事,玉賢參加村里的冬學識字班,從楊老師那里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但是后半部分卻演變為婦女翻身故事的反題,玉賢發現楊老師只是玩弄了自己,她帶著懺悔重新回到了丈夫身邊。“離鄉—返鄉”的情節模式取代了“傳統—現代”的進步敘述模式。
從《藍袍先生》到《白鹿原》,作家對“傳統”的態度悄然發生了變化,呈現為更為客觀和正面的評價。這種變化源于作家對鄉村現實問題的觀察。80年代中期以后,鄉村社會在經歷了最初的欣欣向榮之后,開始暴露出一些問題。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投機倒把、價格雙軌制、腦體倒掛等中國社會的問題,一定程度上也在鄉村表現出來。作家對這些問題都有所關注,創作了諸如《旅伴》《燈籠》《失重》《轱轆子客》等作品。即使是在這些反映社會問題的作品中,陳忠實也往往側重于從心理或精神的層面去進行把握,作家最為關注的是鄉村倫理及價值觀念的變化。
正是道德喪失的現實,使得作家重新評估“傳統”的價值。此時,即使是《藍袍先生》中反復出現的“慎獨”,也具有了積極意義。對鄉村倫理的關注,讓作家走向了“傳統”并發現了其復雜性。《白鹿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性格鮮明的人物,其中尤以作為“仁義”化身的白嘉軒、朱先生等形象最為動人。在歷史的洪流中,白嘉軒的“恒”與鹿子霖的“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朱先生也有著明確的充當人間“砥柱”的自我期許。這種對做人原則的堅守之所以贏得了讀者的普遍共鳴,也需要置于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道德缺失的語境中來理解:通過這些人物,人們重溫了某種已經變得久遠和模糊的道德信念。作家對白嘉軒這個人物的偏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陳忠實在面對“傳統”時又是足夠清醒的,他沒有單純跌倒在“傳統”這個懷抱中,同時從被壓迫者、被侮辱者特別是女性的角度,看到了“傳統”壓抑性的一面。《白鹿原》道德態度的含蓄,也正是作家此時對“傳統”的復雜態度的寫照。
《白鹿原》之后,陳忠實很少再創作小說。進入21世紀之后,作家零星發表的幾篇短篇小說仍然是在80年代中后期的框架中書寫鄉村。不過,鄉村倫理每況愈下,形同消亡。這可能也是陳忠實很少再寫小說(鄉村)的一個原因。鄉村倫理是鄉村區別于都市的一個重要維度,也曾是陳忠實“離鄉”母題創作的根基,作家確信這種倫理的存在及其優越性。中國的鄉村社會的變遷,完成了從互惠、合作的道義倫理到理性的個人經濟倫理的轉變。隨著鄉村倫理的衰微,鄉村倫理逐漸與都市倫理趨同,價值意義上的鄉村實際上也就終結了。毫不奇怪的是,作家與此同時對故鄉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令他“肅然敬仰”的人物發生了興趣,寫下了“三秦人物摹寫”系列短篇《娃的心娃的膽》《一個人的生命體驗》《李十三推磨》。然而,無論是中條山戰役中的孫蔚如、作家柳青,還是嘉慶年間的劇作家李十三,都已成為歷史,他們恰恰映照出了現實的匱乏與蒼白。
鄉村政治:國家政權的“內卷化”與出路
陳忠實對于鄉村倫理的關注,使得他一直對鄉村政治和鄉村社會機制的變遷保持著敏感。與新時期許多作家著力于反思“文革”不同,陳忠實更為關注的是“四清運動”。相比于“文革”,“四清”運動對農村社會的沖擊更深入、劇烈。就此而言,陳忠實準確地抓住了鄉村政治悲劇的關鍵。在陳忠實的前期創作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塑造了一批農村基層干部的形象。《尤代表軼事》中的老安和尤志茂代表了陳忠實筆下農村基層干部的兩種類型,前一類型還有如《豬的喜劇》中的韓主任、《鄉村》中的葛隊長等,都是不了解農村現實、上級政策教條式的執行者。后一類型則是從農村生活和勞動實踐中自發產生的領袖,如《信任》中的羅坤、《鄉村》中的泰來、《梆子老太》中的胡長海和胡振武等。鄉村政治的悲劇源于前者對后者的粗暴打擊,培植出了像“梆子老太”這樣的政治怪胎,造成了國家權力與群眾之間的裂隙。
在新的歷史時期,“好干部”的界定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首先,“好干部”體現為對自己歷史錯誤的正確認知和懺悔意識。《土地詩篇》《土地——母親》都是寫地方干部對土地、母親、人民懺悔并得到寬恕的故事,寄寓了作家對于新的干群關系的期盼。其次,“好干部”應該有勇氣通過自己的努力修正歷史錯誤,繼續帶領群眾生產、致富。在《反省篇》中,作家深入思考了“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地方干部職能轉變的問題:干部可能會從“瞎指揮”的極端走向“不指揮”的極端,或者忙于自己致富,造成農村一盤散沙的局面,如小說中河東公社的情形那樣。不幸的是,作家筆下的河東公社后來成為了中國鄉村更為普遍的形態。農民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孤立、無序地勞動和競爭;基層干部對這種經濟生產基本采取不作為甚至是為己謀利的態度。
《白鹿原》中忠實地記錄了中國當代鄉村的前史。白鹿原鄉村的結構性變化始于“鄉約”成了“官名”,官僚機構的膨脹不僅帶來了賦稅的增加,更為重要的是它破壞了舊的鄉村結構。隨著國家權力向鄉村的逐步滲透,原先由“鄉約”和族長維續的鄉村秩序讓位于“鄉約”“甲長”所代表的國家權力,鄉村由德治、自治轉向政治統治。在《白鹿原》中,“交農事件”是國家權力與鄉土社會相遇的一個象征性時刻。“交農事件”之后,白鹿原上出現了兩個變化,一是“‘鄉約’的條文松馳了,村里竟然出現了賭窩”,二是保障所新組建了配備槍支的“民團”。二者之間并非沒有關聯,國家權力的強化與鄉村社會自治力量的衰弱總是同時發生的。
杜贊奇曾借用吉爾茨的“內卷化”概念,以“國家政權的內卷化”來描述“20世紀前半期中國國家政權的擴張及其現代化過程”。及至20世紀后半期,國家權力的擴張也未停止。集體化時代,“國家史無前例地滲透到農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地方制度和農民價值觀失去了根基”,“村社準則、鄉規、共享的觀念,退出了公共話語空間,甚或不復存在”。 新時期以來,國家權力雖然不像之前那樣將鄉村社會置于嚴密的控制之下,但是農村干部卻迅速轉向杜贊奇所說的“贏利性經紀”,成為鄉村社會發展的新的阻礙因素。
從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來看中國20世紀的變遷無疑是一個頗富啟發性的視角,然而,它也潛存著將國家與社會對立看待的危險。最為極端的情形便是:否定國家所有的社會計劃包括社會解放與革新的努力;以“傳統”“自治”等名義,遮蔽或美化社會既有的問題。黃宗智認為,基于現代西方經驗的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模式并不適合于考察中國的情形,中國“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一個第三空間,而國家與社會又都參與其中”。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如帝國晚期、民國時期和當代,都曾發展出一些不同形式的“第三領域”。在這個領域內,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協商性而非命令性的”。“第三領域”的歷史經驗也可以為解決當代中國農村社會問題提供有益的思想資源:需要重視和發揮鄉村社會中自發形成的地方精英的結構性作用。村莊作為國家政權與地方社會直接相遇的接觸點,村莊干部應該是村莊中的精英,而非國家政權內卷化中最低的一個層級。各級地方干部也需要從官僚尤其是“贏利型經紀”的角色中轉換過來,成為農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帶頭人。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摘自《文學評論》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