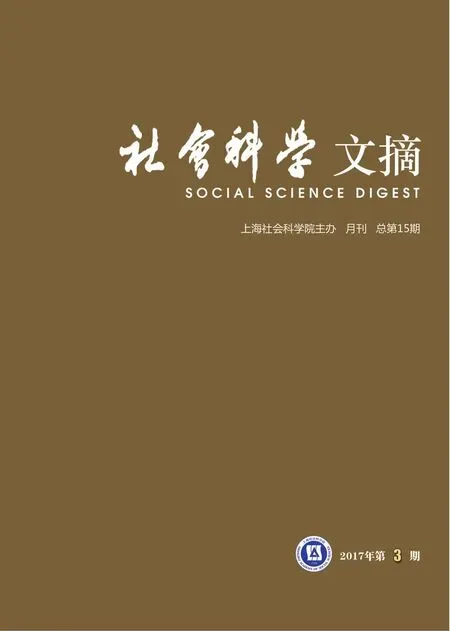18世紀英國奢侈消費大討論
文/李新寬
18世紀英國奢侈消費大討論
文/李新寬
隨著17世紀末英國消費社會的出現和形成,過去被視為奢侈的商品和服務越來越多地進入中等階層的消費清單,甚至社會下層也通過各種渠道滲入到奢侈消費中來,奢侈消費日益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社會現象,成為“沒完沒了爭論的話題”,從而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兩種意見的交鋒在17世紀后期至18世紀引發了一場有幾百位作者參與的奢侈消費大討論。
奢侈消費大討論的內容
在西方思想史上,從古希臘開始奢侈一直就是重要的議題。從內容上看,英國奢侈消費大討論主要聚焦于以下四大主題。
奢侈的定義是這次大討論的核心主題之一。奢侈的定義之爭不僅是一個概念上的爭論,也是解讀這次大討論的鑰匙。因為奢侈的含義在17世紀中后期開始發生了重大轉變,這種轉變始于霍頓、尼古拉斯·巴本等人,但決定性的轉折點是曼德維爾。這一重大轉變的關鍵之處在于將奢侈的定義與道德脫鉤,與經濟發展掛鉤。轉變是從思想觀念的突破開始的,霍頓列舉了一系列當時被視為奢侈品的進口商品對英國的好處,認為如果摧毀了這些貿易,抵制高水平生活,英國人就會淪落為“農夫和酒鬼,倫敦城很快就會成為愛爾蘭棚屋”。約翰·比爾在雜志上看到霍頓公開宣稱奢侈的惡習可以使英國變得富裕的觀點后嚇壞了,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他捍衛傳統道德,并公開反駁霍頓,要求霍頓給予回應。圍繞奢侈的爭論很快擴展到當時的知識圈中。曼德維爾將討論推向了高峰,他將奢侈寬泛地定義為“一切并不直接滿足人的生存需要的東西”,直截了當地挑戰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限,公開反駁所有對奢侈的指控,認為奢侈是一項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夠滿足人們追求快樂的心理需要,人們沉溺于奢侈品能夠推動商業的擴展和窮人的就業。曼德維爾“對奢侈定義的挑戰設定了隨后討論的框架,更有意義的是,他將奢侈和貿易的結合開啟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對商業擴展和商業社會的討論”。曼德維爾的激進觀點雖然引發了軒然大波,但也為大討論起到了消毒的作用。之后,大衛·休謨、詹姆士·斯圖爾特能夠從容客觀地重新定義奢侈,將其視為社會進步的力量。從此,從促進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待奢侈消費問題逐漸成為思想界的共識。
大討論的另一個主題是奢侈與道德的關系。雖然正統派認為奢侈敗壞了傳統道德,但在近代早期包括一些重商主義思想流派在內的思想家都旗幟鮮明地支持奢侈的去道德化。但是保羅·斯萊克指出,對奢侈和消費者欲望極度放縱的道德反擊曾在17世紀90年代獲得了一致的支持,形成了道德改革的同盟,從而引發了奢侈消費道德問題的激烈爭論。詹姆士·惠斯頓就抨擊“懶惰、奢侈、淫逸、瀆神、自然神論”以及“宗教、美德和公眾正義的衰敗”導致了自古到今“帝國、王國、國家的所有革命”。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中對“傲慢的道德家”的道德拷問提出了強烈質疑,認為眾多“蜜蜂”的生活“實在是奢華安逸”,但私人的惡德引致的是公眾的利益,“眾多蜜蜂當中的最劣者,對公眾的共同福祉貢獻良多”。由于不少道德家也參與到當時的商業活動中,這樣他們就采取了一個論戰策略,就是承認奢侈是一種罪惡,但同時認為這是商業社會中實現富裕的道德代價。在切身利益面前,道德改革同盟很快瓦解,從而為理性看待奢侈與道德的關系提供了土壤。
奢侈消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也是大討論的核心主題之一。W.D.史密斯認為,“討論的基本問題是奢侈作為一宗罪或稀缺資源的一項消耗,是否應該由國家禁令限制,或者作為一種擴張的經濟力量,是否應該不管其道德含意給予支持甚至鼓勵”。尼爾·麥克肯德里克指出,17世紀之初的思想家還沒有認識到奢侈消費的益處,把奢侈視為異國情調,因而對貿易平衡有害。到17世紀晚期,英國的思想家開始從經濟方面而不是道德方面來思考奢侈問題。阿普爾比指出,“人類作為一種消費動物,具有永無止境的欲望,能夠驅動經濟達到繁榮的新水準,這一思想在17世紀90年代的經濟作品中出現”。巴本就指出,“揮霍是一種對人有損害而不是對貿易有損害的罪惡”,因為“最能促進貿易的支出,是花在穿和住、花在裝飾身體和房屋上的支出”。從曼德維爾開始,奢侈消費更是逐漸被看作是一種經濟優勢,能夠促進窮人就業,刺激工業發展,鼓勵工匠改進工藝。
在古希臘、古羅馬和中世紀的觀念中,奢侈損害身體健康,造成精神墮落、狂躁、懦弱,使得男人變得女里女氣。這一問題在大討論中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喬治·切恩就認為,隨著整個國家變得更奢侈、富有、揮霍,疾病就成倍增長。巴本則從另一個角度來闡述這個問題:“精神需求是無限的,人天生就有渴望,當他精神振奮的時候,他的感官就更為精致,更有能力獲得快樂。當他的渴求增大,他的需求伴隨著他的愿望一起增加,這些對稀有東西的愿望能夠滿足他的感官,裝飾他的身體,促進生活的舒適、愉悅和奢華。”曼德維爾對奢侈損害健康的指控進行了駁斥,認為“追求感官享樂者亦像任何人一樣悉心在意自己的身體”,“潔凈的亞麻布和法蘭絨同樣使人虛弱。錦緞墻圍、精美油畫或華麗墻板,并不比不加裝飾的四壁更有益健康”。
這次大討論加深了當時社會對奢侈問題的認識,達成的最大共識是奢侈消費可以促進經濟發展。
奢侈消費大討論的原因
奢侈成風在當時英國社會引發了多方面的焦慮和擔憂,同時隨著“新奢侈品”的生產擴展,也要求重新認識奢侈消費的經濟意義,這些正是這次大討論的原因所在。
原因之一是隨著奢侈消費的流行,當時一些思想家擔憂奢侈消費破壞了禁奢法所要維護的社會秩序。一些道德家擔心新的消費模式削弱社會等級至關重要的視覺標記,比如,一些人擔憂無法將女仆和女主人區分開來,因為她們的服裝太像了。英國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出臺了一系列禁奢法,規定了不同等級的飲食和服裝,來“限制奢侈和炫目的消費”,以維護原有的社會等級秩序。但到了17世紀中后期,“已經影響了社會中上層的奢侈會快速擴散到社會下層的擔憂已成老生常談”。特別是到了18世紀,英國奢侈消費下移,被阿瑟·揚稱為“普遍”奢侈,外國評論家稱之為“英國國民根深蒂固的奢侈習慣”,對此極為震驚。時尚成風的結果就是突破了原有的社會等級限制,“當貴族都仿效王公的富麗堂皇,紳士都渴望貴族的得體莊嚴,商人走出柜臺占據了紳士的空位,混亂不止于此,直到社會最底層,他們也渴望超越屬于他們的層次”。當時人們已經注意到了追求奢侈的消費模式,特別是在消費面前等級秩序和公共習俗完全被打亂,自然會引發爭論。
原因之二是一些道德家對當時奢侈消費會敗壞傳統道德充滿了焦慮。奢侈被視為“瘟疫”,“社會所有階層都卷入到肆無忌憚的享樂追求的爭議之中,窮人和富人一樣都因為酷愛飲酒、沉迷賭博、輕裘肥馬、花心濫交而受到嚴厲批評。”曼德維爾將奢侈視為美德的觀點更是引發了道德家的憤慨。“今天鮮有人讀曼德維爾,但在18世紀,即使是他把‘馬蜂窩’直接倒在有教養的英國布道壇上和書齋里,也幾乎不會比他著名的對英國社會的昆蟲寓言有更大的影響了。”愛德華·亨德特也指出,“曼德維爾在整個18世紀極為聲名狼藉,但并不是因為任何深埋在《蜜蜂的寓言》的對話和討論文章中假定的經濟學說。相反,是因為他宣稱基督教道德在心理學上是行不通的,源于基督教的道德哲學傳統服務于意識形態和社會交往目的,使得人類欲望的利己主義根源隱藏在了思想的背后”。曼德維爾對奢侈的辯護和全新的道德觀成為眾矢之的,成為道德家瘋狂攻擊的標靶。
原因之三是一些重商主義作家仍固守傳統立場,擔心大量進口奢侈品會破壞貿易平衡,因而與看到奢侈消費與經濟發展、人民富裕正向關系的經濟思想家產生了思想沖突,從而引發了討論。阿普爾比指出,雖然在17世紀90年代構建新經濟理論的材料已經出現,但舊有的貿易平衡套話一直到18世紀仍頑強地存在著。但早在17世紀70年代,一些作家開始把經濟增長假定為不斷擴展的需求的動態結果。巴本就認為,“時尚和服飾的改變是貿易的偉大促進者,因為它在舊衣穿破之前,就引起衣物的消費”。巴本批駁了當時英國人的一個錯誤觀念,那就是英國人如果不買外國奢侈品,就會消費本國的商品,指出“不是身體的需要引致消費,很少的東西就能滿足人體的自然需求。引起貿易的是精神的需求、時尚、對新奇物品和稀有事物的熱望”。
原因之四是隨著海外貿易的繁榮,過去被視為奢侈品的商品現在成為普通日用品,再加上針對新消費群體而開發生產的“新奢侈品”種類繁多,規模大增,都要求重新界定奢侈品的定義和認識奢侈消費的經濟意義。隨著進口奢侈品數量增大,價格下跌,它們逐漸成為普通人也能消費得起的商品,1719年什魯斯伯里的一家雜貨店就出售許多過去是奢侈品的商品。正如安格斯·麥克因尼斯所言,奢侈像一塊色斑一樣滲透到了層層的商店。所謂“新奢侈品”是指新發明的,比過去的奢侈品更接近于中產階級,但仍然昂貴的高質量產品。這些新奢侈品又被稱為“現代奢侈品”,主要是滿足以中等階層為主體的消費人群的不斷膨脹的消費需求。這些新奢侈品“是新奇、時尚和獨創的奢侈品”,具有“快樂、舒適和便利、實用、令人愜意”等特點,遵循品味和美學原則,英國制造商通過模仿進口奢侈品和工藝革新,創造出了“現代奢侈品”,從而擴展了奢侈品的種類,使參與大討論的英國作者對奢侈品的定義不斷變化,特別是面對外國商品的激烈競爭,推動本國新消費品生產的需求也促使他們重新思考奢侈消費的經濟意義。
奢侈消費大討論的經濟和社會后果
第一,通過大討論逐步擺脫了消費的道德意識形態困擾,促進了英國人消費觀念的轉變,使得消費形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推動英國在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中期左右誕生了消費社會。
在近代,道德的基礎性理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再加上在大商業時代,即使是道德改革的鼓吹家本身也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中,分享了經濟發展的好處,這是大討論能夠逐漸擺脫道德意識形態的根本原因所在。奢侈與道德的脫鉤并不意味著奢侈作為進步社會力量的倡導者在18世紀就能輕易取得優勢,批評者仍持續不斷地挑戰他們的觀點。但奢侈消費的激烈辯論的后果就是社會輿論能夠理性平和地看待奢侈問題,消除了日常消費中的意識形態限制。人們也認識到了奢侈消費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財富增長,他們看到“哪里變得越富有,哪里的消費就越龐大”。再加上本國生產的“新奢侈品”大量涌現,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了英國人的消費觀念,導致“英國的普通男女擁有比以前吃穿范圍更廣的商品”。而且“所有階層的生活方式和人們的條件都令人稱奇地改變了”。
第二,大討論促使英國人重新思考本國生產的消費品特點,使他們認識到,英國人必須也能夠生產出與眾不同的奢侈品和新的消費品來滿足急劇增長的社會多樣化的需求,從而促進了消費品設計和生產的創新,成為工業化的動力。
在大討論過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論取代了“貧窮效用”理論,逐步承認在所有社會等級中生活舒適和便利同生活必需品一樣有益,能夠對工業形成強有力的促進。新風氣促使進口商和制造商意識到,這為產品革新和時尚與設計的變化提供了大量的商業機會。英國制造商受東方奢侈品啟發,充分借鑒其設計、多樣性和美學特性,實踐了大討論過程中反復提到的一個核心概念“模仿”,再結合消費者的品味和時尚,進行產品創新和工藝革新,終于成功開發出本國生產的“新奢侈品”或者說“新消費品”。“這些新商品并不是以前國產產品的簡單替代品,他們是用與眾不同的材料和風格做成的特殊物品,供個人與家庭裝飾之用,他們通常能夠喚起異國情調。”這些新商品以“能買得起的價格滿足了中產階級和鄉紳消費者要求的優雅品味”。正是這些產品創新和工藝革新促進了制造業的增長和生產力的變遷,馬克辛·伯格認為:“博爾頓和瓦特的蒸汽機長期以來被18世紀史家看作是發明和創造的關鍵指示器,但是18世紀本身值得驕傲的地方是從鍍銀的咖啡壺到刻紋的黃銅器皿和上漆的紙型托盤等全新精細消費品的爆發。”這些消費品不但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而且成為英國占領世界市場的利器。
第三,在大討論過程中,奢侈成為18世紀政治經濟學的主題之一,與此同時,為了避開奢侈的爭議,當時人使用了“舒適”“品味”“幸福”“優雅”“體面”等詞匯來描繪和界定日益豐富的物質生活,從而極大地豐富了經濟和社會理論,不斷刷新人們對所能達致的理想生活狀態的期望,從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從曼德維爾之后,奢侈就不再是道德哲學討論的主題,而成為政治經濟學的主題,成為范圍寬廣的商業討論的一部分,成為休謨、斯圖爾特、斯密討論的主題,并且完全與商業、便利和消費聯系在一起。由于奢侈一詞從古以來就具有道德的涵義,所以當時的政治經濟學家為了避免陷入爭議,使用“舒適”等一系列詞匯來替代奢侈一詞。麥克里·奧迪爾-伯尼茲指出:“使用舒適一詞指代18世紀取得的物質幸福,表示物質享受和生活舒適,它為18世紀經濟理論提供了一個替代奢侈的詞匯。” “品味”是界定奢侈的關鍵詞匯之一,哈奇森、休謨、艾莉森都對品味進行了系統闡述。“幸福”是另一個替代詞匯,據保羅·斯萊克考證,國民幸福在18世紀得到不斷的共鳴。隨著文化消費的擴大,“優雅”也成為奢侈的代名詞之一。波考克指出:“優雅和斯文的概念是18世紀商業意識形態中的關鍵因素。”按照《牛津英語詞典》在18世紀的定義,體面是指“品行端方的立場,以及與此相適應的道德品質。因此在后來的應用中,指不提社會地位,或者盡管身處簡陋的環境中,所具有的誠實和得體的性格和行為”。這一系列與奢侈具有內在聯系的詞匯的使用和探討,極大地拓展了對奢侈的理解,豐富了當時的經濟和社會理論,推動人們不斷改善現有的社會狀況,追求更為理想完善的社會生活。
這場大討論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奢侈品的定義和概念,不再從道德角度來看奢侈消費的問題,而是從商業經濟角度出發,開始關注中等階層甚至勞工等廣大人群的消費動機和消費實踐。隨著英國奢侈品生產不斷推陳出新,過去被視為奢侈品的商品現在成為日常用品,人們可消費的商品種類也隨之越來越豐富,極大地提升了人們的生活質量。
(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教授;摘自《世界歷史》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