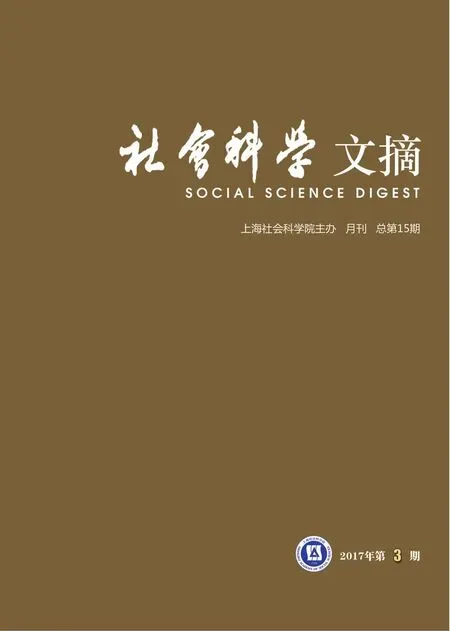收入不平等的公眾感知與態度
——國際比較視野下的中國
文/方長春
收入不平等的公眾感知與態度
——國際比較視野下的中國
文/方長春
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得以快速發展的同時,收入不平等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有關中國社會不平等相關議題也早已成為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但是,對民眾對社會不平等的“主觀”認知與評價等議題卻缺乏有效討論。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而言,關注人們對收入不平等的感受和態度與關注事實的收入不平等一樣重要。這是因為,不平等的增加會導致社會信任的下降,進而導致社會凝聚力的下降,影響到社會的整合。截至目前,針對公眾對收入不平等的認知與態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西方市場化國家。盡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一些研究涉及到社會主義轉型國家的相關問題,但針對中國的研究則非常少見。在本研究中,我們采用國際比較的方式來認識中國公眾對收入不平等的感知與態度,特別是將中國的情形與同樣經歷市場轉型的前社會主義國家比較。
文獻回顧與課題的明確化
以往的研究主要從個體層面和國家兩個層面來分析收入不平等感知與態度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從個體層面而言,其一,人們的認知與態度被看作是受制于社會現實的,因此,人們對不平等的認知和態度也被看作或多或少是其生活于其中的現實社會的不平等的一種反應;其二,個體在社會事實中的生活體驗也會影響到人們對收入不平等的看法和態度,譬如,人們的社會流動經歷和人們對社會流動機會的認知都會影響到人們對收入不平等的態度;其三,人們自身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也會影響到人們的社會態度,自身的社會與經濟狀況越好,人們越傾向于對收入不平等持更寬容的態度,而那些處于弱勢地位者則更傾向于持有平均主義的經濟觀念;其四,很多經驗研究則表明,人們對收入不平等的態度受到人們對收入不平等感知的影響,即人們對不平的容忍程度(legitimate inequality)受到人們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perceived inequality)的影響,人們感知的收入不平等越高,則對收入不平等容忍程度越高。
從國家層面而言,首先,一個國家的主流價值觀念通常被用來解釋不同國家人們對收入不平等的態度的差異。例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強調平等被看作主流價值觀中的主要成分,而在西方資本國家中,譬如美國,機會均等和個人自由被看作是主流價值觀中的主要成分。因此有研究指出,美國人更多地將收入不平等歸因于個體因素而不是結構性因素。其次,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也被用來分析不同國家人們對收入不平等態度的差異。有研究指出,經濟發展程度有助于增加人們對不平等的容忍度,這是因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增加了人們經濟上的安全感,減弱了人們對經濟議題的關注。最后,有關市場轉型國家人們對不平等的態度,現有的研究得出來互不相同的、甚至相反的結論。其中一種觀點認為,由于前社會主義時期對平等的強烈強調,使得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對收入不平等持有更多的批判態度,并繼續持有平等主義的觀念。另外一種觀點則與此正好相反,認為隨著市場化的轉型,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對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會隨之增加,這是因為,市場轉型國家在轉型過程中,事實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增加,因此人們對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也隨之增加。
本文關注的重點是通過與其他市場轉型國家比較來分析中國公眾對收入不平等的感知與態度。根據前述有關個體和國家層面的討論,我們試圖回答以下問題:
(1)市場轉型國家的公眾對三類精英(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技術精英)的相對收入優勢的感知是否不同于傳統的市場化國家?中國公眾對三類精英的相對收入優勢的感知與市場轉型國家是否一致?(2)市場轉型國家的公眾對三類精英的相對收入優勢的容忍程度是否不同于傳統的市場化國家?中國公眾對對三類精英的相對收入優勢的容忍程度與市場轉型國家是否一致?(3) 市場轉型國家公眾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容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否不同于傳統的市場化國家?中國公眾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感知與容忍度是否與市場轉型國家表現出一致性?(4) 感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否影響到人們對收入不平等容忍度,這一因素的作用在市場轉型國家和傳統的市場化國家中的作用有何不同?對中國公眾的收入不平等容忍度又有何影響?(5)結構位置因素,或者說自利性原則的作用在不同市場轉型國家和非市場轉型國家中有何不同?對中國公眾的收入不平等容忍度又有何影響?(6)根據自利性原則,在轉型國家中的國有部門工作者是否傾向于包容收入不平等?中國公眾是否也表現出這一特征?(7)教育的啟蒙作用是否體現于市場轉型國家當中?中國的情形又如何?(8)性別和年齡因素如何影響人們對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市場轉型國家和非市場轉型國家有何不同?中國的情形又如何?
數據與核心變量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國際社會調查項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簡稱ISSP )2009年的調查數據(ISSP2009)。為了比較分析,我們選擇了中國和其他4個市場轉型國家(匈牙利、波蘭、俄羅斯、斯洛伐克)的樣本,同時也選擇了4個傳統的市場化國家(丹麥、西班牙、英國、美國)作為比照對象,其中選擇美國和英國作為市場化國家中不平等程度最為突出的代表,而選擇丹麥和西班牙作為市場化國家中平等程度最突出的代表。
本文核心的變量是人們對收入不平等的感知和態度。在ISSP的調查過程中,被訪者被問到一些職業位置的實際和應得收入,例如:“在您看來醫生/企業高層管理人員/銷售人員/政府的高級雇員/體力工人的實際收入是多少?”“在您看來醫生/企業高層管理人員/銷售人員/政府的高級雇員/體力工人應該得到的收入是多少?”其中被問到的職業位置是按照這些職業位置在職業結構等級中的位置進行選擇的,其中一些職業位置作為高職位(high status occupation)的代表,另一些職業位置作為低職位(low status occupation)的代表,通過比較人們對高職位者和低職位者收入不同的看法和態度,就可以了解人們對收入不平等的看法和態度。在本研究中我們依據ISSP的現有測量,從兩個層面來構建我們的核心變量。首先,我們分別以人們所認為的體力工人的實際收入和應得收入作為基數,以人們所認為的其他職位的實際收入和應得收入分別除以體力工人實際和應得收入,計算各職位相對于作為低社會位置(low status)代表的體力工人的收入優勢,按照ISSP的研究設計,我們以醫生作為技術精英的代表,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作為經濟精英的代表,政府高級雇員作為政治精英的代表,計算方法公式1和公式2所示:
其次,參考國際上的一些常見做法,我們按照以下方式對感知的不平等(perceived inequality)和認可的不平等(legitimate inequality)進行了度量:
結果與分析
在經驗分析當中,我們首先比較了不同國家公眾感知和認可的高、低職位的收入比。
就感知的不平等而言,分析結果(統計表格略)表明,在市場轉型國家中,人們感知到的收入優勢群體是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和政府高級雇員,并且他們的收入優勢普遍高于傳統的市場化國家的同類群體。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公眾感知到的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和政府高級雇員的收入分別是體力工人的11.75倍和10.21倍。也就是說對市場轉型國家而言,人們所能感受到的是這兩類精英的收入優勢是非常突出的。
就人們認可的收入不平等而言,市場轉型國家的公眾所能認可的經濟精英的收入相對于體力工人收入倍數,大多與傳統的市場轉型國家接近,但相對于那些高福利性質的、強調收入平等的歐洲國家(如丹麥和西班牙)而言,市場轉型國家公眾認可的經濟精英的收入優勢要高得多。就公眾所認可的政府高級雇員的收入相對于體力工人收入的倍數而言,中國和俄羅斯最為突出,分別為5.25和5.27。總體來看,市場轉型國家的公眾所感知到的政治精英的收入優勢遠遠高于傳統的市場化國家,而這些國家的公眾所能容忍的政治精英的收入優勢也普遍高于傳統的市場化國家。如果把中國和俄羅斯看作是市場轉型過程中的不完全轉型國家的代表的話,那么在不完全轉型國家中,公眾所能容忍的政治精英的收入優勢最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于市場轉型國家中的中國、俄羅斯、斯洛伐克而言,公眾感知到的作為技術精英代表的醫生的收入相對于體力工人的收入的倍數并不是很高,分別只為2.07、1.68和2.75,遠遠低于英國和美國,后兩個國家的這一比例分別為5.32和6.71,甚至低于歐洲收入最為平等的丹麥,丹麥這一比例為3.43。與此同時,市場轉型國家的公眾所能認可的作為技術精英代表的醫生相對于作為低職位代表的體力工人的收入的倍數也普遍低于傳統的市場化國家,俄羅斯的這一比例為1.64,而中國的這一比例最低,只有1.47。這或許意味著,公眾并沒有意識到所謂的技術精英實際和應該獲取更高比例的收入。
那么,什么樣的因素影響到了人們對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呢?
首先,人們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對人們的對收入不平等容忍度的影響普遍存在于所有國家當中,即人們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人們對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也相應地越高。而本研究的結果表明,這一結論同樣適用于市場轉型過程中的中國。
其次,就結構位置,或者說自利性原則的影響而言,分析結果(圖表略)表明,作為結構位置度量的國際標準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對人們的收入不平等容忍度的影響在幾乎所有國家(包括市場轉型國家和傳統的市場化國家)的模型中的均具有統計學意義,唯獨中國是個例外。作為家庭經濟狀況度量的家庭人均收入的自然對數,對收入不平等容忍度的影響也表現出類似的特征,在多數國家中家庭經濟狀況可以按照自利性原則來解釋其對人們的收入不平等容忍度的影響,即家庭經濟狀況越好,則人們對收入不平等越傾向于持寬容的態度,但中國同樣是個例外。只有作為結構位置或者說自利性原則的度量的另一指標“在國有部門工作”對人們的不平等容忍卻有著一定的影響。對于部分市場轉型國家而言,由于制度慣性的作用,國有部門在轉型過程中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續,從分析中可以看出,作為市場轉型國家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那些處在國有部門者對不平等容忍度要高一些,在中國也有類似的情形(只是顯著性水平略低),而在傳統的市場化國家,“在國有部門工作”這一變量對人們的收入不平等容忍度的作用普遍沒有統計學意義,或者情形正好相反(如丹麥)。
再次,就教育的影響而言,分析結果顯示,在作為市場轉型國家的波蘭和斯洛伐克,教育體現的是自利性原則,即教育程度越高,對收入不平等越寬容,而在中國接受高等教育者對收入不平等的寬容度反而是下降的,俄羅斯的模型中,高等教育這一變量對收入不平等容忍度的影響盡管沒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但在作用的方向上也與中國類似。
最后,就性別和年齡這兩個變量對人們的不平等容忍度的影響而言,在一些國家當中(如丹麥、匈牙利、美國模型中的性別變量,波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模型中的年齡)體現的也是自利性原則,但在中國,年齡對人們的不平等容忍度是負向的,即年齡越大越趨向于不能容忍收入不平等,這或許與轉型之前的平等主義傳統有關。
總結與討論
國際比較結果表明,就中國公眾對收入不平等看法與態度而言,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公眾所感知到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低于多數市場轉型國家,但人們所能容忍的收入不平等卻高于多數市場轉型國家,并且與其他市場轉型國家和傳統的市場化國家一樣,人們所能容忍的收入不平等隨著人們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這一研究發現或許可用以解釋中國事實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與社會穩定的關系,也就是說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中國事實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非常突出,但并沒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社會的穩定。與此同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公眾對收入不平等的態度并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們自身社會位置的影響(除了體制位置——“是否在國有部門工作”有著微弱的影響之外),這是否意味著不同社會位置的人們對社會不平等持有比較一致的態度呢?如果這一觀點成立的話,那么這是否又進一步意味著,人們對收入不平等滿意或不滿意不僅僅是不同的具體社會位置的相對利益差異所導致的,而是由超越不同的具體社會位置的其他的結構性或制度性因素所導致的呢?本文的分析還表明,對中國的樣本而言,高等教育體現的不是自利性原則,而是表現出啟蒙意義,這是否也意味著前述超越具體的社會位置差異的其他因素的存在呢?
此外,盡管中國公眾與其他市場轉型國家的公眾一樣感知到的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的相對收入優勢非常突出,并且中國公眾所能容忍的經濟精英的相對收入優勢與其他市場轉型或傳統的市場化國家并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差異,但與其他市場轉型國家和傳統的市場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與“不完全市場轉型”國家俄羅斯一樣,公眾所能容忍的政治精英的相對收入優勢最為突出。這至少說明,中國公眾更加許可政治精英相對收入優勢,這或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在社會流動中大多數人認為理想的社會位置是存在于那些權力結構的優勢位置當中。相比較而言,中國的公眾跟其他市場轉型國家的公眾一樣,感知和認可的技術精英的收入優勢都要低得多。如果說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社會位置差異更多地受到經濟和技術理性的影響,從中國公眾對技術精英收入優勢的態度中或許可以看出,所謂經濟和技術理性對合理的收入差異形成的影響并不充分。
社會態度隱含著社會行為傾向性,特別是隱含著對合理社會行為的傾向性。對中國公眾的收入不平等感知和態度的把握,不僅有助于解釋事實的收入不平等可能以及不可能的社會后果,也有助于解釋在事實的社會差異的形成過程人們所認為或可能采用的所謂的理性化行為。
(作者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摘自《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年第1期;原題為《收入不平等的公眾感知與態度:國際比較視野下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