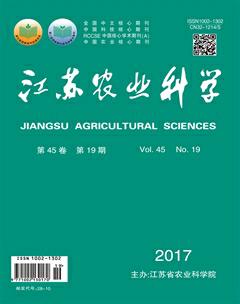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及優化機制
曹玲玲 姜麗麗 劉彬斌
摘要:江蘇省農業供需結構失衡、資源環境惡化、經營效率難以提升、區域發展極其不平衡嚴重限制了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可持續發展。為追本溯源,基于農戶主體特征、農業供給主體能力、農產品創造能力及競爭能力、農村自然稟賦及生態環境、農業信息和現代化、農村金融服務能力以及相關制度保障7個維度構建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結合模糊綜合評價的方法,在對指標體系賦權的基礎上,有效地測度江蘇省13個省轄市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對比分析結果發現,蘇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效用明顯優于蘇中、蘇北地區,而蘇中、蘇北的改革效用速度大幅度提升。7個要素中只有農產品創造能力及競爭能力、農村金融服務能力2個要素相對出現下滑,其他5大要素都得到了長足發展。蘇北的農產品創造能力及競爭能力、農戶主體特征、農業供給主體能力3個方面優于蘇南和蘇中城市,蘇南的農村金融服務、農村相關制度保障遙遙領先。鑒于此,有效推動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完善農業現代化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和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產業附加值;深化農業信貸和農業風險分擔機制的改革,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效率;實現農業資源協調發展、優勢互補,縮小蘇南與蘇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的差異。
關鍵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區域差異;效用評價;模糊綜合評價;可持續發展;江蘇省
中圖分類號: F323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19-0103-05
收稿日期:2017-08-25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編號:15YJC790082);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編號:2016SJD790049、2015SJD804);江蘇省社科應用研究精品工程課題(編號:17SYC-070);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編號:2017ZDIXM168);宿遷學院科研基金重點項目(編號:2015KY03)。
作者簡介:曹玲玲(1983—),女,河北衡水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為農村金融與統計分析。E-mail:lingling.cao@163.com。 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凸顯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家戰略地位,這是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和2015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調整在農業這一領域的有效貫徹,更是2004年以來連續14年聚焦“三農”的跨時代之舉,對改善農村供給結構、提升農業供給效率具有現實意義。2017中央一號文件《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指出,今后的農業工作主線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2016年中國農業經濟學會2016年會在蘇州市成功舉辦,肯定了我國當前關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的顯著成效,重點對江蘇省農業供給側改革攻堅的成果與阻礙提出了建設性意見[2]。
江蘇省作為我國的一個農業大省,在農業現代化建設、確保農副產品的有效供給以及提升農民福祉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同時也要看到,江蘇省的農業發展中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1)2016年江蘇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為95 394元,位居全國第4位,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達17 606元,標志著江蘇省正式跨入高等收入階段,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迫在眉睫,中高端農副產品有效供給匱乏;(2)自2011年以來,江蘇省農業生產總體效率逐年下降,農戶凈收入中來自二、三產業的比重連年下滑,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以及農業生產經營效率的提升成為當前政府的重中之重;(3)江蘇省資源環境壓力難以應對農業供給側的改革,人均耕地面積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生態環境惡性透支嚴重,致使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持續性備受質疑;(4)江蘇省農業現代化水平雖居全國前列,但蘇南、蘇中以及蘇北的差異始終成為區域協調發展最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因此,本文通過對江蘇省13個地級市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用進行綜合評價,在此基礎上提出更具針對性的優化改革意見。
1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文獻述評
農業供給側結構問題主要是農產品供給與市場有效需求在數量、比例和品種等方面出現了不匹配[3]。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引致眾多學者展開研究,但主要是圍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障礙、影響要素及其完善建議的分析。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障礙分析方面,吳海峰指出農產品質量難以滿足市場需求造成市場供需失衡[4]。陳錫文闡述了糧食品種供需矛盾的日益顯現、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國際競爭力低造成結構失衡[5]。江維國基于農產品視角,明確了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嚴重不足加之高庫存的雪上加霜才是造成農業供給側結構問題的重要原因[6]。沈貴銀闡述了農產品供給結構與消費結構的不匹配、區域農業發展的失衡、農業經營效率不完備以及農村生態環境的惡化是造成農業發展停滯不前的原因所在[7]。黃祖輝等基于制度角度對農業供給側結構進行了相關論證[8]。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影響要素和完善建議分析方面,國外相關專家學者認為,農業激勵與補償政策、農村生態環境、地理條件、自然稟賦、農村技術變遷、勞動力資本、相關體制變更以及全球經濟的蔓延等是影響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的主要因素[9-11]。然而國內的相關專家學者認為,新型農戶的培育和農業技術的改進[1]、城鎮化的推進和產業結構的優化[3,12]、生態資源環境的有效利用、農村經營效率的提升[7]、農業轉型升級、農業科技創新[13]、高品質產品生產能力、農業信息和研發技術、農村資金融通功能[14]等是影響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的主要因素。
綜上所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提出以來已引致大量專家學者進行研究,疏理形成了基本完備的影響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素體系。然而,大多數學者還停留在理論分析層面,實地調研與實證分析的研究較為少見。針對全國及具體某些區域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的研究還未有專家學者介入,鑒于此,本文在梳理影響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素的基礎上,采用綜合評價方法對江蘇省13個地級市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進行區域分析和序列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針對江蘇省的具體實踐,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進措施。endprint
2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從根本上對傳統農業經營模式及農業經營主體進行突破式創新,不斷整合農村各種可利用資源,掌控市場有效需求,從供給端著手改革創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得以持續性發力必須依托于多方聯動的網絡動態性合作模式,即需要對農產品形成及效率、各要素供給安排以及相關制度政策有機結合[8]。由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影響要素眾多,加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是一個綜合性問題,單一指標或參數均不具有代表性,本文通過專家意見,構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指標體系(表1),重點剖析江蘇省各地區農業供給側改革效用的差異。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是各地區農業各要素有效配置能力的體現,而與農業生產相關的核心要素由農戶主體特征、農業供給主體能力、農產品創造能力及競爭能力、農村自然稟賦及生態環境、農業信息和現代化、農村金融服務能力以及相關制度保障等7個方面組成。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導力量和主要抓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不斷擴大,對促進農村就業、提升農民收入和農業生產效率具有顯著作用。大力發展農村電商是壯大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是擴展農村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有效手段,有利于線上線下互動良性發展,有利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在于農戶是否增收,因此在農戶主體特征方面,選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數量、農村電商示范村以及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3個指標。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種類繁雜眾多,特此只選擇2個代表性群體,即省級農業合作社示范社和省級示范家庭農場。農業供給主體能力主要選取糧食種植面積以及農林牧漁業總產值2個指標。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根本上需要對農村的供給進行調整,使之與高端的市場需求相匹配,因此農產品供給的質量、品牌以及市場競爭力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之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重點分析高端產品創造能力及市場競爭力,主要包含農產品出口額、農產品地理標志商標數量以及產品抽檢質量合格率等3個方面。
江蘇省農業發展中面臨水資源環境污染、土地退化等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給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以及綠色食品的需求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農業產業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農村土地流轉受農業生產基礎條件、地形地貌等自然資源稟賦特征影響,同時農地流轉對農業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發展起到了遏制作用[15]。因此在研究農村自然稟賦及生態環境時,選取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旱澇保收率以及污染治理項目投資額等3個指標。農業的信息化及現代化水平對實現農業規模經濟至關重要,也是當前政府等相關職能部門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著力點。農業信息和現代化水平選取農村居民家庭計算機擁有量、農業機械總動力2個指標來衡量。
加速推進農村金融全方位創新,有效激活農村金融服務鏈條,為農業全面轉型升級提供重要的資金支撐,有效形成補齊農業現代化短板與金融轉型升級穩健經營的雙贏局面,是確保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順利推進的關鍵路徑。農村金融服務能力主要包含農業生產擴展的有效資金供給以及農業損失的資金補償,因此采用農業財產保險支出和支農貸款用于衡量農村的金融服務能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需要農業各方主體及金融機構的參與,更需要政府的相關政策保駕護航。
3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綜合評價
3.1 研究方法
模糊層次分析法(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FAHP),克服了層次分析法的缺點,并引入了模糊數學的思想[16]。具體步驟如下:
首先,構建模糊判別矩陣。判別矩陣R的建立是針對上一層某因素,本層次與之相關各因素之間重要程度的比較,采用0.1~0.9標度得到判別矩陣。
式中:判別矩陣R中變量rij表示因素ai和因素aj相對于上一層因素比較時,ai和aj具有模糊關系的隸屬度,且滿足rij=1-rji。
其次,檢驗判別矩陣的一致性。在實際經濟問題中,各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錯綜復雜,往往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加之FAHP方法主觀性較強,判別矩陣的一致性往往得不到滿足,因此需要對判別矩陣進行調整,調整好的隸屬度滿足下列等式。
在對上述模糊判別矩陣一致性處理后,整理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指標體系中各指標的權重(表1)。
3.3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分析
3.3.1 數據來源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的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江蘇省統計年鑒》《江蘇省農村統計年鑒》以及13個市的農村統計年鑒、各級政府網站的統計資料、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
3.3.2 數據的標準化處理 對選取的17個指標進行歸一化及去量綱化處理,為保證綜合評價的可比性,所有指標都須轉化為正指標計算,同時為保證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在去量綱化處理時,確保所有變量取值介于0~1之間,特此采用改進的功效系數法計算公式:
dij=x′ij-x(s)jx(h)j-x(s)j×α+(1-α)。(4)
式中:x(s)j為同類指標中的不滿意值;x(h)j為同類指標中的最滿意值;α的取值范圍為(0,1)。變換之后指標值dij取值介于0~1之間,α的取值由評價者自定。由于dij關于α的一階導數小于0,因此若想提高指標在評價中的權重,可適當降低α的取值。
3.3.3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測度結果分析 運用模糊綜合評價方法對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的指標體系進行加權測度,得出2014、2015年度江蘇省13個地區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的綜合得分以及7個維度的測評分。根據表2的測度結果,針對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的變動趨勢及空間差異分析如下:endprint
3.3.3.1 綜合測度分析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明顯提升,區域發展速度差異較大 從整體運行結果來看,2015年江蘇省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效用的平均測度值為0.389 5。2015年相對于2014年而言,江蘇省13個省轄市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效用基本得到明顯提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效用最優的3個地區分別為蘇州、無錫和南京,而綜合效用較差的3個地區為宿遷、揚州和鎮江,蘇州與宿遷綜合測度分相差近3倍,這也凸顯了江蘇省內部區域協調發展的弊病所在。從發展速度來看,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效用得分平均提升26.58%,全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效用增長速度較高的3個地區分別為宿遷(53.42%)、鹽城(46.84%)、徐州(39.93%);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效用增長最為緩慢的為蘇州,增長速度僅為5.94%。
3.3.3.2 七大要素貢獻度參差不齊,改善效用差異性較大 從要素貢獻程度來看,農產品創造及競爭能力、農村金融服務能力這2個要素都出現了下滑的現象,其他五大要素都得到了較好改善。在農產品創造及競爭能力方面,僅有徐州、常州、連云港、泰州以及宿遷出現了上漲,其他地區均出現了回落。主要原因在于蘇北地區農業資源豐沛,農產品特色品牌效用得以彰顯,而蘇中地區尤其是蘇南城鎮化水平較高,特色農副產品品牌效用可挖掘潛力不足。在農村金融服務能力方面,蘇中城市農村金融供給乏力現象較為嚴重,蘇南城市農村金融供給速度也較為緩慢,說明農業規模效應及品牌效應還未完全彰顯的情況下,農村金融機構支農的意愿較弱。
農戶主體特征、農業供給主體能力2個要素,蘇北、蘇中城市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蘇南城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隊伍的不斷壯大、糧食產量的穩步提升加之農副產品質量的有效改善,這也完全契合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在農村自然稟賦及生態環境要素方面,13個省轄市都出現了較穩速度的提升,生態環境得以有效改善。《江蘇新農村發展報告2016》中闡述,江蘇省在綠色江蘇建設、生態示范村建設、村莊環境整治以及完善生態保護制度等方面均躍居全國前列。同時,江蘇省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有效制定帶動了農業規模化經營及農產品質量的提升。在農業信息和現代化水平方面,蘇中平均測度水平值不足蘇南平均測度值的25%,蘇北平均測度水平為蘇南平均水平的40%左右。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依托于物質和技術支撐、農業產業體系鏈條完備以及3大產業融合發展等多方合力才得以促成,而蘇北和蘇中地區技術落后、農業產業鏈條不完備嚴重限制了該區域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在農村相關制度保障要素視角下,蘇北和蘇中地區的測度值也僅分別為蘇南平均測度值的44%、41%。
4 結論與優化機制
4.1 結論
第一,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系統性工程依托于多方聯動的網絡動態性合作模式,需要農戶主體特征、農業供給主體能力、農產品創造能力及競爭能力、農村自然稟賦及生態環境、農業信息和現代化、農村金融服務能力以及相關制度保障等7個維度協同發力。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的七大要素供給大體呈增長趨勢,確保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量”,而面臨消費結構的變遷、國際競爭力的擠壓,只有從“質”上提升才能堅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效并促進其可持續性發展,“質”的飛躍需要各要素資源配置結構的再調整。
第二,江蘇省的13個省轄市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均有了長足進步,蘇南地區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效用明顯優于蘇中、蘇北地區,然而蘇中和蘇北區域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效用提升的速度較快。江蘇省內部區域協調發展任重道遠。
第三,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評價的7個要素中,農產品創造能力及競爭能力、農村金融服務能力這2個要素相對出現了下滑,其他5大要素都得到了長足發展。蘇北地區的農業資源豐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大力培育、農副產品品牌效應的彰顯,使其2015年在農產品創造能力及競爭能力超越蘇南地區,農戶主體特征方面超越蘇中地區,農業供給主體能力方面全面趕超蘇中、蘇南地區。蘇北區域在農村金融服務、農村相關制度保障方面無法與蘇南相比,差距甚遠。
4.2 優化機制
4.2.4 完善農業現代化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和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產業附加值 現代化農業生產體系的完善依托于生產的技術能力、農產品標準化及品牌體系的建立,而關鍵在于提高生產的技術能力。加快發展農產品初級加工和精深加工,著力培育個性化食品、營養食品和功能食品。挖掘、壯大江蘇省食品老字號品牌企業,培育地方特色的江蘇省食品品牌,彰顯江蘇省地方文化及內涵。農業技術的改良與提高離不開科研經費的支撐,各級政府要確保承擔農業技術的科研開發經費充足,才能確保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以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積極培育、壯大江蘇省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隊伍建設,結合政府、地方高校等資源完善家庭農場、各類合作社等主體的培訓和職業教育機制,健全符合市場需求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準入機制,重點形成具有明顯區域性、競爭力及輻射能力強的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構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產業集群。農業產業體系的建設,需要3大產業的有效融合,打破原有的生產加工相分離的模式,結合當地的自然資源稟賦,融合信息化發展的新形式新常態,盡快形成生產、加工、貯藏、分銷等一體的產業鏈條。
4.2.2 深化農業信貸和農業風險分擔機制的改革,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效率 當前,江蘇省的農業發展邁入集約型、規模化經營,對資金的依賴程度日趨提高,農村金融服務能力的提升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功至關重要。然而,伴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眾多農業資金在利益驅使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渠道轉移到了城鎮及非農部門,造成江蘇省農業信貸和風險分擔機制完全不能應對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需求。進一步引導和加大政策性銀行在農村基建、城鎮化、農地流轉、公共服務事業等方面的資金支持力度;加強農村金融機構的創新力度,增強農地流轉的主動性,盡可能滿足不同需求的農地經營者的金融需求;農地抵押貸款、涉農集合債券、農業聯保貸款、農業保險等多種金融產品多措并舉;加快金融產品創新,提升直接融資在城鎮化建設中的比例,利用建設—經營—轉讓(build-operate-transfer,簡稱BOT)、移交—經營—移交(transfer-operate-transfer,簡稱TOT)、建設—擁有—經營(building-owning-operation,簡稱BOO)、建設—移交—運營(build-transfer-operate,簡稱BTO)等模式,充分實現政府、金融機構和私營企業的有機銜接。endprint
4.2.3 實現農業資源協調發展、優勢互補,縮小蘇南與蘇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用的差異 蘇北地區的農業資源豐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大力培育、農副產品品牌效應的彰顯,使其2015年在農產品創造及競爭能力超越蘇南地區,農戶主體特征方面超越蘇中地區,農業供給主體能力方面全面趕超蘇中、蘇南城市。而蘇南的農村金融服務、農村相關制度保障遠遠超過蘇北和蘇中的水平。鑒于此,江蘇省各市級政府應打破格局,放眼整個江蘇區域,實現優勢資源的有效輸送和對接。蘇北優勢的農業資源和現代化經營主體的壯大隊伍,匹配蘇南高效的農村金融服務效率及農業相關保障制度的保駕護航,不僅確保江蘇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可持續性,還能形成全國乃至全世界聞名的地方特色品牌。
參考文獻:
[1]錢 津.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要點探究[J]. 經濟縱橫,2017(5):14-19.
[2]陳曉華.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中國農業經濟學會2016年會上的致辭[J]. 農業經濟問題,2016(12):4-5.
[3]羅富民. 城鎮化發展對農業供給側結構變動的影響——基于分布滯后模型的實證[J]. 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52-59.
[4]吳海峰.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考[J]. 中州學刊,2016(5):38-42.
[5]陳錫文. 農業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J]. 農經,2016(5):18-21.
[6]江維國. 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J]. 現代經濟探討,2016(4):15-19.
[7]沈貴銀. 關于推進江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若干問題[J]. 江蘇農業科學,2016,44(8):1-4.
[8]黃祖輝,傅琳琳,李海濤. 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調整:歷史回顧、問題實質與改革重點[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6(6):1-5.
[9]Goddard E,Weersink A,Chen K,et al. Econo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agriculture[J].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3,41(4):475-489.
[10]Happe K. 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farm structures-agent-based si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to EU-policy reform[J]. Econ Papers,2005(2):1209-1220.
[11]Psaltopoulos D. Causes and impacts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s[J]. European Review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8,35(2):251-254.
[12]項光輝,毛其淋. 農村城鎮化如何影響農業產業結構[J]. 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6,31(2):77-87.
[13]周 倩.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義、困境及其實現路徑[J]. 農業經濟,2017(3):3-5.
[14]王 平,王琴梅.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區域能力差異及其改善[J]. 農業經濟,2017(4):89-96.
[15]程相友. 農地流轉區域性差異及其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影響[D]. 重慶:西南大學,2016.
[16]曹玲玲,秦小麗,吳憲霞. 提升“淘寶村”集群效應的影響因素分析[J]. 江蘇農業科學,2017,45(12):311-315. 楊麗君. 基于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的農業增長與農業供給側改革[J]. 江蘇農業科學,2017,45(19):108-11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