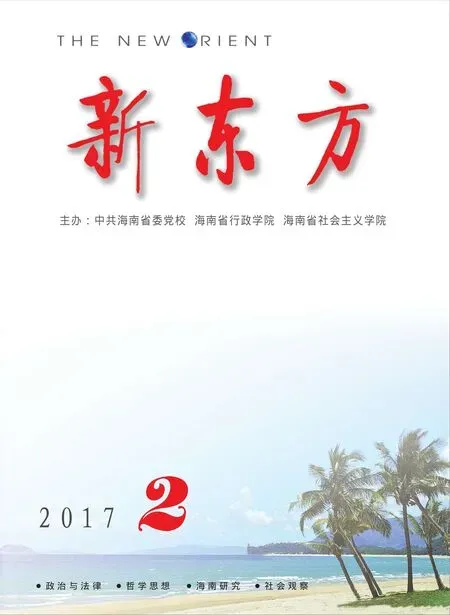加強新聞立法的若干思考
柏林
加強新聞立法的若干思考
柏林
立法在保障新聞事業健康發展方面意義重大,是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是規范新聞媒體的重要手段,是推動新聞媒體良性發展的重要動力。但目前新聞立法面臨著挑戰,如新聞訴訟中無法可依現象突出,新聞報道與司法審判間存在沖突,自媒體的傳播缺少監管,等等。為此筆者建議,在整合新聞法律體系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立法應理順新聞監督與司法獨立之間的關系,立法應完善對自媒體的規制。
新聞立法;新聞訴訟;新聞監督;自媒體
新聞是國家發展的重要事業,立法是保障新聞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方式。新聞立法的呼聲很大[1],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就曾主張對新聞加以立法,此后歷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都會有一些代表和委員提出新聞立法的相關議案或提案。特別是2014年底,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透露,全國人大正在研究新聞傳播立法,新聞法治化將提上日程。30多年來國務院法制部門也作了大量準備工作,但截至目前,新聞法學理論的研究仍明顯滯后、新聞相關權利義務關系仍未理順,新聞法仍遲遲不能出臺。
一、新聞立法的必要性
(一)新聞立法是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
從一定意義上講,新聞媒體的發展程度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與否的重要標志。而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規則,加強新聞立法不僅是新聞事業發展所需,更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迫切需要。新聞與法律相互依賴、不可分割,新聞傳播對法治起著宣傳和促進作用,法治則可規范和制約新聞傳播。法治健全的社會必然會保障新聞傳播活動在法律框架范圍內正常運行。
新聞工作影響力大、影響面廣,在建設法治社會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它是社會最重要的宣傳教育渠道之一,在宣傳和普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發揮應有效應;它是發揮輿論監督的重要方式,為國家機關特別是行政機關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保駕護航。立法就成了保障新聞在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發揮應有職能的重要途徑。
(二)新聞立法是規范新聞媒體的重要手段
新聞工作特殊性較大,媒體從業者需與各類人員打交道,總體情況是好的,但也不免有極個別人員在利益驅使下衍生“灰色地帶”,如虛假新聞、有償新聞、封口費、版面費等“潛規則”不時發生,不僅丟失了自己的職業道德與榮譽感,而且也給全社會帶來了惡劣影響。
由于我國沒有新聞立法,因此缺乏追究新聞工作中的不良現象制造者責任的機制,不少時候僅由道德層面進行譴責,很難真正糾正不良現象,不利于凈化新聞業界的風氣。因而亟需新聞立法對不良現象進行他律,通過立法規范媒體機構的從業人員。
(三)新聞立法是推動新聞媒體良性發展的重要動力
新聞立法可有效促進新聞媒體行業朝著良性方向發展。
第一,新聞媒體的合法權益會得到保障。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一般是事后監督,在現實的新聞傳播活動中,某些被新聞監督了的官員,可能會為了個人私利要求對相關新聞報道進行封殺,此時如果沒有法條來保障新聞媒體的報道權,則不良風氣就會被助長,長此以往新聞媒體將不敢行使監督權。
第二,記者的合法權益會得到保障。在采訪中,記者所代表的其實已經不是他作為公民的個體,而是在替人民行使監督權,如果此時,他的人身權利都得不到保障,談何完成監督任務。人民所享有的知情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也就難以實現。2009年《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第5條雖然指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干擾、阻撓新聞機構及其新聞記者合法的采訪活動。”但操作上,卻未有對干擾、阻撓合法采訪活動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罰的具體規定。
二、新聞立法面臨的挑戰
(一)新聞訴訟中無法可依現象突出
業界一般認為,我國改革開放后首個新聞訴訟是1985年的“20年瘋女之謎”的官司,其作者沈涯夫、牟春霜被告上法庭。時至今日已過去30多年,隨著全社會法律意識的高漲,新聞訴訟有增無減。所謂新聞訴訟一般是指,新聞媒體及其從業人員在報道時發布了失實內容,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人格權,受害方為維護自身權益,將新聞媒體及其從業人員告上法庭而引發的訴訟。因為新聞媒體具有傳播速度快、覆蓋范圍廣、受眾人群多等特點,就會讓受害者承受更多的輿論和心理壓力。通常情況下,這些新聞訴訟沒有可供適用的法律,只能借助于民法中的相關規定,在林林總總的新聞訴訟面前,就會出現無法可依或者牽強附會的現象,不利于維護社會的公平公正。
(二)新聞報道與司法審判間存在沖突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對媒體的監督權作了詳細闡釋,主旨內涵是審判應主動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輿論監督審判對促進司法的公正性而言意義重大、無可厚非,但在現實生活中,會有部分媒體在新聞報道時為賺取點擊量、追求經濟效益,不時夸大報道或虛假報道,攜輿論之意對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帶來挑戰。這就反映出新聞報道與司法審判間存在一定沖突。較為典型的如“許霆案”“藥家鑫案”以及近日的“山東辱母案”等,均存在著利用輿論給法院施壓的現象,形成了輿論導向,判案法官心理壓力加大,容易影響司法審判。
(三)自媒體的傳播缺少監管
電視、報刊等是傳統新聞媒體的主要傳播方式,需受到媒體機構層層把關,其真實性、客觀性一般會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但最近十年新媒體迅猛發展,特別是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自媒體方興未艾。但是,大多數群眾在使用這些自媒體時,并沒有經過專門新聞報道專業的學習或培訓,其傳播內容不免質量低劣,甚至有少數人故意造謠,給社會造成危害,容易形成網絡暴力[2]。
三、加強新聞立法的建議
(一)在整合新聞法律體系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
《憲法》是我國處于最高位階的法律。《憲法》中涉及新聞的相關法條主要有第22條①、35條②和第41條③。位于第二位階的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出臺的法律,其中與新聞有較大關聯的有《民法通則》第100-102條分別規定了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有《刑法》第103條規定的分裂國家罪、煽動分裂國家罪,第105條規定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第308條之一規定的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有《著作權法》第22條④,等等。位于第三位階的是國務院出臺的各種行政法規和條例,這一類的數量最大,目前共有約700多部,如《報紙管理暫行規定》《音像制品管理條例》《印刷業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等等。
上述不同位階的法律都在不同層面調整了新聞法律關系,若制定專門的《新聞法》,勢必會和上述相關規定重復或沖突。因此,新聞立法不僅是一部專門的行業法,而且應整合上述相關立法,調整好如下各類關系:新聞媒體及其從業人員的、國家新聞管理機關的、被采訪對象的等各有關主體的權利義務責任。做到內在的協調性與系統性。
(二)立法應理順新聞監督與司法獨立之間的關系
無論怎樣協調,新聞傳媒與司法獨立的矛盾都會在特定情況下存在甚至激化,這就需要立法在二者的不斷摩擦中去努力尋求平衡點。
一方面,應盡快制定和完善中國新聞立法。作為一個有成文法傳統的國家,我國應盡快制定新聞法,如果短期內難以實現的話,《憲法》第22條的規定就會難以落實,公民的言論、出版的自由也難以得到保障。用法律手段來調整新聞自由與司法公正的關系,避免現實操作中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使傳媒與司法之間的關系有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應完善新聞接近司法的系統制度。人們應認識到新聞介入司法,在總體層面上是避免司法腐敗和專橫的不可或缺的有效方式。因而,在凡是涉及公開審理的案件都應允許媒體報道的基礎上,須建立起一套雙方共同遵守的規則,如明確新聞介入案件的時間、新聞接觸司法文書的程度、法官的解釋責任,等等,要努力通過法治的規范,做到既保證新聞自由,又確保實現司法權的依法獨立公正行使,進一步理順新聞與司法的關系。
(三)立法應完善對自媒體的規制
加強立法,使得自媒體環境下的表達自由的保障和限制都能夠通過法律的方式來體現。
一方面,明確懲治的標準。如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一)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的”。
另一方面,立法規定用戶實名制。對此,2011年底北京出臺了《北京市微博客發展管理若干規定》,明確了對北京市微博客用戶采取實名制。這樣,自媒體用戶在發表言論前會受到一定的制約。這對懲治謠言、凈化新聞媒體環境,具有積極的意義。
沒有法治的社會,必將混亂不堪[3]。任何一部法律都是權利、義務、責任的統一與平衡[4]。制定新聞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能一蹴而就,這就需要政府機關、學者及社會各界人士充分發揮潛能,合力而為。注釋:
①該條規定為“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開展群眾性的文化活動。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
②該條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③該條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由于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
④該條第3項規定為“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三)為報道時事新聞,在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
[1]孔澤鳴.論我國新聞立法的思路構建[J].中國報業,2015(11).
[2]王亦高.談談對新聞法問題的基本認識[J].傳播與版權,2016(11).
[3]]趙中頡.新聞立法芻議[J].現代法學,2003(1).
[4]]張晶晶.為什么我們沒有“新聞法”[J].政法論叢,2014(1).
(作者單位:蘇州市吳江區電視臺)
D901
A
1004-700X(2017)02-0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