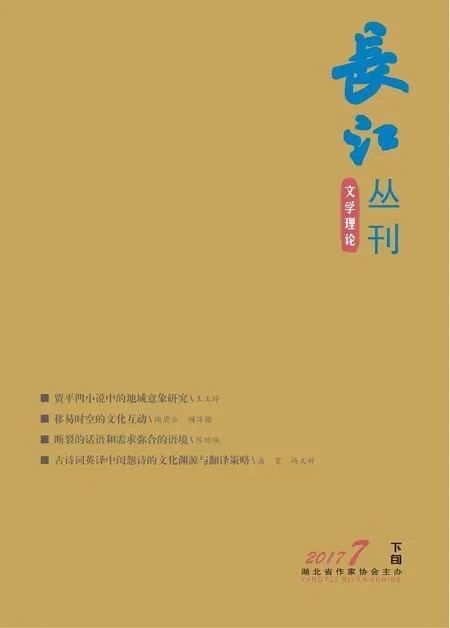鄉土情結與巫山印象的視覺轉換
馬小鳳
鄉土情結與巫山印象的視覺轉換
馬小鳳
神秘夢幻的巫山云雨,浸潤孕育巫山詩人熊魁的性靈,熊魁詩集《我在巫山等你》以獨特的個人感官圖式抒發當代地域性的鄉土文化經驗。巫山文化以相對獨立的姿態得以保持自身特殊的美學特質,文章著重從文本細讀的角度分析詩歌抒情主體的寫作姿態,指出巫山文化在當代地域性時代環境中被構筑作為精神原鄉的文化軌跡,同時為漢語詩歌觀照現實生活以及審美知識結構的轉化提供一種可行性的思路。
熊魁 巫山文化 鄉土情結 視覺轉換
詩人熊魁曾說過:巫山是有福的,生于斯成長于斯的我,也是有福的。具有充分文學敏感性的知識分子群體,難免會擁有一種錯綜復雜的心理年齡,類似葉威廉在《中國詩學》前言中強調的“郁結”。巫山風雨浸潤的鄉土文化內核,熏染和哺育生養于巫山的詩人熊魁,蘊涵詩人對于巫山和鄉土的生命體驗。“從裂縫處,生出語言的胚芽”,詩集《我在巫山等你》詩風誠摯素樸,以熾烈的深情表達對故鄉巫山的詩意眷念。鄉土情結作為一種知識與文化的傳統,伴隨時代演進的同時而不斷生成、深化成為文化傳統的一部分。詩人熊魁的詩集《我在巫山等你》分為五輯,包涵詩人個體經驗與人生歷程,始終籠罩著對巫山、神女峰、高唐觀、大寧河等巫山鄉土人事的眷念。巫山印象點綴而成的詩歌意象,在具體詩篇文本中得以多角度的復現,同時給予縱深層次的挖掘以避免鄉土意象僅僅停留在符號的層面。
巫山印象的文本復現,是詩人熊魁重點處理的藝術方式。當代詩人韓東的詩論認為“詩歌以語言為目的,詩到語言為止[1],即是要把語言從一切功力中解放出來,使呈現自身。”文學本身即為一種語言的藝術,詩歌的美感和內涵是立足于語言并最后依靠著語言而得到最后的實現的,賦予語言以情感的張力,蓬勃而出詩歌一種獨特的含蓄、蘊藉的詩性言說和表達。巫山印象,付諸詩性語言的表達,使詩歌閱讀接受者的期待視野導向聚焦為一點——即,巫山印象背后的鄉土文化內涵。巫山印象是詩人灌注強烈而熾熱內心情感表達的訴求,這在詩集的第二首《巫山有大紅》中表露地尤為明顯。“心藏十萬面大鼓,也抵不上十萬枝/晶亮的響箭從天而降,同時擂響/這三峽大地鴻蒙開辟就立于斯的巨鼓。”[2]巫山之“大紅”的具體呈現,首先在于一種磅礴的氣勢和旺盛的生命力,力度的張揚和響鼓的震動,激蕩著歷史延續至今的種族情愫,給予詩歌接受者一個宏觀的巫山印象。“我的黃櫨我的歌/我的夢想我的中國紅我的故鄉我的中國/你是我的世界,是我十萬畝疆土”,無疑使詩歌語言的張力發揮到極致。同時,也為詩人熊魁整部詩集奠定一種昂揚積極的詩性言說態度,巫山印象同故土、同中國緊密相連,是詩人內心澎湃的生活力量和希望源泉。“鷹擊長空、巖羊攀援”(《神女峰》《炮臺》《峽江的鷹》),“一葉扁舟”(《圣泉書院》《龍舟吟》《今夜,我乘坐一片葉跟你對話》),“一片云朵”(《回到張家堡》《高唐觀》《折到巫山一片云》)等巫山印象的特征性意象,給予了讀者一種“大愛巫山”的詩歌經驗期待視野。正是因為作者心中濃郁的鄉土情結和巫山大愛,所以詩性語言下巫山印象得以在文本中復現,并在與閱讀接受者情感共鳴的互動對話中得以情感深化。
鄉土意象群與傳統文化結構的內在交融,是詩人熊魁抒寫鄉土情懷的內在觀念。巫山是鄉土的縮影,更是鄉土文化的一面鏡子,印證著農耕文化的鄉土族群勤勞、質樸的生活信念與人生態度。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曾提出中國文化的十四大特征,臺灣學者韋政通在《中國文化概論》中認為鄉土文化觀念重實際求穩定的農業文化心態。農耕民族的中國人,鄉土文化觀念更是從農業生產生活中直接生發出來的精神和意識,并在傳統和現代社會中沉淀、嬗變。鄉土文化觀念是對傳統或消逝中的濃郁鄉土氣息的追溯與延續,同時在傳統“安土樂天鄉土文化觀念”[3]中激發出對生活恒久靜定認識的變更,以更加積極的心態觀照現實、投注當下生活。
詩人熊魁飽含著對故鄉巫山的深情的眷念,這同現當代文學中魯迅、蕭紅、沈從文、遲子建等等作家延續的鄉土文化觀念寫作的內涵一致,結合詩集《我在巫山等你》的具體內容主要呈現為三個方面:首先應當在于對巫山自然和土地的眷念;巫山的安靜閑逸,遠離塵囂,更得到了大自然的豐厚的禮遇和饋贈。自然山水孕育了詩意的人生棲居,“安土樂天”的生活情趣,自然土地給予詩人的內在熏陶,使詩人熊魁筆下的田壟、稻茬、峽江,無不含蘊了鄉土的深情。“我就這樣/向著一彎月牙田走去,埂外的/絲茅和蕨類植物/喂養過童年/放牧的水牛,如今依然”(《大畈田》)自然深情,寥寥幾筆勾勒出歷史時間和空間的流駛下對故土和童年的詩性感受,真摯綿厚。其次是對巫山人民的生活態度的歌詠,質樸平常的鄉土人事成為詩人熊魁筆下的詩意鏈條,以此貫穿起巫山人民對生活的熱愛。[4]“我愛你,沒有誰比我更堅決,更徹底”(《巫山有大紅》),巫山文化的魅力是因為平凡而質樸的故鄉人們善良淳樸、堅韌達觀的生活態度。詩人熊魁記寫巫山、高唐,更是記寫巫山人民對自然山水、對平凡生活的深厚熾情。例如“鞋”意象的使用,《草鞋》詩中“一雙雙草本的鞋/就這樣流落到民間”,《自畫像》詩中“我粘在一個進城農民工的鞋上/從東走到西,在那棵老黃桷樹下”,草鞋所具備的泥土質感與生活氣息濃縮著幾代人的鄉土記憶,詩歌以此作為書寫的切入點能夠充分融匯群體的社會經驗。詩人自身同時作為巫山鄉土文化的參與者和締造者,詩歌中的詩意抒寫是巫山文化的鄉土積淀生養和給予的。[5]最后一個層面則是詩人對巫山文化地域脈搏的準確把握,特別是神話傳說使詩人鄉土情結得以積淀得豐厚而深沉;神女峰,用詩人熊魁在《神女賦詩,江流步韻》一文中所說,“神女,是激發文人奇想與靈感的觸點,在蒼茫時空中飄逸著千萬斯年的發絲”。神女“孤獨地旋舞”,在詩人的心上馳騁,牽動著所有關于巫山、鄉土的慨嘆,“那么,讓我們巖羊一樣/攀到你身邊,用唇齒/梳理你的銀絲鬢發”,用盡詩人畢生的摯誠。鄉土觀念和鄉土意象,在詩人筆下自發渾然融合。
詩人熊魁《我在巫山等你》用詩性的語言詮釋著三峽文學、巫山文化的深刻內涵,具有鮮明地域色彩的巫山濃郁鄉土氣息。鄉土文化經驗的藝術轉換,側重于從懷舊與牧歌兩個側面對鄉土文化情結進行創造性地闡釋。詩人或讀者,在閱讀經驗期待視野中獲取的是一種懷舊與理想交融的二重變奏:對巫山文化為代表的故土家園的追溯性懷舊,激起一種美好的類似落葉歸根的文化歸屬情懷,這同樣也是一種自我身份的投射和認同。現實時代缺乏一定的理想性,是詩歌閱讀體驗中一種有距離、有目的的審美性觀賞,鄉土情結的質樸純真誠然是理想性的伊甸園。《神女峰》一詩正是如此,“用干枯的柴柯/為你生燃一堆篝火/煨融漫天雪凍,然后/陪你,一起眺望遠天杳鶴”,溫暖融化凜冽,渴望以神女峰兒女的身份用全部身心的愛供養她,觸摸巫山和神女的靈魂,更是追溯詩人內心最初的鄉土情結,譜寫著理想的田園牧歌。
實際上當前的鄉土詩歌寫作面臨鄉土自身精神文化資源貧瘠的危險,鄉土愈發被粗暴地剝離成為一種言語符號,巫山鄉土文化的精神內核只有放置于鮮活、生動的現實土壤中,才能夠調動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共識與群體意識,并以此為契機形成思想的共鳴,更加熱情地擁抱現實和當下,從另一個層面上讓鄉土的傳統得以延續和深化。從這個意義來看,熊魁的詩歌從個人感官和視覺轉換的角度充分注意到日常生活經驗的“重復”,用細膩敏感的筆觸將這種重復賦予深情與留戀,文化的親和力與感染力躍然紙上,這對于當代鄉土經驗的詩歌書寫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性。
[1]薛世昌.現代詩歌創作論[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233.
[2]熊魁.我在巫山等你[M].武漢:長江出版社,2011.
[3]張岱年,方克立.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72.
[4]聞一多.唐詩雜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9.
[5]傅小凡,蘭浩.鄉土情結與傳統文化歸根意識[J].中北大學學報,2011(6).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
馬小鳳(1990-),女,甘肅平涼人,碩士研究生,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研究方向:中外文學關系、比較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