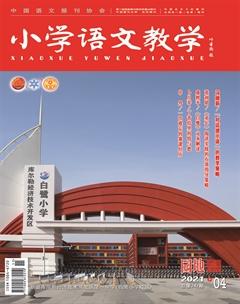指向整本書閱讀的節選類課文教學
趙永常
統編本教材非常重視學生的課外閱讀,主編溫儒敏先生指出:教材遠遠不能滿足閱讀教學需要。因此,統編本教材除了設置精讀課文和略讀課文,還將課外閱讀納入課程體系中。其中,很多精讀課文都來自著名作家的經典原著,教師切不可就一篇課文教一篇課文,而要著力于一篇,著眼于整本,積極打造從一篇到一類的課堂教學體系。統編本五年級下冊習作單元中《刷子李》一文,選自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主人公刷子李是奇人,身上的奇聞軼事應該很多,但作者并沒有鋪開描述,而是選擇一件極富沖突性和戲劇性的事例,展現其獨特的本領和智慧。那如何從這篇《刷子李》,順勢過渡到馮驥才先生整本的《俗世奇人》呢?
一、導入順勢而下,把握小說文體的創作特性
節選類課文有著自己的特點,導入新課時教師不妨將目標放大一些,不要僅僅局限在所教學的課文中,還可以從原著入手,形成從原著到課文的過渡,建立起一篇課文與一本書之間的內在聯系,為后續閱讀整本書奠定基礎。
教學《刷子李》時,教師就可以引導學生從馮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入手,出示整本書的封面,介紹作者馮驥才,然后關注書本中的目錄。在仔細觀察中,學生從目錄中不僅發現了“刷子李”,還發現了這本書的目錄大部分都是以人物的名字命名的,如“蘇七塊”“藍眼”“背頭楊”等,而且每一篇都獨立成章,互相之間并不干擾。隨后,教師將學生的關注力從目錄中各種不同的人物身上回歸到整本書的體系上來,讓學生初步理解“俗”與“奇”的意思,讓學生了解到這些人物都是普通俗世中有著特殊本領的人。今天,我們就來學習其中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教師相機揭示并板書課題:刷子李。
馮驥才的《俗世奇人》是一篇充滿天津衛色彩的短篇小說集,整本書的書名、目錄和入選統編本教材中的題目,二者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通過這樣的導入,學生不僅知道了課文《刷子李》的出處,同時也感受到這本書中小說的內容彼此之間的聯系,將所要學習的課文與整本書進行了首次聯系,為后續的拓展提供了認知性的儲備資源。
二、開課聚焦重點,洞察小說語言的獨特風格
馮驥才先生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這本《俗世奇人》又是反映清末明初各種奇特藝人的生活,所以整本小說流淌著濃郁的天津氣息。為此,教師就可以選擇天津傳統的說書形式,為課堂教學服務,讓學生在聆聽說書、嘗試說書的過程中,感受小說作品中獨特的語言形式和濃郁的地方特色。
以教學《刷子李》的第1自然為例,筆者先播放了一段天津說書選段,其內容就是第1自然段對刷子李的介紹:“刷子李專干粉刷這一行……只要身上有白點,白刷不要錢。”這一舉動看似簡單,卻改變了學生對文本語言的感知方式,將原本枯燥的語言文字符號轉化為更加契合學生認知規律的聲音,學生不僅聽得認真入神,更激活了認知思維,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聽完之后,我組織學生迅速梳理和整合素材,并交流自己的發現:有的學生發現了刷子李得名的原因,有的學生描述了刷子李獨特的本領,還有的學生從刷子李立下的規矩感受到了他的個性特點。我相機將學生的發現進行提煉與升華,形成對刷子李這一人物的高度概括:奇特的絕活、奇特的規矩、奇特的綽號。在這樣的基礎上,筆者迅速拓展了《俗世奇人》對其他人描寫的片段,并鼓勵學生也嘗試運用說書的方式,與同桌交流這個人的特點,并緊扣“奇特綽號”結合自己說書的信息,從目錄中尋找還有哪些相同的命名方式,比如泥人張、背頭楊等。
借助說書的形式,學生發現了作者為人物起名字時的共性思維,實現了文本之間的再次聯系,同時對于整本書所描寫的人物以及人物的特點就有了更加深入的感知。
三、品味凸顯神奇,感知小說人物的豐滿形象
任何一篇小說都離不開人物、環境和情節這三個核心要素,其中情節的設定和環境的渲染,都以刻畫人物的形象為目的。因此,一篇小說是否成功,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就在于其所刻畫的人物是否鮮活且富有獨特個性。
《刷子李》為展現人物技藝高超,以刷子李帶著徒弟外出刷墻的經歷作為載體,教師就要緊扣這部分內容,通過印證的方式,凸顯刷子李獨特的人物形象。教師可以組織學生自由閱讀課文第3~6自然段,關注描寫刷子李言行的語句,并圈畫出相關的關鍵性詞語,讓學生運用批注的方式寫寫自己的感受。隨后,教師引導學生緊扣語段中的關鍵詞語進行交流,有的學生從“悠然擺來”“悠然擺去”等詞語感受到刷子李的胸有成竹、氣定神閑;有的學生從作者想象出來的“鼓點”“琴音”等,想象到刷子李在刷墻時獨特的節奏感,讓人覺得看刷子李刷墻,絕對是一種藝術的享受;還有的學生從描寫刷墻效果的“雪白的屏障”“平平整整”“天衣無縫”等詞語中,感受到刷子李刷墻令人震撼的效果,將“神奇”二字真正鐫刻在學生意識深處。在對課文的正面描寫進行了體悟和品析之后,教師相機從情節的角度展開追問:“作者為什么要描寫徒弟曹小三發現師傅有詐的反轉情節?”這樣讓學生感受一波三折對于小說的重要性。在這樣的基礎上,教師再次組織學生利用目錄,選擇其中一個人物,相機猜測這個人物可能會做什么絕活,并鼓勵學生快速閱讀小說中重要的語段,印證自己的思維,對這篇課文的閱讀形成必要的補充。
一個是正面的描繪展現,一個是側面的積極烘托,作者著墨不多,但將整個人物都寫活了。依托這樣的寫法,教師讓學生從其他小說中進行拓展閱讀、猜測印證,實現了從一篇到整本書的第三次聯系,豐富了學生的感知。
四、依照循序漸進,體悟小說情節的獨具匠心
作為相同地域、相同時期、相同目的的一本小說集,這就意味著這本書中所有的小說,無論是人物、情節、環境,亦或者是寫作方法,都有著諸多的共性。教師就可以借助整本書中的其他篇目,與統編本教材中的課文形成相得益彰的匹配,形成“1+1”的模式結構,讓學生更好地感受小說創作的獨特之處。
如教師可以借助《俗世奇人》中的《泥人張》,組織學生分段落進行快速閱讀,并提出自己的問題,關注小說情節設置的精妙。如海張五嘲笑泥人張:“在哪里捏?袖子里,還是褲襠里?”此時此刻,你覺得泥人張會有怎樣的表現呢?在閱讀《泥人張》中第二個片段時,可以鼓勵學生再次猜測情節的發展變化,如當泥人張捏出來的泥人惟妙惟肖,之后會有怎樣的情節變化呢?后來又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呢?……可以繼續引導學生進行猜測。由于課堂教學中拓展的文本,教師不需要也沒有充足的時間要求學生進行細讀,所以在這一系列的過程中,教師就可以組織學生以分段的方式進行閱讀,一方面能減輕學生閱讀的壓力,同時也能給予學生大膽猜想情節、相機體會小說情節特點的契機。在這樣的基礎上,教師可以將《泥人張》與《刷子李》這兩篇小說統整起來,組織學生繪制兩篇小說的情節圖,讓學生找出彼此的相通之處,并鼓勵學生閱讀《俗世奇人》中其他小說時,也可以采用繪制情節圖的方式,從而提煉并感受這本書中短篇小說在情節設置上的異同點。
單篇教學終覺淺,深入感知要整合。在這一案例中,教師就借助書本中的其他小說,與所教學的課文形成對應,構建表達上的認知框架,并作為整本書閱讀的策略,提升學生的語言實踐能力。
節選類課文的教學既要關注課文這一篇,又需要有整合和擴展意識,幫助學生建立從單篇向整本書邁進的通道,鼓勵學生進行語言實踐,為學生語文綜合能力的發展奠定基礎。
(作者單位:山東莒縣招賢鎮浩宇浮來春希望小學)
責任編輯 宋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