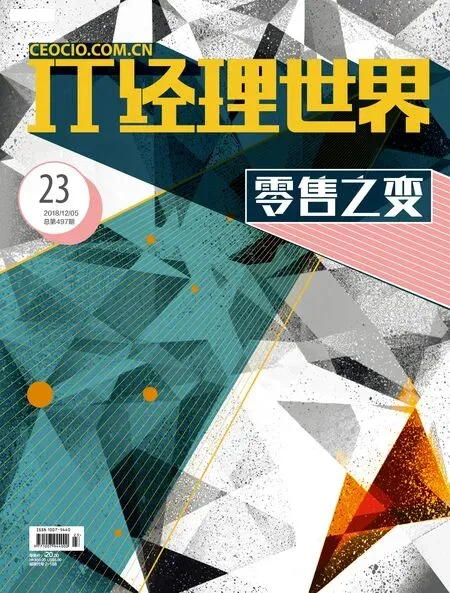如何破解全球貿(mào)易和氣候變化難題
鄭渝川
最能體現(xiàn)全球化復(fù)雜性的問題,就是全球氣候問題及相應(yīng)的聯(lián)合行動(dòng)。
最能體現(xiàn)全球化復(fù)雜性的問題,就是全球氣候問題及相應(yīng)的聯(lián)合行動(dòng)。氣候問題作為全球議題被提上議程,是在20世紀(jì)70年代。之后,世界各大洲的多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以及主要的經(jīng)濟(jì)組織都參與到這其中。1987年《蒙特利爾議定書》簽署,之后又有了《京都議定書》等合作協(xié)議。而在這期間,科學(xué)界更加清楚的解析了造成全球氣候危機(jī)的原因,并不斷提交人類活動(dòng)改變氣候的科學(xué)證據(jù)。
最近幾年,世界部分地區(qū)頻繁遭遇極端氣候變化的沖擊,例如,干旱和洪澇災(zāi)害的強(qiáng)度加大,亞洲東海岸地區(qū)遇到的夏季季風(fēng)更加不穩(wěn)定,海洋加速升溫已經(jīng)使得格陵蘭和南極的冰蓋加速融化。至于巴西、澳大利亞等國,則更加頻繁的遇到森林山火。另外,部分地區(qū)在夏季的最高氣溫看上去失去了控制,以至于死于高溫的人不斷增加。
可以說,包括頻頻在全球氣候變化行動(dòng)中提出異議的美國在內(nèi),世界各個(gè)國家和地區(qū)對(duì)于氣候變化的危險(xiǎn)性、成因和解決方案,有著廣泛的共識(shí)。這也是多個(gè)國際框架公約和議定書得以簽署的原因。但究竟應(yīng)當(dāng)如何劃分各個(gè)國家和地區(qū)的減排份額,是按照世界人口數(shù)量確定排放額度還是依照現(xiàn)有排放總量確定減排比例,需不需要考慮到一些工業(yè)化國家歷史上有過的嚴(yán)重污染記錄,這一系列的爭議迄今沒有得到確切解決。
澳大利亞、美國哲學(xué)家、國家倫理學(xué)學(xué)會(huì)前主席、普林斯頓大學(xué)生命倫理學(xué)教授彼得·辛格在其所著的《如何看待全球化》一書中,討論了當(dāng)前全球化最為核心的幾項(xiàng)議題,包括全球氣候變化、國際貿(mào)易進(jìn)程、國際法與國內(nèi)法、對(duì)外援助與慈善。彼得·辛格以世界級(jí)倫理學(xué)家的視角,超越單個(gè)國家的狹隘視角,基于促進(jìn)全球和平、持續(xù)發(fā)展的出發(fā)點(diǎn),對(duì)上述問題給出了深入淺出的介紹。
彼得·辛格詳細(xì)討論了應(yīng)對(duì)全球氣候變化所展開的行動(dòng),所需遵守的倫理法則。首先,歷史原則即污染者付費(fèi)原則不可忽視,無論是洛克的觀點(diǎn)還是斯密的理論,都沒有為富人、富國工業(yè)化過程中濫用大氣排污提供足夠令人信服的理論依據(jù)。彼得·辛格認(rèn)為,中國、印度和巴西等發(fā)展中國家就制約氣候變化所給出的解決方案是相當(dāng)公平的,也就是說,工業(yè)化國家需要為過去的工業(yè)化、更長時(shí)間的、不受節(jié)制的污染排放承擔(dān)歷史代價(jià)。其次,即時(shí)原則也同樣重要,這需要換算出氣候變化帶來重大危機(jī)的污染程度,以及對(duì)應(yīng)的排放存量,然后按照人均相等的原則算出各國份額。
當(dāng)然,彼得·辛格主張的上述兩項(xiàng)原則,很大程度上與美國、日本、歐盟等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體在氣候變化行動(dòng)上的立場是完全相悖的,后者更希望依照國家排放總量、不考慮歷史存量來計(jì)算份額,并且要建立排放份額的交易市場,這樣一來,富國可以通過向窮國購買份額的方式來維持生產(chǎn)、生活水平不變。另外,還有經(jīng)濟(jì)學(xué)者主張依照經(jīng)濟(jì)規(guī)模、生產(chǎn)效率確定排放總額。在彼得·辛格看來,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體的主張存在嚴(yán)重缺陷,他認(rèn)為無論如何都必須考慮到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巨大資源差距,要盡可能改善最弱勢群體的境遇,由富國來承擔(dān)必要變革的主要成本。
《如何看待全球化》書中在討論國際貿(mào)易時(shí),列舉了反對(duì)經(jīng)濟(jì)全球化、要求限制國際貿(mào)易的幾種主張(經(jīng)濟(jì)全球化將對(duì)經(jīng)濟(jì)的考量置于環(huán)境等關(guān)懷之上,經(jīng)濟(jì)全球化侵蝕了國家主權(quán),經(jīng)濟(jì)全球化主要是由富國集團(tuán)操控的,經(jīng)濟(jì)全球化助長了不平等)。彼得·辛格分別解析了上述幾種反對(duì)主張。在他看來,宣稱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國際貿(mào)易會(huì)破壞環(huán)境的說法,實(shí)際上罔顧了正是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力量,才在全球范圍內(nèi)加速實(shí)現(xiàn)了環(huán)境保護(hù),并且使得美國這樣的發(fā)達(dá)國家以及眾多的發(fā)展中國家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去保護(hù)海洋環(huán)境、海洋生物。當(dāng)然,經(jīng)濟(jì)全球化議題往往確實(shí)會(huì)涉及到國際法、國際道德義務(wù)與國內(nèi)法的抵觸,需要依照社會(huì)正義和環(huán)境正義的原則進(jìn)行必要的調(diào)適。
經(jīng)濟(jì)全球化和國際貿(mào)易秩序目前存在的最突出問題,的確在于少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掌控著制定標(biāo)準(zhǔn)及裁量沖突的主導(dǎo)權(quán),而其他多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只能被動(dòng)接受。彼得·辛格提醒人們,時(shí)至今日,要在WTO內(nèi)部聽到最貧窮國家的聲音仍然非常困難。而經(jīng)濟(jì)全球化是否增加了全球范圍內(nèi)的不平等,這一問題并無權(quán)威答案,因?yàn)橐环矫妫?jīng)濟(jì)全球化特別是金融全球化,如《21世紀(jì)資本論》等著作指出的那樣,使得全球范圍內(nèi)頂級(jí)富豪的財(cái)富進(jìn)一步加速積累,貧富懸殊拉大;但另一方面,經(jīng)濟(jì)全球化也增強(qiáng)了全球扶貧濟(jì)困的能力,極度貧困人口總量近年來發(fā)生了下降。
當(dāng)然,作為倫理學(xué)家的彼得·辛格,認(rèn)為WTO及主要的貿(mào)易大國都應(yīng)做得更好。他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的經(jīng)典論述后指出,自由貿(mào)易在促進(jìn)創(chuàng)新、增加消費(fèi)者選擇權(quán)的同時(shí),確實(shí)也會(huì)打破原有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行業(yè)秩序,在監(jiān)管失當(dāng)?shù)那闆r下,還可能加劇污染、造成工人權(quán)益得不到保護(hù)。書中提出建議,希望主要的貿(mào)易大國要在降低上述沖擊和負(fù)面影響的情況下,繼續(xù)遵照市場的力量創(chuàng)造價(jià)值。
《如何看待全球化》書中還提出,要以地球共同體、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意識(shí),增強(qiáng)對(duì)于世界部分地區(qū)極度貧困人口的援助,而這也是全球化進(jìn)程所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的道德使命。